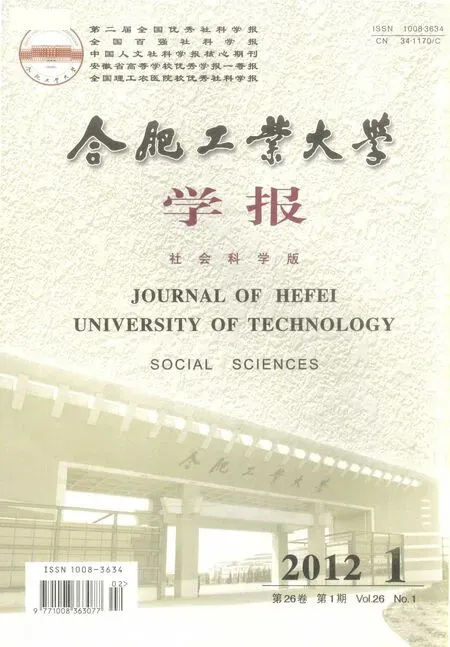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丁 进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私人叙事的兴起:武王伐纣时期的铭文创作
丁 进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最早的两篇铭文,《利簋铭》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天亡簋铭》记载了灭商之后十二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众神的事件,出现了三线索叙事,使用了抒情手段和修辞格,构建了立体叙事场,显示了明显的写作艺术追求。两篇铭文开创了西周私人写作的文化传统。
利簋铭;天亡簋铭;私人叙事
殷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艺术,造型奇特、纹样复杂、气魄宏大,让周人难以企及。然而周人在青铜器文化上有足以与殷人媲美的东西,那就是铭文创作。他们将晚商人开创的铭文私人化写作发扬光大,将青铜器作为文字载体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创作了为数众多的青铜器铭文,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西周青铜器铭文创作的开端,《利簋铭》和《天亡簋铭》在这个传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私人的眼光从多个角度记录了武王伐纣这一伟大事件,在史官叙事之外,展开了多侧面的私人叙事,开创了西周私人化写作的先河。
一、以武王伐纣事件为中心的文学创作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当时的文艺创作对这一伟大事件也做出了反映。根据《书序》,收入《尚书》的就有《泰誓》、《牧誓》、《武成》、《洪范》、《分器》五种共七篇:
惟王十一年,武王伐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而归,识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1]。
根据《逸周书·周书序》,《逸周书》至少有十四篇记载了武王伐纣历史事件:
武王将起师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
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喻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顺》、《武穆》二篇。
武王将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众,作《和寤》、《武寤》二篇。
武王率六州之兵,车三百五十乘,以灭殷,作《克殷》。
武王作克商,建三监以救其民,为之训范,□□□□□□□□□作《大聚》。
□□□□□□□□□□□武王既释箕子囚,俾民辟宁之以王,作《箕子》。
武王秉天下,论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
武王命商王之诸侯绥定厥邦,申义告之,作《商誓》。
武王平商,维定保天室,规拟伊洛,作《度邑》[2]。
加上《尚书》七篇,一共二十一篇,内容包括从出兵前的谋划到灭纣后的政权巩固,囊括了整个进程①近代关于上述《牧誓》等篇写作年代多有否定两《书序》说,以为后人追述其事。但近年来学界又逐渐接受两《书序》的大部分说法,只是认为这些篇章虽为当时史官所记,但在流传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后代词汇和语法的“玷污”。可参阅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相关篇目的“讨论”部分,中华书局2005年版。。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史官文化传统的杰出成果。然而这二十一篇只有《尚书》中得《牧誓》、《洪范》以及《逸周书》中得《度邑》、《克殷》和《世俘》等篇并不完整地流传下来,《泰誓》虽在,已经真伪难辨。
当时的诗歌创作对这段历史进程也有所表现。根据今人马银琴的研究成果[3],武王时期创作的仪式乐歌有《周颂》中的《我将》、《赉》、《酌》、《时迈》、《般》,作于周公、成王时代的有《周颂·武》,《大雅》中的《大明》、《维清》、《维天之命》②关于雅、颂诗篇创作年代问题颇为复杂,《毛诗序》多有提示,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列武王时期诗歌竟然有13首,因无有力证据,今不从。。青铜器铭文创作方面,目前已经发现《利簋铭》和《天亡簋铭》。与《诗经》、《尚书》、《逸周书》诸篇不同,这两篇铭文的原器均在,是武王时期的实物,也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原文,为我们研究西周文章提供了十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本文试图从史官叙事和私人写作的分野这个角度入手,考察两篇铭文的文学史地位。由于时代久远,今人对当时的历史文化已经有诸多隔阂,造成铭文阐释的困难。为了便于艺术价值的分析,本文从两篇铭文的解读开始。
二、利簋铭释读
利簋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铭文三十二字。文字隶定没有争议,但在“岁鼎”两个字的解读上出现了重大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铭文内容的通读,影响对铭文写作艺术的评价。《利簋铭》全文如下③此种释读依据的是于省吾先生的《利簋铭文考释》,见载于《文物》,1977年第8期,本文尽可能采用于先生提出的通假字代替原铭中难以识别的生僻字。: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师赐有司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关于“岁鼎”二字,唐兰、于省吾、张政烺、郭沫若等学者分别提出“夺鼎说”、“占卜年岁说”、“岁星当位说”、“岁祭说”。三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岁鼎”问题,绝大多数文章只是对以上四说的细化和补充,总体上没有超出唐兰、于省吾、郭沫若、张政烺各说的范围。
“夺鼎说”由唐兰提出。他认为“岁”字是“戉”字,即“越”字的初文。越鼎就是夺鼎,他将“岁鼎克闻”读成“越鼎,克昏”,夺了九鼎,打败了昏庸的商纣[4]。按照这种说法,周武王曾经在牧野之战前就组织了一支夺鼎突击队,并先于大军行动,深入商都,潜入宗庙,在甲子日早上得手。随后西周联军行动,在牧野接战,取得胜利。问题是传说的夏禹所铸九鼎虽不一定如春秋王孙满所形容的那样沉重,但也不是随便就能带走的轻便装备,让突击队深入商都重地去抢夺九鼎,几乎是送死。由于九鼎是重器,只要在正面战场上击溃了商纣王的主力,商纣王的公室宗庙及其重器不都是胜利者的战利品?《克殷解》是说武王入都以后才命南宫迁鼎,而铭文所说的“岁鼎”是在甲子朝,即大战之日的早晨,时间不符合。
“占卜年岁说”由于省吾先生提出。认为“岁鼎”即“岁贞”,而“岁贞”也就是“贞岁”,占问年成好坏:“总之,‘岁贞克闻’,是说武王伐商之前,从事岁贞而吉,已为上帝所知。”[5]
占卜年岁说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与“唯甲子朝”的叙时不一致。“唯甲子朝”应当是正在发生事件的时间,若按照于先生的解释,则刚提到具体时间却不说所发生的事情,直接插入以前的“岁贞”及其结果,不但文气断了,而且句子残缺不全。“岁贞克闻”若按照于先生的解释,属于预谋阶段的事件;“珷征商”则是对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叙述,两句在时序上颠倒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说完,忽然插入另一件事情,这种时空跳跃的写法在西周铭文中没有第二例。
“岁星当位说”也为于省吾提出[5],不过他并不主张。倒是张政烺主张该说,以为是木星正当位,有利伐商[6]。
“岁星说”也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传世文献有多篇提到武王伐纣事件,但都没有指出那一天是“岁星当空”;如果真有这一天象,正好代表“天意”,武王凌晨誓师时候怎么可能不讲?《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白光琦认为这是战国人根据战国时期的立法知识倒推出来的,商周之际尚未发现岁星运行规律[7]。黄怀信也不赞成此说,以为岁星在星空运行,无所谓当位不当位,因此他提出“岁鼎”为岁星在中天。黄怀信依据当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在公元前1101年3月9日早晨7点正好岁星在天空中央,即使这样,黄说也还是“岁星当位说”的一个衍生[8]。
“祭祀说”根据黄盛璋的文章,应当为郭沫若首先口述,再由黄盛璋转述,以为“岁”为甲骨文常见的祭名。“岁鼎”读为“岁,贞”,即岁祭并进行占卜[9]。
“祭祀说”似乎都能讲通。“岁祭”不是“祭岁”,是杀牲而祭祀,大战在即,祭祀一下鬼神祈求胜利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如果将前后文联系起来看,有司利(或者右史利)在这次战略中做了什么就不得而知,铭文前面大部分成了客观的历史叙事,与有司利无关。我们不禁要问:右史利凭什么获得周武王的赏赐?
笔者曾经著文认为铭文中的“岁”是人名,就是下面提到的有司利[10]。利是字,岁是名。“赐有司利金”是对周武王赏赐命令的转述,属于“他称称字”;“岁鼎”之“岁”属于自称,自称称名。“岁”的本义为斧头之类的武器,“利”为锋利,是武器的属性,一名一字,名字相因。“鼎”从于省吾释,为“贞”,“贞”即占卜。“岁贞”即岁进行了占卜。这样,利簋铭文就可以标点如下了: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
辛未,王在管师,赐有司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岁”字问题一旦解决了,我们不难通读全铭了: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这一天早晨,有司岁利受命占卜,占卜结果为“克”。果然听到前线传来捷报:到第二天凌晨,周军完全控制了商都。到了第八天,武王到达管师,在这里赏赐了有司利铜料,有司利就用这些铜料为檀公制作了宝器。
由于“岁”字乃是人名,加上前辈学者成果解释了“鼎”、“闻”、“夙”等字,铭文的通读几乎没有障碍,内容非常简明,三十多年来的种种争论看来都是求之过深了;同时建立在“岁星当空”或者“岁星在天空正中”的说法失去了依据,虽然有些遗憾,但恢复铭文本来面目也是一种解脱。
三、天亡簋铭文解读
天亡簋有铭文七十八字,篇幅是利簋铭文的一倍:
乙亥,王有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饎上帝。文王监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庚,丕克讫殷王祀。丁丑王饗,大宜,王降,亡赉釐复饢。惟朕有蔑,敏启王休于尊簋①天亡簋铭文隶定还没有统一的意见,此处断句从于省吾、刘晓东等学者意见,天亡所获赏赐物品,从孙常叙意见。。
据陈介祺介绍,该器出自陕西岐山。孙稚雏根据陈介祺《聃敦释说》推断,该器大约出土于1843年之前,出土后不知去向。1956年北京琉璃厂振寰阁古物店从上海周姓人士处购得,后归故宫博物院[11],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天亡簋的年代问题,学者大多根据“文王监在上”,定为武王器。但在伐商之前还是之后,尚有有争议。以为在武王伐纣前的又分两说。孙作云以为在武王伐商前一段时间[12],孙常叙以为在大军出发前夕十三天,举行大封之礼,会同东南西三方诸侯[13]。唐兰[14]、于省吾[15]以为伐商以后祭祀文王所作。于省吾将此篇与《世俘》相比较,以为同一事件,只是《世俘》的天干传写错误而已。刘晓东以为时间在克殷之后的“度邑”期间,与克殷没有直接关系[16]。笔者以为,依据“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以文王为“显考”,则时王非武王莫属;“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庚”是互文兼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的还是武王,是对如何完成事实“丕克讫殷王祀”的回顾性陈述,不是祈祷句,三个“丕”连用,营造气势,加快节奏,更暗示三句为同一类型陈述句,因而“丕克讫殷王祀”说的是事实,而武王克商后一年即去世,唐兰、于省吾说正确。铭文记载的是武王伐纣成功后的第十二天,武王先拜祭了西、南、北三方名山大川众神,以感谢他们对来自三方向伐商联军的保佑;然后利用殷人的“天室”举办祭祀文王和上帝的大礼仪,天亡作为佑者参加了这次大祭祀;又过了两天,武王举行饗礼,天亡受到武王的赏赐,天亡因此作器纪念这次荣耀和武王的恩赐。
四、利簋铭文显示了从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
中国文化中的史官传统极其发达。早期诗文二分,其中“文”的创作传统由史官所建立,并且树立了“史传文学”的典范,与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中散文的三座高峰。
青铜器铭文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有显著的区别。历史散文的作者——史官几乎不显露个人的情感,他们的叙事立场类似于“为天地立心,为万世立法则”,即他们为代表超越于时代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法则而写作,他们的写作立场是“历史理性”。诸子散文有私人叙事,但哲学意味更浓,主要表现个人的思想认识成果。青铜器铭文写作主要从私人立场出发,写私人生活。而私人生活写作必然催生纯粹文学意义的散文诞生。在从史官历史叙事向青铜器铭文私人叙事的发展中,利簋铭和天亡簋铭是一个标志,代表西周私人叙事的兴起。我们先从天亡簋铭谈起。为方便理解史官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区别,我们先引用《尚书·西伯勘黎》进行对照。
《西伯勘黎》记载了殷之大臣祖伊谴责商纣王的事件: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摰。’今王其如台?”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与戮于尔邦!”[1]
在这篇短文里,关于作者个人的信息几乎没有出现。文章有价值判断,有感情取向,这些判断和取向隐藏在客观叙述之下,归依在“秉笔直书”的史官文化传统之中。
青铜器铭文写法有显著的差别。这里以小臣宅簋铭为例:
隹五月壬辰,同公在丰,令宅事伯懋父。伯赐小臣宅画甲、戈九,赐金车、马两。扬公、伯休,用作乙公尊彝,子子孙孙用宝,其万年用飨王出入[17]。
五十三字的短文叙述了四件事情:第一,同公派小臣宅到伯懋父那里去办事;第二,伯懋父赏赐了小臣宅;第三,小臣宅为了宣扬同公和伯懋父给予自己的荣耀,制作了青铜器;第四,小臣宅祈祷自己子孙永昌。比较《西伯勘黎》不难看出,这段铭文的私人叙事性质是《西伯勘黎》所不具备的。特别是第四点的嘏辞部分,是典型的铭文写法,成王中晚期以后铭文写作大多有这一项。小臣宅铭文创作的年代,陈梦家将它放在周成王时期,从其体制看,铭文虽短,已经完全具备了标准铭文的结构,因而具有典型性,我们不妨用图表形式展示一下小臣宅簋铭的叙事链:
受命→事伯→受赐→作器→祈愿……
利簋铭是西周开国第一篇铭文,他的作者右史利是个史官①当然,铭文中的“右史”也可以隶定为“有司”,即使这样,也不会动摇本文立论的基础——“有司”是朝廷官员的统称,“右史”也是“有司”中的一员。,其铭文写作显示了史家笔法的高超技艺,同时又兼具私人叙事的性质,标志着西周私人化的青铜器铭文创作即将兴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采用事件链和叙事场域来分析,下面是利簋铭的叙事场域图:
从内容上看,图中左边的事件链可以放在史官叙事传统中,总共只有25字,却叙述了四件事情,叙事效率极高。同时也可以看出铭文侧重点仍然在左边。左边的叙事内容可以统摄在武王伐商这个主题之下,其中“征商”、“有商”完全属于历史写作;“岁贞”和“赐金”则介于历史写作与私人写作之间,因所叙述的事情也属于国家事件。右边则属于纯粹的私人叙事,所叙事件“作器”只是右史利家族私事,在比重上也只有七字,呈现出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的过渡状态。
从选材角度看,则铭文的私人叙事意味更浓一些。左边四个事件采取的是显性叙事方式表达,其实在这一天尚有更多的事迹,铭文没有直接叙述。这种选择性叙事反映了铭文的偏向——重在私人叙事:所选择的不是正面战场将士们的英勇事迹,而是右史利个人在这次战役中的贡献和所受嘉奖。由于右史利自己就是史官,铭文的写作风格还是简洁明了,追求每一个字最大的信息表达量,真是一字千金。

图1 利簋铭文史官叙事与私人叙事示意图
五、天亡簋铭显示了铭文创作的艺术追求
天亡簋铭记载的事件比利簋铭只晚六天,两文的创作技法有一致处,更有重大差异。除了篇幅多出利簋铭一倍而外,创作风格上一改利簋铭的严谨和简略,有四个方面不同:三线索叙事、抒情、修辞与叙事场域的扩张。
在叙事线索方面,《利簋铭》是双线索叙事,一主一副,剔除了与双线索无关的其它内容,即使其它内容意义重大也不入笔下。利簋铭的主线是武王伐商,副线是右史利的活动。武王伐纣是主线,体现在铭文主体事件因武王伐纣而起,其中右史利的占卜、受到赏赐都是由于武王的指令。然而铭文的副线也制约着主线事件叙事的选择:武王伐商期间激动人心的事件很多,但铭文只选择与自己有关的事件去记载,这是因为右史利所作之器是祭祀檀公的礼器,具有严格的宗族排他性,此种排他性无疑也促进了铭文叙事的私人化倾向。
《天亡簋铭》则是三线索叙事,一主二副、二显一隐。显性线索是武王与天亡的活动,隐性线索是“文王监在上”与上帝等众神等待告成功;主线是周武王的礼乐活动,第一副线是天亡参与这些活动并受赏赐,第二副线是文王与众神。虽然两铭所记作器目的不尽相同,《天亡簋铭》也如《利簋铭》一样,只选择与三线索有关的事件记叙,排除了其它事件。
《天亡簋铭》在创作上出现了抒情体句子,采用了反复、对仗修辞格,这是《利簋铭》所不具备的。铭文出现了类似于《诗经》“颂体”的句子:“文王监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庚,丕克讫殷王祀”——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可见铭文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事件叙事,在创作中注入个人的感情,对文王的德行和在天之佑的歌颂,对武王效法文王,完成克商大业的赞美,以及个人对完成伟大事业的兴奋之情洋溢其间。这四句即使不是天亡的独立创作,至少也是对祭祀仪式用辞的改写,不是简单的抄录。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抒情性效果是通过反复、对仗的修辞手段实现的,体现了铭文对写作艺术的追求,这在西周铭文中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中华散文写作史上的第一次。
在叙事场域方面,《利簋铭》体现了史官叙事向私人叙事过渡的状态,叙事轴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天亡簋铭》由于引进了文王这个线索,实现了空间的拓展,将虚拟的天神世界与人间世界对接在一起,此种效果虽然为天亡个人的宗教观念所引起,却拓展了铭文创作空间,提高了铭文的表现力。
六、利簋铭与天亡簋铭的文学地位
私人叙事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大事。上世纪梁启超等学者宣称战国以前中华无私人著述,但由于西周青铜器铭文私人叙事性质的确认,梁启超等人的论断将受到挑战,同时这也将为研究春秋战国中华思想文化大爆发的原因提供新思路。另外,由于青铜器铭文私人叙事性质的确认,先秦文学之林中一大批铭文作家的地位也将被确认,中华个人创作的历史将被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这无疑将丰富先秦文学史的内容,为我们探索中华散文创作的源头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
由于私人叙事的偏向,利簋铭、天亡簋铭除了证实文献中关于伐商时间为甲子日之外,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武王如何伐商的细节,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是,这里正是史官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差别所在,凸显了私人叙事的侧重点所在。就这一点说,《利簋铭》和《天亡簋铭》的文学价值足以和她们的历史价值相媲美。
《利簋铭》、《天亡簋铭》的出现是西周铭文创作的“报春鸟”,在她们之后到周成王晚年,私人化的铭文写作层出不穷,今天有案可查的就多达五十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何尊铭》、《中方鼎铭》、《中甗铭》、《太保簋铭》、《士上尊铭》、《商卣铭》等精美篇章。这些铭文从私人视角反映了西周初年重大历史事件和士大夫政治、军事、宗教活动与个人生活感受,为中华私人写作第一次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1]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513-518.
[2]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 127-1 130.
[3]马银琴.两周诗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02-118.
[4]唐 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J].文物,1977,(8):8-9.
[5]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J].文物,1977,(8):10-12.
[6]张政烺.利簋释文[J].考古,1978,(1):58-59.
[7]白光琦.利簋的岁字不释岁星[J].文博,1996,(5):45-53.
[8]黄怀信.利簋铭文再认识[J].历史研究,1998,(6):159-162.
[9]黄盛璋: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J].文物,1978,(6):77-84.
[10]丁 进.周礼考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93-395.
[11]孙稚雏.天亡簋铭文汇释[C]//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166-180.
[12]孙作云.说“天亡簋”为武王伐商以前铜器[J].文物参考资料,1958,(1):12-16
[13]孙常叙.天亡簋问字疑年[J].吉林师大学报,1963,(1):25-58.
[14]唐 兰.朕簋[J].文物参考资料,1958,(9):69.
[15]于省吾.关于“天亡簋”铭文的几点论证[J].考古,1960,(8):35-36.
[16]刘晓东.天亡簋与武王东土度邑[J].考古与文物,1987,(1):92-95.
[1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中华书局,2004:33.
Rise of Private Writing:Bronze Inscriptions Creation on the Event of Overthrowing Shang Dynasty by King Wu
DING Jin
(School of Literature,Art and Media,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The Ligui Bronze Inscription”and“The Tianwanggui Bronze Inscription”are the first inscription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we can find nowadays.“The Ligui Bronze Inscription”recorded the great history of overthrowing the Shang dynasty by King Wu and reflected the transition state from the official narrative to private narrative.By recording the event of sacrificing to King Wen and the Gods twelve days after overthrowing the Shang dynasty,“The Tianwanggui Bronze Inscription”used three clues to narrate and adopted the lyrical and rhetoric means,which built a stereo narrative field and showed an obvious pursuit of writing art.The two inscriptions started Chinese private writing tradition.
The Ligui Bronze Inscription;The Tianwanggui Bronze Inscription;private narrative
I206.2
A
1008-3634(2012)01-0068-06
2011-10-1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51001)
丁 进(1962-),男,安徽青阳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