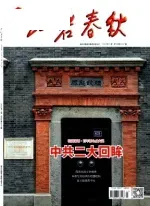康定建站迎空投
文◎杨克强 李 淼 口述 何瑞云 整理
康定建站迎空投
文◎杨克强 李 淼 口述 何瑞云 整理
艰难跋涉 进入康定
1950年初,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进藏部队,成都解放后不久,上级决定在成都市军管所会空军处组建康定空军站。这支新成立的队伍由站长张秉德,协理员王质宣,财务科长王巨波,留用人员工程师傅家瑶、肖人隽、王庭训以及报务员、机要员、后勤人员等几十个人组成。我们作为西南军区空军气象处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为了便于随62军186师直及556团进军西康,我们每人只带了空盒气压表、高度表、阿司曼、手携式风向风速器、常用表、电码本等仪器和有关书籍。
1950年2月7日,空军处在成都总府街明湘春饭店设宴,为康定空军站人员送行。下午,大家便随军出发,每人发了一匹马代步。当晚住簇桥,次日到新津,9号往邛崃,从10号开始边行军边剿匪。黑竹关、百丈、名山、金鸡岭,一路打着走着,2月13日到达雅安。
到雅安后,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周公山一带整日枪炮声不断,空军站人员与师直一起学藏语,学习民族政策。不久,雅安剿匪任务完结,部队即赴康定。站长张秉德、工程师肖人隽、气象员艾振寰等7人暂留雅安指挥空投。3月14日,成都空军处来电,空军站正式更名为“康定航空站”。
鉴于康定和平解放后又被匪军占领的紧急情况,3月19日,航空站人员与师直队伍一起立即离开雅安,进军康定。在紫竹关、滥池子,经过几道河、几座铁索桥时,我们都是把行李从马身上卸下来,人背着行李,两个人一前一后分别推牵着马过桥的。就这样,骑兵连副连长的坐骑还掉下了深涧,险恶异常。
22日晚,因要解放泸定,保住泸定桥,我们便马不停蹄连夜翻越二郎山向泸定进发。二郎山北坡当时无路可走,积雪很厚,前面一个排的战士扒雪开路,后面紧跟着向上爬。早晨6时,我们到达山顶干海子。二郎山南坡又是一片瀚沙,长满了像大树般的仙人掌,我们还得经此下山。经过一夜的爬山,人人疲惫不堪,深感“下山更比上山难”。下午3时许,我们终于赶到了泸定。稍事休息后,又途经冷竹关、扎里、烹坝等地,于3月24日赶到康定。匪军率300人逃向九龙。
支援部队 开始空投
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供应,从4月1日起,由康定邮局发电报,航空站安排人每日到城南机场值班,摆放丁字布,挂起风向筒,以随时迎接空投。后来,航空站在中央银行接受了一部100瓦的发电机,直接与空军支前基地新津机场联络。
自1950年3月康定解放后,因公路只通到雅安,后勤运输补给严重困难,西南军区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派飞机支援空投。装载着军用物资的飞机从川西新津县军用机场飞进康藏高原,第一关是康定山口,前面横亘着邛崃山、大雪山等海拔6000米以上的连绵雪峰,很难横越。因此,直到4月15日第5次试航,C-46大型军用运输机才终于顺着山峰峡谷,再度飞抵康定,并在视线良好的情形下,将空投品准确投下。
最初的两次空投,由于空投场在两个山头中间,峡谷很窄,飞机飞得很高,粮食又以大麻袋整仓投放,投下的粮食落在山上,粮袋撞碎后沿山坡滚下,浪费很大。经电报向新津机场建议,将粮食改为小包双层,飞机再飞低一点空投后,损失大为减少了。
为了支援18军进军西藏,4月4日,傅家瑶、王邦佑随部队去营官寨查看机场,并接管机场留存物资。5月8日,协理员王质宣带领全站人员出关,开赴营官寨。上级指示在营官寨一切事宜暂归18军指挥。于是,我们随骑兵连一起赴营官寨,经折多塘,过海拔5500多米的折多山,到山顶后下马走几步就气喘不止。我们第一天搭帐篷宿营折多山南脚下,第二天到达营官寨。
营官寨在康定属地折多山以西约70里处,地处贡嘎山侧,海拔3520米。那里有一区公所,汉藏杂居十几户人家,解放前修有一个简易迫降场。5月20日以后,我们就在迫降场北头开始简易观测,发报空投。5月27日,飞机来空投,却因找不到机场而返航。后来,我们利用驻新都桥18军先遣营(后改为兵站)的电台报话机,才与飞机联系上。6月3日,重新开始空投,第一天2架次,第二天3架次,为18军进军西藏的南路先头部队——开赴巴安(塘)的一个团队准备了给养。
7月21日,康藏公路已通至营官寨,并向前延伸,但泸定大桥尚未修好,汽车只能拆散后用橡皮船运过大渡河重新组装,故大量军需物资仍靠空投。记得最多的一次是8月10日,4架C-46大型运输机空投银元及棉衣等。
8月15日,气象报加密,由电台编发。航空站的十轮卡车载来了大功率电台及发报机器,电台队长、机务员给我们气象台带来了全套仪器。因当地野狼很多,夜间不便观测,我们就将百叶箱架在二楼平顶上。
8月底,电台队长吴占元到重庆开通信会议,回来时带来各种观测记录簿、报表、操作规范等。10月1日起,我们开始正式观测并记录,并从1951年元月起正式报送报表给新津机场。
自己动手 修建营房
进驻康定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保障都很困难。由于粮食供应不上,全站30多人曾3个多月未见大米,全靠去河里捕鱼作为主食,兼以山上采摘的野菜、野果等充饥。
我们的居住条件也很差,最初全部分散暂住在藏胞有限的空房内。后来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站上决定自己动手修建营房,计划建三层楼房和十多间平房,加上马厩,急需大量木料。
为了盖房用的木料,大家每天凌晨2点就起床,沿雅砻江支流立曲上游上行25公里,前往海拔3500米的东俄洛乡。那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我们腰缠皮绳,每人带一把利斧,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微明,即上山伐树。每人伐直径40厘米以上的树4棵,当天砍完放倒,第二天剃掉树冠,截成七八米的圆木,用皮绳捆成木筏,再砍一根5米以上的青冈树棒,作为撑杆,一人撑一筏,顺流而下。由于缺乏营养,又每天干着重体力劳动,有的鼻子出血,有的双手磨出血泡,有的嘴唇干裂,但为了支持进藏,人人干劲十足,都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途中经过50里的险滩激流时,会游泳的便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去放筏,不会游泳的就走旱路,帮助战友拿衣物。当时,我们上身穿棉军衣,下身穿内裤、打赤脚,每人只喝了几口酒就开始放筏了。如遇险滩,得下水推拉;如遇深潭,得脱棉衣,跳入江中,游着推筏前进。最怕的是在激流中木筏撞上石头,人就会因惯性一头栽入冰冷刺骨的激流中,虽然只有几秒时间,但待抓上筏子爬上来时,身上棉衣已结成硬冰,双臂撑筏时冰块嘎嘎作响,真有寒流刺骨之感。何况当时还高寒缺氧,腹中无粮。自然环境之恶劣,可称极限!
木料备好后,接着是烧石灰。这也要跋涉到远远的深山中去发掘石灰石,再就地建窑烧制,然后用背兜背回建房工地。
依照藏族习惯,建房用石头,得去河边、山脚漫山遍野地四处寻找。当时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全靠人背。我们的行为感动了藏胞,大多都会顺路帮助解放军背上几块石头才离去。
站里的老兵中,能人巧匠很多,有木工、电工、泥匠、铁匠,还有盖窑的。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一座三层、每层20间的楼房屹立在了机场跑道北侧,旁边还有十几间平房,形成一个漂亮的住宅大院。大门上方匾额是“劳动乐园”四个大字,门内木制影壁上彩绘着一张毛主席在盛大节日招手致意的巨幅画像。
1951年5月,在西藏宣告和平解放的大喜日子里,我们满怀豪情,在自己建起的大院中迎来了从北京来的贵宾——中央慰问团。我们还接待了中国气象学界的元老竺可桢教授,他是从北京出发,兴致勃勃去西藏做科学考察的。竺老此行,对他从70岁开始写、至83岁完稿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很有助益。
1952年10月,康定营官寨航空站完成了支援进藏空运空投的战斗使命,奉命撤销,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去。
62年前,康定县属西康省,是康藏高原上一座中等县城,也是从北路进藏的必经之地。当时,康定无航空站,飞机也就无法突破“空中禁区”进入西藏。今天的康定,已建起世界第二高海拔的民用机场,航班四飞,交通便利。然而,回想当年艰苦创业的情景和同甘共苦的军民关系,仍令人心潮难平……
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