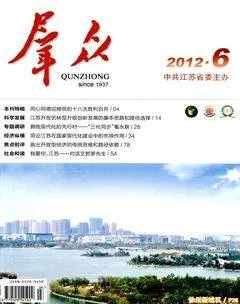论“八荣八耻”荣辱观的伦理创新意义
理
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八荣八耻”,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奸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要使其成为广大公民普遍的信仰,必须对它所具有的重大创新价值作更深入地探究。
“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体现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道德精神进步与发发展的大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个人利益的追求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和道德上的认可,于是出现了在道德与利益二者关系问题上的困惑(如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带来道德的退步),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是爬坡还是滑坡的争论。由于道德自身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兼之主流社会舆论的不懈宣传,人们对以无私奉献精神为特点的革命道德传统仍然无限地留恋。与此同时,人们又觉得个人的利益与幸福是行为选择的最终原动力,道德必须能够给人们带来真正可持续的利益满足和持久的幸福,否则它对人们就没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于是,近十几年来特别是自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发以来,我国的道德建设出现了两大全新的特点,其一是注重了道德的层次性,即将最高层次的道德要求与较低层次的道德要求相结合,并特别注重从低层次的道德要求做起,进而也悄悄地实现了由革命道德向生活道德的转换;其二是将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和社会建设有机结合,利用利益机制来推动道德进步,这不仅克服了道德教育上的唯意志论,也深刻地反映了道德的广泛深透性的特点。近年来,道德赏罚、道德回报等道德功利性评价成为道德舆论的主导陸话语。
经过这十几年创造性的道德建设,特别是社会用刚性的制度力量和物质利益手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道德的践行。然而,道德之为道德,它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律的道德生长的起点固然是他律,但他律只是低层次的道德和道德的不稳定存在,自律才是道德更高层次和更稳定的存在。制度力量和物质利益手段是实现道德他律向自律升华的重要力量,但他律性的道德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的道德存在。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做守德之人的必要性,守德是人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和重要内容。这种对道德的强烈自愿正是道德自律的表现,而自律的道德就是主体充分体悟到的和内化了的道德,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荣辱观。人们按照道德规则活动可能来自于两种不同的力量,从而显现两个不同的道德境界的层次:外在的压力(如物质利益的考量和制度性的赏罚)即他律性的道德行为和内在的动力(如良心)即自律性的道德行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升华。公民拥有更多的道德自决权是道德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荣辱观的提出正是顺应了公民对道德自我判断和选择能力提升的客观需要,是他律性道德向自律性道德发展的反映。
“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不再是以原来的外在于个体的社会视角和外在他律视角,而是从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内在自律的角度,强调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和自主能动性;不再仅仅是强调道德是社会向个体提出的约束和个体对道德的自觉遵守,而更强调个体对道德的內在自愿追求和道德对人生幸福生活的意义体验,
一、“八荣八耻”内容的层次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解读“八荣八耻”的时代意义时,还应当看到荣辱观的悄然演进。长期以来,我们遵循的是奉献型荣辱观,那是救亡图存特别是革命战争时期继承下来的荣辱观,虽然其精神价值具有永恒的导向意义,然而道德的生命力在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救亡图存的血雨腥风年代里,个人利益不仅是极其有限的(主要是最基本的存活需要),而且它与革命事业这一整体利益存在着“毛”与“皮”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任何一个革命者都能够深切地体验到的。那时,整体利益的至上性是每一个革命者行为的必然选择。只有为集体无私奉献,才能有个人存活的可能,换言之,为整体利益奋斗就等于是在为个人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
然而,在和平发展时期,个体的人有了日益增多的自我利益,社会也为个人谋取自我利益提供了法理的依据和情理的支持,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也出现了时空上的适度分离,二者“毛”与“皮”的关系逐渐变化为契约关系。前些年关于“真小人”与“伪君子”的争论从侧面反映了道德话语表达方式和道德价值观念必须与时俱进的要求。因为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合理地谋取个人利益是行为的主要动力源,那么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无法绝对地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入之道德化是入之社会化和人性化的必须,没有道德需要的人就不能称之为人,然而,上述道德要求又难以做到,于是,就必然会产生道德焦虑和道德伪善,后者即是“伪君子”。道德要求的至高互大正是“伪君子”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实,“真小人”也未必是道德恶棍,他可能只是过于强调了自我利益的目的性,与“伪君子”相比,他至少不虚伪,这正是人们反而能够宽容“真小人”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偏爱理想化标准,未能注重道德的层次性尤其是较低层次的道德,这使得较高层次的道德无以生根,也使不同层次的人无法进行适合自己的道德选择。“八荣八耻”以守法为底线,以服务人民为价值导向目标,呈现出不断递进的道德层次性,使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够作出适合自己的道德选择。它不仅规定了最高层次的“荣”的要求,也规定了最低层次的“耻”的内容;不仪服务人民是光荣的,而且守法也是光荣的。“荣”为人们提供了积极的价值导向,“耻”则为人们设定了底线和禁令,引导与禁止相辅相成。
三、“八荣八耻”充分彰显了人性的力量而具有普世意义
“八荣八耻”荣辱观重要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它将人为何要道德化的根据拓展到了人性。在传统儒家那里,耻不仅是重要的伦理范畴,而且成为人格的重要规定。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无荣耻之心者乃衣冠禽兽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习惯以耻感文化来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西方是罪感文化),由此可见,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说荣辱观作为个体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内在依据涉及到了敏感的人性,并以荣耻来界定人性,那么,“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伦理理论基础上便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即从人性、人的本质视角解读道德需要的根据,亦即《中庸》中的“仁者,人也”。长期以来,从人性谈道德被视为伦理禁区,仿佛涉及人性便是抽象人性论,即使讲人性,也多承认人性的阶级性和变化性(这样的人性最终也变成了不可捉摸的无意义之命题),不承认人性的共同性和相对恒定性。其实,既然道德是人所独有的,且唯有人才能真正成为道德的存在,特别是道德还是以内心信仰的方式充满情感因素地附着于人,那么,它怎么能与人性毫无关联呢?道德之能打动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人性力量。虽然人性不是万能的,但丧失了人性力量的道德生活则是苍白的。人陸是目前最能打动人的话语了,汶川地震时“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的话语感动了多少人啊!共产党是最现实的人道主义者,他讲阶级性,但也讲人性,党性、阶级性和亲情本质上是一致的。“八荣八耻”里的话语大多是全民性的和人类共同的话语,其共同的理论基础便是人类共有美好人性。
总之,“八荣八耻”因为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注重了层次性内容和使用了全民性话语,必将成为大众化的道德,进而成为全体公民共有的道德信仰追求。口
(作者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