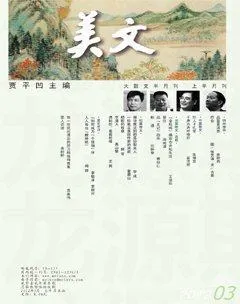李满天
尧山壁
1939年6月16日生于河北隆尧,1962年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任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6年起任河北省作协主席,河北大学教授,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已出版诗歌散文四十余部,散文《母亲的河》《理发的悲喜剧》《石头的生命》《陶醉壶口》入选语文课本。
在近代文学典型人物画廊中,白毛女是最具光彩的形象之一。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登上世界各国的舞台和银幕。但是问起谁是第一个创造了白毛女这个典型人物,大部分人回答会不正确。正确答案是河北作家李满天。
这位李满天也不是等闲之辈。原名李涓丙,曾用名林漫,叫得顺口,开玩笑时叫“林副主席”。1914年生于甘肃临洮一个普通农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组织一二·九游行示威。1938年赴延安,鲁艺文学系二期班长。1944年深入敌后,任晋察冀边区政府教育科长,兼晋察冀日报记者。1942年在盂平县采访时,听到了一个故事。佃农聪明美丽的女儿被地主看上,利用逼债抢霸去,强奸后欲杀人灭口。女孩在女仆的帮助下,逃进天桂山,躲在山洞里,生下一个女婴。由于长期不见阳光和缺乏食盐,头发变白,直到八路军来了,才重见天日。
林漫捕捉到这个题材,多方搜集资料,采访了几十名群众,反复修改,写成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白毛女人》。1944年任应县宣传部部长时,托交通员到延安亲手交给老领导周扬。那一天正是中秋节,周扬看到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个故事既有宣传作用,又有教育意义。新旧社会两重天,适合改变成歌剧,为党的“七大”献礼。任务交给鲁艺音乐系主任张庚。一稿由邵子南执笔,邵子南是个诗人,在晋察冀工作过。写成后,彩排五场,大家认为诗的风格较重,舞台效果不理想。二稿交由贺敬之、丁毅操刀,年仅二十岁的贺敬之,自身有父亲遭逼债去世,弟弟夭折的痛苦经历,奋笔疾书,八天交卷。张鲁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基调,谱出了《北风那个吹》等名段,女主角由唐县人王昆扮演,黄世仁由宁晋人陈强扮演,都是河北人。
1947年林漫随军南下,曾任应山县区委书记、军分区宣传民运科长,鄂豫报副总编,新华社湖北分社总编辑,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先后出版过小说《苦根记》《哑巴讲话》《家庭》《绊脚石》等。1952年申请回河北深入生活,一头扎进定县西建阳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完成了长篇小说《水向东流》三部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全国宣传,可惜迟了一步,风头被柳青的《创业史》抢去了。
后来,林漫把关系转到河北,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1961年参加了整风整社,恢复短篇小说创作,两年写出了《穆桂英当干部》《杨老恒根深叶茂》等九篇作品,带动河北作家掀起一个短篇小说创作高潮。以李满天、康濯、张庆田、刘真为主将的《河北文学》,与以柳青、王汶石、杜鹏程为阵容的《延河》并驾齐驱,形成全国两个短篇小说创作中心。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满天的短篇小说集《力原》,受到了茅盾先生特别关注,应邀参加了1964年大连小说座谈会。周扬当众把林漫介绍给大家:“他就是白毛女故事的写作者,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你们要记住,不能忘了。”周扬对此念念不忘,早在1952年北京一次会上,谈到电影《白毛女》的成功,就特别指出歌剧《白毛女》是根据林漫提供的小说改写的。大连会议备受推崇的作家首先是赵树理,其次是李满天。当然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林漫一直把赵树理当做学习楷模,开口闭口是老赵。在河北带出来一支“山药蛋派”。“文革”后,山西“山药蛋派”因为外来知青作家崛起,日渐退化,而河北的“山药蛋”还是丰收,比如保定的赵新,被称作赵树理的真传“小老赵”。人说“山药蛋”从山西移到了(太行)山东。
大连会议结束不久,就遭到政治嗅觉灵敏者们的公开批判,罪名是“宣扬中间人物论”。帽子扣在会议主持者、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头上。“文革”开始升级为“大连黑会”,林漫作为“大连黑会”的“黑干将”,被河北当局首先抛出来,当做批斗的靶子。省文联机关揪斗大会,革委会坐一排,“黑帮”站一溜。“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多,与群众大体上是一比一。造反派让群众给“黑帮”挂牌子,牌子上人名打了黑×,打红×就该枪毙了。分给我的任务是林漫,他们知道我俩关系好。看着牌子上的“反革命分子”与慈眉善目的林漫怎么也对不上号,出手时心慌意乱,眼一闭,结果挂在了另一个人的头上,引起哄堂大笑。会后我就被打入另册,名目是“修正主义苗子”。
机关批斗,林漫没有大受皮肉之苦,他不像田间那样认死理,常常顺杆爬,光棍不吃眼前亏。问:“交代《穆桂英当干部》的黑心!”答:“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穆桂英是谁?”“彭德怀”。我暗暗捏了一把汗,劝他注意后果,他说:“老运动员了,积三十年经验,摸着了运动规律。开始敲山震虎,有枣没枣打三竿,末了甄别,赔礼道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儿戏,陪着玩吧。”造反派文化不高,看不透林漫,还以为态度好呢。在唐庄劳改农场,林漫表现好,调到厂部喂猪,摆脱了残酷斗争。我去看地,床头两本书,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一本《猪的饲养》,都翻旧了,给猪看病,也给人看病,工宣队员有个头疼脑热,也去找他。林漫深有体会地说:“人性不如猪性,猪吃饱了睡觉,人吃饱了整人”。
1970年冬天,我被分配到临西县插队落户,工宣队不容分说,把城市户口也注销了,这意味着从此便一生一世成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林漫来送行,看我不愉快说:“知足了吧,农民就有了公民权,总算熬到出头之日了。不像我们,连当农民的资格都没有,属地主富农一类的。”
林漫好像有话要说,平时阳光灿烂的脸阴沉下来,要下雨的样子。说是经过好多天的思考才向我提出的。家属在昌黎当农民,三个孩子,如今工资减到30元,养活不起,求我在临西找一户人家收养他一个孩子,更名改姓,永不见面都行。他抽泣着说完,我哽咽着听完,泪眼相望。一个大作家、高级干部竟然落魄到这种地步。
林漫的妻子李茵我见过,一位聪明贤惠的女人,老家山西浑源,17岁参加革命,当过村妇救会主任,婚后随军南下,一直是国家干部,正科级。三年困难时,动员15%城市职工,为国家担担子,下放到农村去,一般阻力不大,正如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哪里艰苦哪安家。”文联知识分子成堆,心眼多,没人报名,党组会开了半天,沉默不语。林漫是个红脸汉,站起来说:“党的任务要完成,我不上天堂谁上天堂。(不好说地狱二字)我想了想,我是行政十一级,工资一百八九十元,能养活她娘儿四个,换成一般干部,五六十元,拉家带口就难办了。”一阵掌声,四朵红花,把娘儿几个送到昌黎县。昌黎在燕山脚下,渤海之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鱼米之乡,花果之乡。
人间的事就是这样,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林漫的老婆孩子果真下了地狱。李茵虽然挣不了多少工分,还可以交钱买口粮,渐渐没了怨言,反正她一生都是为了丈夫活着,万万没有想到赶上“文化大革命”。老乡首先起来造她这个外乡人的反,抄这个大作家的家。也令乡亲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林漫的家除了铺板之外,就是半屋子书刊,一根火柴就烧成了一个穷光蛋。直到1973年落实政策,李满天恢复原职,李茵也结束了十二年寒窑生活,回到了丈夫身边。
庆祝粉碎“四人帮”,省直举办文艺晚会,机关选送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林漫的《改造二流子》,延安时期的独角戏;一个是我三岁半女儿的童谣,祖孙两代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年轻时心气高,想先立业后成家,突如其来的文革使美梦破灭,睁眼已到“小子过了二十五,衣裳破了没人补”的境地,匆匆找了个对象,还撞了个好运,十分满意。可是天下大乱,人心惶惶,我俩决定不办喜事了,愁有千万,喜从何来?两头瞒着,回老家就说在外地办了,回机关就说在老家办了,不想瞒不过林漫的眼睛。在唐家胡同摆了一桌酒席,为我们祝贺。1968年儿子出生,林漫被劫持到天津一宫,正处在“砸二黑”的风暴眼里,不曾得知。1972年女儿出生,林漫在唐庄干校,特意拍来一份电报祝贺,一时传为佳话。迁居石门,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女儿经常出没在李爷爷的臂弯膝下。
林漫生就一个老农,城里住不惯,乡下为家。到正定县深入生活。正定有个作家贾大山,两人经常一起光着膀子干活。对阳光的反映,林漫是黑,身上一层黑釉,戏称黑非洲;贾大山是红,脸上一色紫红,自称印第安。幽默是两位乡土作家的共同特性,碰到一起就笑话连篇。林漫说起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贾大山是慢条斯理,不温不火,活像是说相声。我也常去凑热闹。一度习近平任县委书记,吕玉兰副书记,聘请一批顾问,工农科技之外,还有黄绮和我,每月一次咨询会,还发车马费。大会之后分头到对口部门,我就去找林漫和贾大山,正事之后常常唱两口。我和贾大山都写过剧本,也都是票友。贾大山比我专业,县城戏园子熏陶的,我是农村戏台子学的,林漫不会京剧用秦腔。《打渔杀家》大山的萧恩,我的桂英,林漫的丁郎。《沙家浜》一个叼德一,一个阿庆嫂,一个胡传魁。林漫官大,还得唱配角。
好日子没过几天,林漫又撞上厄运,还是他自找的。1980年编辑部李克灵写了短篇小说《省委第一书记》,题材是废除终身制,老干部让贤。《河北文艺》要刊发,报请宣传部。领导让文艺处拿意见。文艺处说,题材新颖,立意较好,问题是对第一书记描写不大真实,有对老干部厌弃之嫌。领导不同意发,作者转投《鸭绿江》发了,同期还发表了一篇《普通劳动者》,主题相同,地委第一书记让贤。后来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是橘生淮北则为枳,河北的文艺处主管处长为此被养病,文艺组进入多事之秋。省里还发了一个红头文件,通报全省,要内部处理李克灵和李剑下放廊坊当工人。
这事本来与林漫无关,他可以在正定县埋头劳动,还可以与贾大山调侃生活。但是事不由人,一种什么力量,扯着他的耳朵回头看——他个人还有很多人的脚印。1957年反右前夕,本来安排梁斌领导运动,老兄写完《红旗谱》,严重神经衰弱、高血压,大把的吃药,支撑不了,求助林漫代劳,没经心爽快地答应了,进了五人小组,没当组长,但是脱不了责任。文联文化厅打了那么多“右派分子”,《蜜蜂》编辑部还有戏曲工作室,几乎全军覆没。他也提过不少反对意见,但是无济于事,最后不举手也不行。这些同志被打进了地狱,一待就是二十二年。他常常自责,也找过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诉说心灵的痛苦。远千里比他还软弱,提起来刘艺亭、王思奇他们就掉泪,感叹:“是灰就比土热啊!”
林漫坐不住了,党组会上讲道理,找领导反映意见,对文学作品和学术问题要与政治区别开来,尤其对青年人要冷处理,不可一棍子打死,汲取以往血的教训。两年前在机关大会上,他受良心责备,掏心窝子检查,对受冤枉的同志鞠躬道歉,当众发誓今生今世再不整人了。这件事成为他的一种心病,苦口婆心地讲,最后讲到党代会上。有人听着不爱听,还以势压人,扣帽子。林漫据理力争,说不畏权势。领导责问何许人也,查一下。偏偏林漫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辫子可抓。林漫知道了,说要这样,工作怎么干。领导说就是这样,你打辞职报告。林漫在火头上,提笔就写,领导也在火头上,拿来就批。打电话给人事处长常庚西,马上给他办手续,阳历年前办完。说是辞职与撤职也差不多,那一年林漫68岁,按现在也到了离休年龄了。可是三十年前,还是领导干部终身制,七老八十照样稳坐官位,还没有离休一说,何况林漫还是行政十一级高干。为有牺牲多壮志,林漫振臂一呼,引起社会反响,防止问题闹大,两个青年作家免去一劫,没有下放当工人。林漫辞职了,很多人来慰问,更加受到人们敬重,平时的幽默也好,这次的悲壮也罢,都是他性情正直和善良的表现,正如黄宗羲所说:血气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气不可无。
林漫在正定几年,写了几个短篇小说,《美气的日子》《炉火纯青》《诊脉辩证》,“文革”乱世后气定神闲,笔意老到。我知道他正在着手一个鸿篇巨制,要塑造一个敬业爱民,实事求是,敢开顶风船的地委书记的形象,内中有原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影子,可是船开不久就被搁浅了。
林漫不能再到正定,跟贾大山摽着膀子干活了,住到了省医院,哮喘、吸氧。曾几何时,他还晒得和铁人一样,在我们面前显示他的体能,踢腿时脚尖过肩,弯腰时掌心贴地。才几天就变了一个人,头发胡子都白了。上北大中文系时饿得肺病又犯了,发展成肺心病。中医所指的心,包括心也包括神经系统。几十年一帆风顺,这场打击经受不起,病来如山倒,免疫系统崩溃,心肺痹塞。
林漫人缘好,探望者络绎不绝,人们眼前的原“林副主席”还是一个乐天派,照常开玩笑,但是没有了力气,笑不出来了。每次看见我,他都艰难地伸出手来,好像有话要说,像十年前送我去插队落户那样。张张嘴,又咽下去了。那一次他去送我,现在我要送他,到更远的地方去。临终前两天,终于说出来,放心不下李茵,更对不起李茵。没了我就没了收入,这可叫她怎么活呀!
是呀,以后李茵怎么活呀。当初下放为国家担担子,家中的担子由林漫一个人担。没了林漫,谁来为她担呢。从前大会小会请林漫不止一次地说作家是苦命人,引用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而今不光他一个人命苦,连累老婆孩子也都成了苦命人。三年困难精简下放问题,别的单位都解决了,李茵解决不了。当年下放是因为林漫,今天落实政策轮不到她头上,也是为了林漫,林漫的现在。解决不了的理由是她当年自愿报名,试问历次运动挨整的人,哪个不是以自愿的形式出现,反右派反右倾,不都是本人也得签名画押了吗?这块心病林漫是带进棺材去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山人海,一半是为林漫,一半是为李茵。贾大山说了句令人心酸的笑话:创作了《白毛女》的人,他就是个白毛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