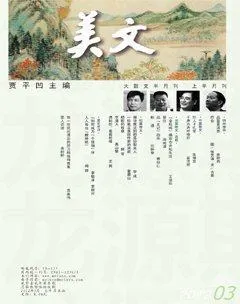据说我见到的是孙犁夫人
李 成
安徽桐城人,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中学时代开始发表作品,部分作品由《散文选刊》《新华文摘》转载或被收入《中国新诗年鉴》《星星诗刊50年作品精选》等选本。现在新华出版社供职。
最近有一段空闲,我接连几个晚上翻阅了孙犁先生晚年的几本集子,對老人晚年的一段情感经历尤为关注,因为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见过一位女士,听人说她是孙犁的夫人。
孙犁對自己的情感生活并不十分避讳,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有散文,也有小说。其实小说也基本上是纪实,正如章无忌、郭志刚在他们所著的《孙犁传》里说:“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幻觉》这篇小说,他写的不是‘幻觉’,是真事,甚至包括细节。”孙犁自己之所以以《幻觉》即小说的形式来写这段感情,无疑是怕写得比较细、比较尖锐,對当事人有什么刺激或伤害吧。
孙犁在散文、小说中写到这位女士时,只以其姓“张”称之。孙犁与这位张女士是自他“赋悼亡”即原配妻子去世约半年后的1970年10月起,经一位“北京的老朋友”搭桥,开始通信联系的。看来孙犁對这位女士一开始就很有好感,所以至翌年8月,孙犁就给她写了一百二十多封信,也就是说,三天左右,他们就有一次通信,这确实可以称作是条“热线”。尤其是對于孙犁这样一位即将年届花甲的老人来说,可谓是爆发了火热的激情,殊为难得。
虽然他们的结合有一定的阻力,但是老人还是毅然克服了一切困难,与张女士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将张女士从江西调到天津某区的文化馆。为了联系工作,孙犁不顾年高体弱,风尘仆仆和张女士回到他的家乡安平县,甚至在县招待所里还因遭冷遇,受了一肚子气。但是,结合以后,家庭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美好,他们之间几乎很快就有了裂隙,我想,其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两人的经历、背景、个性、学养乃至思想意识确实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就要说到我印象中的这位“张”女士了——如果真的如人所说,她是(或者说曾经是)孙犁的夫人的话。
我见到这位张女士是在1982年。那一年的春天,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我们县也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召集全县的写作爱好者共商如何“繁荣我县的文艺创作”,我作为一名初中生有幸应邀与会。报到后,在第一次集会上,我就见到在一群灰头土脸的人当中,有一位容颜端庄、仪表不俗的中年女士坐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上,她微带笑意,始终安静而认真地听着大家发言。也没有人介绍她是谁,但是凭我的直觉就知道,她应该不是本地人,她如果不是上面来的一位领导,也是一位“大知识分子”,很可能是来自省城的。会开了一两个小时,她都坐在那里没有动,毫无倦容,始终對大家的发言保持关注与兴趣。这让我心生敬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到了吃饭的时候,与会者都三五成群向餐厅涌去,独有她与县里的一两位领导以及会议的主持者站在院子里,抱着双臂,以一种自然而安详的神态看着大家,显得是那样的沉静、娴雅。我从会场出来后,也在院子里停留了一会儿,这就得以近距离悄悄地打量她。只见她身材比较高大,脸庞浑圆饱满,肤色白皙而有光泽;头发挽起,似乎还梳着一个罗髻,因到中年,体型略显丰满、富态,总之一看就令人感受到一种比较明显的“高贵”气质,其仪表,其风度,让少年的我不自觉地想起宋庆龄那样一些不凡的女性,当然她还不及宋之完美、漂亮;也有点像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出生在我们县的新月派著名作家方令孺——面貌端庄、大气,眉宇间自有一种奕奕的神采,不管在哪里都会显得卓尔不群。我瞅准机会悄悄问走过身边的我县著名诗人陈所巨她是谁,陈老师告诉我:“听说她是孙犁的夫人,叫张X贞。”我略有些惊讶,因为我那时已读过孙犁的小说集《村歌》等作品,在我的印象里,孙犁是与革命战争,与农村土地联系在一起的,有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家,没想到,他的夫人这么“现代”,也这么好看,一看就知出身很不一般,起码是生长在城市的,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女性。
记不得是当天下午还是第二天,我们这次座谈会又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在这次会上,主持会议的陈所巨一开始就介绍这位张女士,说她是我们省的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来参加我们这个会的,现在就请她讲话。张女士也没有推辞,略一沉吟,就讲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县是个出文人的地方,自古就出了许多诗人、画家、作家,而且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散文流派,现代也产生了一些著名作家、教授、学者、艺术家。我们要向前人学习,继承和发扬这一文化传统,但是仅此还不够,还要深入民间,向身边的老百姓学习,学习他们生动的鲜活的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把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云云,说的当然都很正确。但我记得,她的声音尤其悦耳动听。
这次会议结束后,还有一次聚餐,我有幸随陈所巨老师跟这位张女士同在一桌,席间,陈老师还向她介绍到我,说我还是个初中生,她听后微笑颔首,似乎还说了一两句嘉许和鼓励的话。
这位张女士给我的印象就这么多,以后也再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当然也不能确证她是否真的是孙犁夫人,更没有听说她为何与孙犁先生离异,又为何千里迢迢从天津调来我们省的出版社工作。
其实,我见到这位张女士时,孙犁的几篇可能涉及她的小说、散文俱已发表,可惜我那时没有机会读到。现在,我从孙犁的文字里约略得知,这位张女士在动乱年代曾流落江西,原来是一位大校的妻子。为人可能比较豪爽,善于交际,长于周旋。孙犁拿到她的照片,一见倾心,通了几封信后,即给她汇去几百元钱。孙犁后来自嘲:“这些年,我其他无长进,唯物观念是加强了。”(《续弦》)但他们之间的裂隙也正是从物质、经济开始的,孙犁用他的文字记载了他们婚后生活中这样一番對话: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我有些开玩笑地问。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我说。
“不對,你应该有三万。”
她说出的这个数字,是如此准确无误,使我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有未卜先知之术。
实际上,“文革”一来,孙犁已将大部分稿费上交了国库。但是,“这位女士不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孙犁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里,几天就花完了。他们之间的“不协调”由此生发。我想,这主要还是由于两人性格差异太大。这位女士或许素来大手大脚惯了,长袖善舞,而孙犁呢,经过早年那么艰难的岁月,当然知道“一丝一粥来之不易”,不肯轻易花费一个子儿。如果他们的性格能改变一点,尤其是在對待家庭财务问题上都“中庸”一点,稍稍接近一些,或许他们的婚姻生活要长一些也未可知,那么,晚年孙犁的生活或许也就不至于那么的寂寞乃至显得有些枯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相情愿。
这位“张同志”似乎也想“启发”孙犁。
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能毁家纾难吗?”
我说:“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
她叹了口气,说:“你使我失望。”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對话。但一听就知道这位“张女士”问错人了,她是把孙犁想象成了一位江湖或者战场上的英雄,而且在平时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位英雄。从我所见的这位“张女士”(假设她真的是孙犁的夫人)来看,她与孙犁根本就是两种类型的人,两股道上跑的火车,硬拧到一起,不出问题也怪,这样看来,他们后来分手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孙犁后来与他的传记作者谈到这件事,说他后来的“妻子”离他而去,他也可以理解——到了1975年,孙犁的处境还未见好转,并说他写这几篇涉及她的文字,也无“恶意”。今天我读到这段往事,觉得如果说有什么可惜的地方,那就是孙犁一气之下,将他给她所写的、装订成五册的一百二十多篇书信付之一炬,不然,我们还真是可以读到中国文坛上的另一部《两地书》。
这一举动也恰恰反映孙犁先生当初是真的动了感情的。
我写此一篇拙文,也无“恶意”,更不是发人“隐私”,而是因为少年时代曾经见过这么一个人,并多少在心中引起一种仰慕,我只是写出我的感受,最多只是为了求证,另外,也是表达我對前人前辈感情生活的体会,表达我對人生的认识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