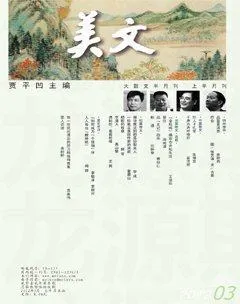千声万声呼唤你
崔济哲
学者,作家,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走近黑色世界》《旧曲新歌》《清唱》《风从天上来》等作品集。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改革开放30年散文选》等。作品多篇获奖,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介绍到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
我去三姐家看望母亲,一进门,看见老太太正对着立柜的穿衣镜打量着自己,看的是那么认真,那么仔细,脸上浮着一层恬淡的微笑。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几乎没有一根黑发。根根白发都是银光闪闪,见过母亲的人都会对母亲的一头白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白,是银白,白得像春天乍开的满园杏花,又像秋天怒放的一池芦花。 母亲80多岁了,脸上的老人斑越来越多了,皮肤松弛地下垂着,两眼也不像从前那样有神了,常常呆望着窗外像在回忆那逝去的年华,又常常呆坐着,别人不拉她起来不叫她,她就像一尊雕塑几乎一动不动。渐渐地,母亲的话也越来越少,常常是自言自语,有时候她会很亲切地对你说几句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她老人家在说什么,细细品起来方知,母亲似乎在讲五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而且掐头去尾,问得人莫名其妙,她还微笑地望着你,等着你回答,你答不出来她也不着急,静静地望着你笑,一会儿她会把一切都忘了。她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会很认真地问:“谁从树上摘下来的?给你爸爸吃的?洗干净就不用削皮了,有维生素。” 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
母亲后来就谁都不认识了,连和她一起生活的三姐她也叫不出名字来,也不知道她是谁。你真不认识我三姐了吗? 母亲拉着我的手,我轻轻抚摸着她皮肤皱起青筋突暴的手问她。母亲看着我,又看看三姐,再看看全屋的人说:“怎么会不认识呢?”字正腔圆,北京话略带些她江苏砀山老家话的尾音。我问那她叫什么呢?母亲似乎也很纳闷,她又反反复复地把周围的人看了一遍,只是重复着我的话,那她叫什么呢?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很严重了,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老太太还认识我,只认识我。姐指着我问她我是谁,母亲爱抚地轻轻摸着我的脸,脸贴脸地看着我,说:“是我儿子。”姐又问她那他叫什么,母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笑起来,嘴里念念叨叨着不知在说什么,好像又是特别遥远的事情。我听见她说十三陵劳动,母亲参加过修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我听她讲过,她们如何睡草棚,打赤脚,拉车担土,半斤重的大馒头,一顿能吃三四个。 但那都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事了,母亲怎么会突然想起那些事呢?正在我们惊愕期间,母亲用手指刮着我的鼻子竟然响亮地叫出了我的乳名,我觉得心头一热,再也憋不住了,凄凄惨惨地叫了声妈,抱着她老人家忘情地哭了起来……
母亲从小待我如掌上明珠,真是托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口里怕化了,因为我前面是三位姐姐,母亲时时刻刻牵挂着我,母亲是怎么教育我的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那泡童子尿,那泡尿在教室里的尿。多少年以后,母亲和人说起来还笑得前仰后合。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国家号召扫盲,母亲就当起夜校扫盲班的教员,每天晚上义务为工人开班上课,母亲不放心我就把我带在身边。记得那时候敲钟上课后,先唱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得翻江倒海似的,把那间老屋梁上的尘土都震得刷刷地往下落,我常常用手堵着耳朵,露出一脸惊讶来。那时候工人们只听党的话,别说干活不惜力,舍出命地出力,就是唱歌也是放开喉咙,可着嗓子唱,谁都怕自己声音小了,听不见了,谁都想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内心的感情,哪有光张嘴不出声假唱的?
夜校就不那么正经,教室就是一座破旧的库房,桌子板凳都是七拼八凑的,墙上挂一块黑板,母亲对着写在黑板上的字,一遍一遍地教。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虽然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但仍然是那么漂亮。 穿着一件双排扣的列宁装,长长的大辫子盘在头上,教起课来一丝不苟。 我呢,就在一边玩,从墙缝里扪蚂蚁,看小飞蛾撞电灯,瞧那擦起的粉笔末怎么又轻轻地落下,在母亲黝黑的盘发上落下一层淡淡的灰白。母亲告诉我只要你不出声不出教室干什么都行。一直相安无事,渐渐地,我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有一次我让尿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可母亲拿着她那根破木棍教的正起劲,我“急”了几次她都不理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那间破教室的墙角撒了一泡尿,憋急了,尿得挺响,滋得挺远。教室里轰然大笑,笑声朗朗,像开课前唱歌一样,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无拘无束无保留地哈哈大笑起来。母亲扭过头来看见我的窘样也禁不住扔下教鞭笑起来,好在那教室墙角尽漏缝,地又是土地,尿上去就只留下淡淡的一幅地图。但笑声却不止,好像一浪高过了一浪,我也纳闷,难道他们就没被尿憋过?就没尿过尿吗?小孩子家真不懂了。直到大家都笑够了,不前仰后合了,直到母亲又捡起那根破木棍来,教室里才安静下来。 我还记得清楚,母亲在黑板上重新写了几个字,然后拿木棍一指,示意大家都跟着她念:“尿,尿尿的尿。”大家又哄堂大笑,随后跟着母亲念,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尿,尿尿的尿。”母亲又趁机把“汗”“水”“流”都教了。 也真奇怪,若干年后,那些扫盲班里的学生在送母亲上调去北京时,还提起陈老师教的“尿”字,别的字忘了不少,但“尿”字记得真是刻骨铭心啊。我那时已懂得不好意思了,赶快走开。
母亲高兴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吹口哨,口哨吹得圆滑流畅,水灵脆亮。60年代初,刚刚熬过节粮度荒的日子,母亲脸上也渐渐有了喜色。有一天母亲让我到烧锅炉的工地借一辆三轮车,我问干什么? 她十分神秘又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三轮车借来后,母亲从家里拿来细扫帚和掸衣服的仙佛掸子!先用扫帚把三轮上的煤渣和灰尘扫干净,又用仙佛掸子掸了好几遍,又从家里抱来一领旧线毯子,然后高兴地坐在平板三轮上像骑在高头大马锦衣还乡的状元。 路上母亲憋不住了,悄悄地告诉我,是去东大桥关东店买一台缝纫机。母亲那高兴劲就别提了,那年月家里添台缝纫机可不是小事,可比现在买辆汽车还震动。6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所有人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裤子褂子,有缝纫机的人家把膝盖处、屁股上的补丁缝补得像军用地图上的标高线,一圈套一圈,大圈罩小圈,穿上都觉得神气。 但更多的人家是用手缝补丁,我就看见母亲在灯下戴着顶针给我们缝补衣服,似乎是让针在穿过衣物时走得更顺畅些,还不时地用针在头发深处梳篦一下。但手缝出来的补丁一是不结实,二主要看上去不美、不派、不神气。那年月补丁里也有学问啊。 现在要买缝纫机啦,一是标志着母亲可以从顶针和一针一线中解放出来了,二是我们家的孩子们都可以在补丁序列中跨入一个高级的序列了,让同学们眼馋羡慕去吧。
我听见母亲坐在板车上高兴地吹起口哨来。 母亲吹的是电影《马路天使》中的插曲,我不会唱不熟悉。我一边蹬着三轮一边回头说:“妈,您吹个我也会唱的。”哨声戛然而止,好像给母亲出了道难题,我突然想起她教夜校时的开课歌不就是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吗?母亲高兴地说对,就吹这首夜校的校歌。母亲的口哨随风传出去很远,像小提琴,像二胡,更像笛子、黑管,那么优美,那么动听……
姥姥是小脚,还是挂着大清龙旗时代裹的脚。 姥姥洗脚后割脚垫时我看见畸形的脚指被强扭着别曲在脚心,像被捆绑在受刑柱上的无辜者。我问姥姥,妈妈为什么没裹脚? 和母亲同一年龄段的阿姨们很多都是“解放脚”,先裹后放。
母亲有一双很健康很漂亮的“天足”,30年代她曾获得华北高校女子80米栏第一名,100米自由泳第三名,姥姥意味深长地说,因为你妈妈聪明,因为她聪明才逃过那一劫。中国女人受苦受罪受歧视的最后一劫:裹小脚。
母亲在他们陈家大排列是十四,在家族中称十四姐,她是我外祖父的大女儿。外祖父赶上大清王朝冉冉西坠的落日,做过几天穿补子戴顶子坐绿呢轿的官,但官不大,估计就是个县教育局或文化局的一个官。家中文人墨客不少,母亲小时候先读的是私塾。 姥姥说,有一次外祖父的一位上司来视察教育,顺路到家中小息,外祖父非常重视这位大人,姥姥说倒不是因为他官居多大,外祖父说他学问大。看见家中有私塾,有琅琅的读书声,就把七八个小孩叫到跟前,老先生也喜欢孩子。 难免一问一答,答对了还有嘉赏。问到母亲时,难免让母亲背两首唐诗,床前明月光之类的。 母亲那时很调皮,从不怕人,外祖父也娇惯她。她连背两首诗,在座的七八位老者都面有不解之状,不知母亲背的是什么。不懂!听不明白。老先生微微皱着眉,不得不让母亲再背一遍,母亲天真调皮恶作剧地笑着,不背了。谁让你们听不懂?外祖父又哄又吓,教书先生也尴尬地催促,母亲极不情愿地背诵了一遍,原来就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众人都长释一口气。到底是那位老先生学问深,突然念了一句谁都没听明白的话:“间云白上远河黄。”在众人瞠目结舌之际,只有他和母亲相视而笑。老先生说,她读的、念的、听的诗词何止万千,但从未见过哪位读书郎能够倒背唐诗。姥姥说其实你妈妈调皮,闹着玩,她从来没有下工夫念过一天书,全凭脑子好,记性强。母亲事后对外祖父说她从来没倒背过,看那位老先生捻着胡子像听戏似的晃着头,她觉得忒好玩,就开了个玩笑。老先生连声叫笔墨摆上,给母亲题下两个大字:心灵。
外祖父大喜,发下话,母亲不再裹脚,十四姐不能就这么待在陈家府,以后还要去北京、上海,不能迈着一双小脚走路。
85岁时,母亲完全痴呆了,她站在穿衣镜前会很有礼貌地对着镜中人说,您是谁?为什么站在这里?难道您不累吗?坐下来吧,给您削苹果吃。我问三姐,像老太太这么聪明,智商这么高的人为什么会老年痴呆呢?三姐说,她读过一本美国杂志说越是小时候聪明的人,老了就越容易得老年痴呆症,比如像美国前总统里根……我打断她的话说,现在家里都挖空心思不惜一切代价要生一个天下最聪明的孩子,培养成天下最聪明的才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难道都是为了造就一批老年痴呆症吗?三姐说,你跟我急什么?这老年痴呆症跟魔鬼厄运似的,谁知道降落到谁身上?它还管你是聪明你是傻瓜啊?母亲扭过头来,不再微笑了,很严肃地问我们,是街道家属居委会的吧?我们报过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