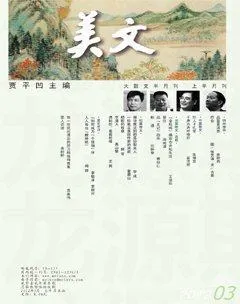作业
十
1982年,78班面临毕业。广西电影制片厂来要人,北京生源何群、咸阳生源张艺谋、杭州生源萧风、新疆生源张军钊分配去了广西。
这在当年的出路中,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最不好的一个去向。当时广西厂要了十一个人,最后定了七个人,其中几个一开始就没打算去,跑了,学校根本找不到人。剩下四个人没什么主意,凑一块儿商量。他们有强烈的流放感。四个人拿着地图找南宁,何群嚷嚷起来,再迈一步就到越南了!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安排工作,户口、档案,一切都带到分配地。这四个人如果不去,张艺谋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户口吊销,没有正规单位,没人理没人睬,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拍上电影。商量来商量去,没什么准主意。张艺谋是老大哥,其他三人表态:艺谋,只要你去,我们就去。
“也许我的宿命感影响了其他几个人,我觉得去就去吧,虽然是个边远的电影厂。先去,在逆境中求生存。”张艺谋说。他在逆境中过惯了,总觉得不管多难,只要你扛住,有你的个人意志和坚持,总有一天老天能看到你的努力,给你一线生机。当然,关键也在于,他们和学校几乎没有什么谈判余地,张艺谋问过学校,能不能去潇湘电影制片厂,吴子牛、张黎他们几个去那儿,也拉过他一起去。学校一口回绝:不可能。
这三个人中最不平的就是何群。78班的同学都叫他何爷。何爷心地纯良、脾气爆裂,“文革”中家庭受到很大冲击,从小游走江湖,同学都叫他愤青。何群是皇城根儿底下长大的,这次远走广西,极度愤怒和沮丧。张艺谋的认命倾向影响了大家,何爷的愤怒情绪也感染了其他三个人。
“其实我原本倒没什么愤怒。我自己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多少次头发丝儿细的可能性抓住才到了今天。家里我这一辈儿中,我是唯一的大学生。我已经很知足了。但是何爷那么愤怒,其他三个人也跟着愤怒起来。团伙的互相感染有滚雪球效应,更何况我们四个那么抱团。后来我们跟厂里要独立拍片的权力,跟当时的情绪都有关系。要不然,我一个人可没那么大胆儿。”张艺谋说。
虽然现在回过头来说,广西厂引进了几个大学生,也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会,开风气之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这才让这几个刚毕业的学生成为同学中第一批直接掌镜的摄影师和导演。不过在决定之初,不会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知道自己远走蛮荒,离开北京这个文化中心,内心无比失落。在拍《一个和八个》时,其中变形的强烈的表现精神,跟这种愤怒和失落不无关系。
张艺谋只做了半部电影的副摄影,四个人和电影厂磨,最终得到了支持,开始拍摄《一个和八个》。张军钊是导演,张艺谋和萧风联合摄影,何群是美工。年轻人第一次拍片,除了斗志之外,更大的特色是,告别过去,颠覆传统。
《一个和八个》摄影风格奠定了它的特殊意义,黑白灰的主调,不完整构图,带有硬照的构图强化色彩。明明卡好了构图,非得扭一下,歪一下,让画面和传统的完整画面不一样。“其实《黄土地》也是一样,虽然在摄影阐述中,我引经据典,搞得自己好像有点文化修养的样子,其实包装了半天,就一个意思:怎么不一样怎么来,标新立异。”张艺谋说。
萧风岁数小一点,比较谦让,跟张艺谋站在一块。何爷就不用说了,老愤青,就喜欢玩造型。导演张军钊,受了四年的导演训练,觉得电影还是要刻画人物,表达情感,不应该那么强调形式,不过三个同学态度如此斩钉截铁,道理如此掷地有声,四个人又那么抱团儿,后来也顺着仨同学走了。张艺谋说:“应该说,我们三个胁迫了张军钊,诱惑了张军钊。被我们仨搞造型的一搅和,张军钊那点儿导演的东西基本冲没了。”
技术的限制,也造成了摄影对风格有很大控制空间。那时候并没有监视器,导演一般蹲在摄影机三脚架底下,根据摄影师摇镜头的位置挪动身体,通过目视揣测拍摄效果。一段戏结束,导演一般抬头问摄影:“怎么样?”摄影说过了就过了。张艺谋和萧风眼睛堵着摄影机取景孔,除了他俩谁也看不见拍了什么。
拍了一个阶段,第一次看片,演员炸了,不演了,要求开会。《一个和八个》的演员现在都已经是大演员,陈道明、陶泽如、谢园、赵小锐。大家很愤怒,电影拍了半天,放出来一看,光线黑不说,很难看到一张演员完整的脸,要么是半拉肩膀,要么是一只眼睛,还有的酝酿了半天感情,表演得也相当投入,最后只看到一只耳朵。
“会议的火药味很浓,也很民主,很公平。每个人站起来发言,演员对我们这种只讲造型的方式强烈不满。我们也很坚决,特地找了周传基老师的录音放给大家听。周传基老师是声音专家,他所说的不完整构图里的画外空间,是由声音而至电影美学,不是针对我们讲的,也未必是我们这一套,但是我们自己就觉得我们跟人家的理论是一套!”张艺谋说。
搬出周传基,于他们而言,打架找到了靠山,吵架找到了帮手,这三个玩造型的,不仅忽悠了导演,还绑架了毫不知情的周传基。
青年摄制组刚刚成立,是当时全国平均年龄最小的摄制组,大家都想做出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加上四个血气方刚的正牌大学毕业生,言之凿凿,态度坚定,最后就拐带着、裹挟着大家往形式主义的路子拍下去。
张艺谋现在还记得《一个和八个》的艺术指导郭宝昌郭爷对电影的评价,他写信给导演张军钊说,“本片的摄影构图严重抢戏”。张艺谋后来觉得,郭爷说得中肯。为了造型,演员表演想把脸扭来对准镜头,摄影师坚决不同意:“背过去背过去!不拍脸!好了,站住,不要动!”张艺谋学着当时的口吻,惟妙惟肖。他和萧风要拍大广角,照大背影,弄个广阔空间一人独立的感觉。“这确实是严重抢戏,干扰演员对人物的刻画,对情感的表达,对演员很不尊重。放在今天,哪个摄影这么拍,绝对得把他炒了。”张艺谋说。他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成长轨迹,也许言下之意是,现在如果他的摄影这么拍就不行,但是他们当时这么拍有着自己的背景和合理性。
《一个和八个》出来之后没有过审,张艺谋说,一个是主题边缘,一个是形式夸张。在电影学院小放映厅放给同学们观摩。师弟师妹们听说片子好像要被毙,蜂拥而至。影片结束出字幕,张艺谋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摄影:张艺谋 萧风。“我岁数大,排第一个。”张艺谋说,“我浑身汗毛都立起来。激动,强自镇定,不露。”
全场掌声雷动,那是张艺谋第一次听到参与影片的直接反馈,不是礼貌性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掌声,他说:“我很幸福”。每次听到掌声,看到你周围的观众看你的眼神,那种热忱、赞赏和亲近,都会如同第一次听到和看到一般感动,觉得自己的努力有无价的回报。张艺谋笑笑说:“只是不是每一部都能听到。”
那是在1983年,距离他们毕业仅一年。
大家的反应出乎张艺谋几个人的意料,这部片子当时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受到了批判,但在文艺评论界却获得了一致的高度赞誉。张艺谋觉得,当时百废待兴,文艺界对于新的东西的呼唤很强烈。《一个和八个》作为年轻人的第一部作品,又赶上被毙,大家对此的一份不满,转为对这部电影的支持。所以文艺界对“破晓”的第一批作品,态度的基调就是肯定,词儿捡大的说,把这拨年轻人的创作上纲上线,高度评价,认为是石破天惊的作品。第五代的雏形就有了,到了《黄土地》,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几部电影都带有强烈的挑战意味。
今天看,这两个作品的故事和主题都落套,很传统,最重要的还是造型带来的叛逆姿态。这种姿态是这批人的成长经历和特殊情绪所致,但是它和当时社会所呼唤的离经叛道遥相呼应。
张艺谋说:“大家高看了我们,高度评价了我们。今天看第五代作品,幼稚粗糙的地方很多。那时候没有商业这一块,电影只谈两样:艺术和政治。评论界在这两点上,把第五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放得很大,是整个时代的需求,所以成就了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以我们的功力和当年作品的力量,不是说的那么好。”
张艺谋承认,这是现在回头看的想法,当年获得众多赞誉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自鸣得意的,只是不显:“想到掌声,想到别人的眼神,想到别人的赞美之词很兴奋。包括《红高粱》得奖,脑子是蒙的,悄悄地高兴,出去还是很谦虚——不是装谦虚,是我们那代人所受的教育。现在呢?这篇儿早翻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标准比别人要苛刻得多,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一个人对突然降临的抬举和荣耀没有准备,也许会忘了自己是谁,也许在高兴之余,忍不住怀疑自己的作品能否承住如此的关注和赞赏——张艺谋大概属于后者。他所说的自鸣得意,也不过是这个意思吧。
在当年需要英雄的时候,一种不妥协的、创新的、不管不顾的姿态获得了超出应得的肯定,之后,张艺谋成为批评的焦点,动辄得咎,也是因为在风口浪尖上,时代也需要对成气候者的讨伐,这大概同样是无需征得个人同意的、磅礴的、焦虑的需求。一誉一弹,来自同一炮口,区别不过是,放的是礼花,或者炮弹。
十 一
张艺谋给人普遍的感觉是,比较土、不时尚、不讲究、脸部棱角分明,像是脸长成之后,又拿刮刀修过,冷、硬。他和高仓健有一些轮廓和神采上的相似,但在高仓健这里,就是酷,是爷们儿,到了他那儿,就是苦,是营养不良。当年吴天明看中这张脸,才用他演了《老井》中的男主角孙旺泉,那是1987年。第二年,他便拍了第一部独立导演的《红高粱》,代表作,赢得了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电影大奖。
也许是他作为男主角的旺泉形象实在神形兼备深入人心,也许是他的前几部作品对准的都是中国农村,他在电影中运用的色彩浓烈、热艳、张狂,加上他在镜头前很少精心修饰,很少谈笑风生,强化了他的“农民印象”。
商业片《英雄》之后,影像的华丽、精致,并没有扭转人们对他的印象,《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中色调倾向半点没有减弱,这回不是农民,改暴发户了——比农民还不如。
1968年到1971年,张艺谋在北倪村插队三年。相比同代人,他插队的地方离家不算远,时间更不算长。他自嘲:“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现在的张艺谋在穿着上是比较讲究的,他的衣服色调较暗,面料精致,颜色层次搭配看似不经心,清越有风致,毕竟这么多年的影像训练,他轻易能找到适合的风格。这些很难在镜头前面看到。唯一有点不拘小节痕迹的,也是因为他说话时会动不动站起来,抡开了比划、扮演,有时候动作幅度太大,他习惯性地要时不时把宽松的裤子往上提提,于是就能不断看到他坐下,站起,提裤子;坐下,站起,提裤子。循环往复。
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知识分子,不少了解他的人也知道,张艺谋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就算知道这些,不少人也很难觉得他有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背景。
1997年,张艺谋还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导演歌剧《图兰朵》,父亲去世。张艺谋没来得及赶回来。在此之前,父亲跟张艺谋说过多次,要把家族故事告诉他,至少需要两周的时间,要细说。母亲跟父亲商量,老大时间紧,要不就说两天?父亲很坚持,家族故事很重要,细节很多,两天说不完。张艺谋是个不能停的人,别说两周,就是两天也得咬牙。“我们这代人受到的教育,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每天有很多事在做,根本不会在家待十几天听我父亲讲故事。”
母亲做了很多努力,让父亲写下来,但老父坚持要亲自跟老大说,也许他早已做好了面对儿子讲述的准备,其他的方式,都更间接。对老人来说,亲口对儿子讲述家族历史,可能既是一个心愿,也是一种仪式,就算在他身体每况愈下来日无多之时,他都坚持等着这一天。可惜这个庞大、复杂的故事,被父亲带进了坟墓。张艺谋说:“我对不起我父亲。”
父亲见缝插针跟张艺谋说的故事,被他一点点串起来,他现在所知道的,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拼图,可惜这拼图中的细节,已经彻底丢失。这段故事中最重要的物证,还是照片。
张艺谋的祖籍在陕西临潼田市镇,那里出兵马俑,陈凯歌在那篇流传很广的《秦国人》里,说张艺谋长得就跟兵马俑一样。他的爷爷,大致也是这个模样。
张艺谋的爷爷是临潼的大户,父亲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说爷爷家当年就是这样,只大不小。爷爷是老燕京毕业生,私立大学,家里没底子上不起。爷爷有报国之志,后来到了陕西柞水县当县长。柞水匪患甚烈,民众不堪其扰。爷爷打算剿匪,那时候政府没钱,爷爷回到田市镇,从家里拿了大洋买枪,装备了一个县剿匪队。
做文人的爷爷实在低估了剿匪的难度,枪买了,土匪抢先一步收买了剿匪武装,行动彻底失败,队伍土崩瓦解。张艺谋跟评书演员似的总结道:“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更坏的结果是,爷爷购买的枪暴露了他的家底,知道他家里有钱,土匪一路追杀。爷爷县长也不做了,落荒而逃,跑回临潼。土匪随后赶到,把家里大院儿给围上,要好几担大洋赎围。家里拿不出这些钱,土匪一把火烧了院子。
爷爷家就此衰败,人跑的跑散的散。爷爷捡回一条命,带着家小隐姓埋名跑到西安,开药铺为生。人到了西安,听说土匪还时不时在临潼找他。
剿匪不成,连累家人,这段经历刺激了爷爷。他觉悟“生逢乱世,家里没有拿枪的不行”,把三个儿子都送到黄埔军校。大伯是黄埔九期,二伯是黄埔十五期。张艺谋的父亲排行老三。
黄埔毕业之后都要带兵打仗,奶奶想留一个在身边,于是张艺谋的父亲做了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军需官。国民党溃退台湾之后,父亲和奶奶留了下来,根据解放初期的肃反政策,军需、军医等技术人员可以留用。正是奶奶的坚持、父亲的孝顺,保住了家,也才有了张艺谋。
大伯一家1948年去了台湾,从此音信杳然,直到1981年,才辗转跟家里取得联系。
二伯从黄埔毕业后,和一批同学一起被蒋介石派到胡宗南部。胡宗南对他们很忌惮,弄了个军官团,把这帮人养起来,不给带兵。这群人报国无门,成天闲得发疯,很痛苦。延安缺少军事干部,听说了之后,派人过来策反。胡宗南部队流传两句话:老蒋不要老毛要,老胡不用老朱用。策反到二伯的头上,他很动心,打算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他只是跟母亲说,要和一个朋友一起出差。没想到,从此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父亲千方百计在军队内部动用各种关系打听。这件事怎么也打听不出来,很神秘。有些人肯定了解发生过什么,就是不说。
1949年,二伯的一个好朋友,姑且称之为张三,拿一包东西到奶奶家,说是你们家老二的东西,放下东西就走了。奶奶打开包裹,里面是二伯贴身穿的衣服和零星的个人用品。奶奶一看,浑身发凉,可能人已经完了。等跑到街上去追张三,早已没有张三的踪影。
张三跟二伯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年曾经寄存过一只箱子在家里,以前没人会去动别人的箱子,现在二伯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而张三是唯一的线索,顾不得那么多了,父亲撬开了箱子。箱子里的东西都是些普通衣物,只有一张合影照片,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大家只辨认出,张三在其中。
父亲拿着这张照片在军队系统内问,有人认出了这张照片,是军统培训班某一期某一班的合影留念。大家这才知道,张三是军统的。父亲根据这条线索,顺着蛛丝马迹,一个人破解二哥失踪之谜。最终捋出了大致经过:二伯和几个朋友,包括这个张三,打算投奔延安,不过最后一刻,二伯一群人被张三出卖。胡宗南把人抓起来,不好处置,给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半信半疑,置而不论。直到1949年,国民党军队政府一片大乱,也顾不上了,二伯和其他人最终被枪决。
父亲探查出真相的过程可能非常艰辛,里面有很多故事。“可惜我听不到了。”张艺谋说。
在台湾的大伯一家和奶奶断了联系,大伯觉得,母亲和弟弟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直到1981年,大伯得知他们还在,激动得难以自抑。大伯很小心,怕给母亲添麻烦,从台湾托人到美国,转了一大圈,给母亲寄来了一张家庭合影。在断了音信几十年之后,张艺谋的奶奶在91岁高龄,收到了大儿子的一张六寸全家福。
“我现在还记得,奶奶家的小桌,上面铺着塑料布,奶奶就在桌前,灯光底下,戴着老花镜,一遍遍看照片,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张艺谋说,“照片的四周都被摸黄了,摸黑了,卷起来了,奶奶还看,还掉泪。”
照片背面在每个人的位置上,标注:“长子某某,长媳某某……”母亲提醒张艺谋,在他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巷口,向远处张望。他们都知道,奶奶在等人。三个儿子,一个去了台湾,一个失踪,生死不明,老人的残年,只指望着能见两个儿子一面——二哥已经被枪决的事,张艺谋的父亲一直没敢跟老人提起。
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和弟弟在隔绝了40年之后重新见面,可惜他的母亲已经等不了,于几年前去世。大伯带着一家给母亲上坟,快80岁的老人,跪在坟前,哭倒在尘埃里。“家里人让我看上坟时的录像,谁看谁掉泪。”张艺谋说。
张艺谋去台湾看望大伯,父亲特地到荣宝斋买了几只毛笔,他记得大哥爱写字。又把张艺谋叫到一边,神秘地拿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张印在石头上的黑白底片,是张艺谋大伯的戎装照。
母亲大惊,“文革”中家里经历过多次抄家,这么危险的东西父亲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连母亲也不知道。不要说像他们这样历史背景复杂的家庭,就算普通家庭中搜出这么个东西,也可能会带来很大麻烦。
张艺谋到了台湾大伯家,台北小巷里很普通的一家人。张艺谋拿出父亲给的纸包,里三层外三层拆开,露出里面的石头底片。大伯一看生气了:“他留着这个干什么?!这有用吗?!不就是一张照片吗……”他责怪弟弟。
军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是不同的。藏着一方哥哥的照片,瞒着世界上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母亲、妻子、孩子。冒天大的风险,张艺谋的父亲也许并没有什么奢望,就为有了它,他就不是一个人撑着,至少还有个兄长。
哥哥当然知道,但他更后怕。
张艺谋问起大伯1948年是怎么到的台湾,大伯讲的故事更为传奇。
国民党撤离1183513901817b574f9ef9780b492770c8fa5612eb21556ee1df52e63a4115cd大陆前夕,大伯接受了一项命令,留在大陆打游击,他需要找白崇禧要50挺机枪。当时一片大乱,白崇禧也不大听蒋介石的命令。大伯老实,在白崇禧那里待下来,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正在此时,遇见了黄埔同学,同学告诉他,先别忙这些,学着别人把家眷送到台湾去。大伯这才找关系带着家眷到了台湾。
安置完家眷,他觉得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又返回大陆。人到了上海,白崇禧找不到了,他也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土崩瓦解,正发愁怎么办,遇见了他的另一位黄埔的同学,是炮舰的舰长。同学说,别想着完成什么任务了,搭我的炮舰回台湾去。
炮舰到了基隆港,几天靠不了岸。当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陈诚,负责对撤台的所有军人集中管训。岸上布满了宪兵,大喇叭里滚动播着:“来台的军人们,请将随身携带的枪支武器交给上船的宪兵,然后依次下船接受安排。”上岸官兵必须先缴械,按照规划重新编队,港口拥堵非常严重。
舰长见老同学着急,想了个办法。那时候只有厨师和采购可以上岸采办,舰长建议大伯换身衣裳,冒充采购。临走,舰长不放心,自己也换了身衣裳,护送老同学上岸,“送佛送到西”,上了岸他才能放心。
上岸不久,身后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接着发生了连环爆炸,正是同学那艘舰的弹药库发生事故引发的。一个舰的人全完了。两个人痴痴呆呆看了半天,恍惚不知身之所至。
大伯说,后来舰长扑通一声给他跪下:“老同学,你救了我。”
张艺谋说:“后来我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有很多感触。故事不一样,感受是相似的。战争、历史、天各一方、生离死别,对每个家庭带来的长久的痛苦,长久的压抑和悲伤,都是共同的。”
今天再说起这些,听起来就像传奇故事,对于亲历者来说,比如张艺谋的奶奶,一辈子唯恐自己的身份会影响孩子的父亲,惴惴不安的姑姑,是最结实不过的创楚。“我都已经算隔了一层了。”张艺谋说。
也许张艺谋有一天会拍出类似题材的电影,如同他用《我的父亲母亲》遥遥表达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一样,他的这些感受可能会因为一个剧本的触发奔泻而出,形成另一段影像。
十 二
张艺谋陆续在几大重要电影节上抱奖而归,媒体、评论人习惯性地为他勾画成功轨迹,他很快被描述成一个如何从小就有远大抱负,不甘命运摆弄,每一步都计算好了的深沉的成功者。到了对几部商业片口诛笔伐之后,逻辑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结论从深沉、胸怀大志,变成了功利、投机取巧。
张艺谋说:“人是要有梦想的,不过我也在想,什么是梦想。我总觉得,梦想是很入世、很具体、很现实的,梦想是你在某一个生存阶段,可以做点什么改善自己的状况,梦想是最切实的想法,它不能在天边,因为那无法作用和影响你的行为。”他从不承认自己有机心。
刚进工厂,张艺谋被分到前纺营二连做辅助工。当时全国向解放军学习,工厂的称呼也模仿军队。那是棉纺厂的第二道工序,大棉花包来了之后,先到清花车间去初步清洗,之后就到前纺车间“梳棉”。“梳棉,俗称弹棉花。”张艺谋仰着头,努力想出一个别人能理解的词儿。
一个棉花包大的有一吨多,小的有几百公斤,外面是包皮布,用八号铁丝捆着。在清花车间初步清理之后,到前纺车间要对棉花杂质进一步清洁,一分钟一千多转的钢针,对棉花做物理舒张。张艺谋所做的辅助工,具体的工作是抄车。每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棉花的杂质会糊满钢针,就需要抄车工清洗。这个工作很危险,一不小心,手指头就会被钢针拔去半截,剩下白森森的指骨在外头。
车间里潮湿、噪音大,非常脏。张艺谋的另一个工作是掏地道,车间的地下有巨大的吸尘装置,每过一段时间就得下去清理。戴三层口罩下去,出来之后最里面那层都是黑的。
每过半个小时左右,张艺谋有机会可以出来透口气,夜里看看星星。别的工友在抽烟、聊天,他就在那个时候背诗词。如同他借的其他摄影书一样,诗词都是借书来抄在笔记本上。
体力活儿,三班倒,尤其上夜班,很受罪。张艺谋说:“我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去工会做个宣传干事。如果不行,去工艺室也好。再不行,去机动车间也好,至少人家可以上长白班。”理想是分层的,不能实现最高一层,那就从最低一层努力起,能到哪儿是哪儿。如果一时都实现不了,至少还能被借调出去打个球,拍个照,做个展览。如果没人借,待在车间,就给自己找点儿事儿,比如背背唐诗宋词。一个班八个小时,能歇个十回八回的,就可以背十回八回的诗词。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一个干了一天脏得只看得见眼白的工人,背诗可能改变不了什么,我就想,多学一点,艺不压身,总是好的吧。”张艺谋说。他对诗词没有什么偏好,手抄本里面既有软玉温香,也有金戈铁马。大学时候不看诗词了,看刘勰的《文心雕龙》,“我觉得写得很好,后来写摄影阐述的时候抽冷子引用一下,显得自己有点文化”。
张艺谋从国棉八厂走的时候,已经实现了第二高级的梦想,调进织袜车间工艺室,只不过是借调,一直没有办正式手续,还算编外。“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张艺谋的父亲只跟他正式谈过一次话。他和父亲之间一直话少,父亲很严厉,张艺谋有点怕他。张艺谋刚上初中二年级,有一回表姐在家哭,后来知道,表姐被分到一个街道工厂工作。表姐的成绩一向优秀,比张艺谋还好,家庭背景让她上不了大学。也许因为这个缘由,父亲想起来问张艺谋,有没有想过将来做什么,要不要上大学。
“我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家庭的问题,但是我早就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的家庭背景是有问题的。”张艺谋说。他内向,对环境敏感。有一次从床底下翻出来一枚青天白日的徽章,奶奶看见了,一把打过去,脸变了颜色。“我就知道我家和这枚徽章有点关系,直到今天,我看见徽章心里还会一拧。”
上小学时张艺谋成绩很好,也是少先队,上了初中,全班同学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按道理,他应该也是第一批入团。那时候入团入党会做外调。班主任石长钢老师把张艺谋叫到办公室,跟他谈话。大体的意思是,出身不能选择,但是道路可以选择,要接受组织长期的考验。没有人提不能入团的事,但是十分钟以后,张艺谋已经明白了,他入不了团。
父亲在“文革”前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怕孩子们有负担。只有一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孩子们都得填各种表。表里面有“家庭成分”一栏,别人都填“贫农”、“中农”,张艺谋不知道怎么填,拿回家。从小学到初二,父母背着孩子们商量怎么填。“我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隐隐觉得我们家一定是有一些难言之隐。”张艺谋说。
父母曾经填过“城市贫民”,老师不认,没这么填的,到底是贫农雇农中农,还是地主资本家,要说清楚。张艺谋很尴尬。后来又填过“城市居民”,一度又填成“职员”。最困难的还是父母的“政治面貌”。父亲很为难,填“曾加入国民党”,这是个铁打的事实,由不得向组织撒谎。后来又填过“曾集体加入国民党”,好像加了“集体”俩字,罪过会轻一些。母亲填“共青团员”,后面加个括弧,“已退”。父亲是板上钉钉的国民党了,母亲琢磨写上自己先进的过去,觉得也许能掰回来点儿。他们不想因为家庭的原因,给孩子的未来添麻烦。当然,这些想当然的努力,实际上也没什么用。
张艺谋观察到的一切,从来不跟家里人提起,他也从来不问。加上表姐的事,他早就认定,完全不可能上大学。
他回答父亲,不打算上大学,要考中技。父亲脸上有难以掩饰的失望。他不知道张艺谋为什么连考大学的心都没有,说了不少话,做了不少工作。张艺谋没有改口,他坚持说,中技好考。
“我一直有自知之明。根本上不了,又何必去提呢?”张艺谋说。父子之间的这场对话很有意思,父亲对儿子的了解,并不如儿子对父亲多。张艺谋没法解释,也没想过解释真实的缘由。即使说出来又如何?父母加倍小心不让孩子们知道,说破了徒惹伤心。
上个中技,出来进工厂,这就是十三四岁的张艺谋的想法。
“人的梦想在不同的阶段是会变的,就因为梦想很现实。1960年,我的梦想就是白面馒头,上学梦想家庭成分能不能填得好看一点,进工厂梦想轻松一点,”张艺谋说,“而我父亲的梦想,就是把双料反革命变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张艺谋收到北京电影学院允许他入学的信之后,声名大噪。父亲的担心一直没有放下,如果因为他的缘故,张艺谋上不了大学,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带着张艺谋去陕西省人事厅,敲开一个人事干部的门。“以我父亲那种身份,当年又不停为二哥失踪的事写申诉,人家当然认识他,老残渣余孽了嘛。”张艺谋说。父亲很客气,跟人家说起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想请人考虑一下,把自己的问题定性给改一改。“你知道政工干部的那副嘴脸,看都不看他,说,去去去,组织定的东西能随便改吗?门直接在我们面前关上了。”跟轰苍蝇似的。
“我从来不做无谓的空想。”张艺谋说。进了工厂之后,有人发动他申请入团,他一点没上心。那时候工人阶级队伍里头党团员很多,一车间800号人,有600多都是党团员,一遇到停电,工厂就要组织学习,最常说的就是“党团员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留下来,其他人可以走了。”全车间就张艺谋一个人走。后来人家也没那么多废话,直接说:“张艺谋,你可以走了。”到最后,有人一出声,要组织学习,根本不用提名字,张艺谋特自觉就拿着饭盒走了。
“我心里不觉得别扭。我就这么个家庭出身,得知道自己是谁。我出来要么背诗词,要么骑个破自行车出去拍照片。我觉得挺好。”张艺谋说。
方希
出版业者。现居北京。
天高(1980)
这是张艺谋大学二年级的摄影作品,也受到了四月影会拍摄手法不拘一格的影响。照片中地平线的处理故意不在黄金分割线上。后来《黄土地》的拍摄风格跟它一脉相承。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1980)
这张静物摄影也是请美术系同学李庚捏的小人儿。放到洗相片的盘子里,倒上墨汁儿,撒上盐。在背后做了个黑纸,放大后大部分做黑,剪个月亮放上面。
也许张艺谋实在喜欢这两句诗的意境,又做了个同主题高调的静物摄影。蓑笠翁的道具沿用,只是背景变成了白色。
局部光效(1980)
这是摄影系的作业之一。标准的局部光效的作业,也就是一个石膏像,要对光源做一定遮挡,让一溜光打到某个位置,比如眼睛,其他地方光线较暗。张艺谋在这张照片上遵循了局部光效的要求,但是努力做得不同凡响,背后的墙上是典型科学意味的标记。虽然它依然带有一点学生腔,和其他同学的灯光作业相比,从技术和表现手法上还是高出一截。
觅(反转)(1981)
这张照片实际拍摄于1980年,地点在北京圆明园,模特是同班同学王雁,不过制作是在1981年。
它是在底片上做二次曝光反转。冲洗底片冲到一半时,闪一下白,再凭经验,是闪完马上定影,还是停个三五秒再定影。为了得到适合做反转的底片,张艺谋在同一构图上连拍三张,拍摄至少三组。这样将底片放在暗袋里估计着下剪子,肯定有一张是好的。三组就会有三次机会得到合适的底片。反转也可以用相纸,但是得不到图片上看到的这些勾边的小细线儿。
这张照片的难度主要在暗房技术,当然,也在于摄影的时候设想好简约的构图,并且在构图中还有材料可以实现反转的勾边效果。在张艺谋的同学中,大家都知道反转的道理,但是极少有人试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