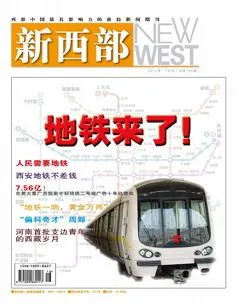“偏科奇才”周郢
周兢老先生今年已81岁高龄,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由于常年给孩子们讲故事,被誉为“故事大王”。这是他写儿子的一篇文章,读来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最近一段时期,报章杂志有关“泰山学”专家周郢的介绍、报道颇多,文章中往往不约而同地都提到一个“谜”字,如《谜一样的周郢》、《泰山文化的揭秘者》、《力破泰山谜》等等。日本学者小仓芳彦教授也在与周郢著作的序言中写道:“这样小小年纪,如何获得如此广博的知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谜……”
作为只有初中学历的周郢,涉足于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锲而不舍而且成果丰硕,这种超出常规的“成长”,似乎真是一个“谜”;在“成果”中,他揭开了泰山学中许多“悬案”与疑点,澄清史实,论证确凿,似乎更是一个“谜”。特别是在他苦战八年,悉心研讨,完成60万字的《泰山志校证》之后,又先后登上“大众讲坛”、北大讲堂、国图讲坛乃至国外讲学,为“中华国山”而诠释呼吁,引起了更多人士的兴趣和关注。为此也就有了一些说法,什么“天才”、“奇才”、“怪才”和“神童”也频频而来,更造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周郢。
我从事青少年教育专业,研究过青少年的成长规律,我始终认为,周郢应是一个“平凡人”、“普通人”,我作为一个周郢成长、成才的“知情人”,还应该谈谈“由头”,谈谈起因,做一些真正的“揭秘”。
小周郢是班里的“差生”,不过,语文、历史、地理学得都不错,还在作文竞赛中夺得过“金牌”(奖章),挂在胸前回来向舅舅炫耀。但他对数学、外语等课,却味同嚼蜡,课本下放着童话、故事书,为此常被老师逮个正着,被拎着耳朵拉到教室外罚站。
孩提时代的周郢,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任何区别,贪玩、爱动,甚至调皮、捣蛋,一个十足的“小顽童”。他精力特别旺盛,过度的“动”,让姥姥终日担心,叫苦不迭,甚至怀疑孩子是否患有“多动症”。而“症状”的逐步减弱与消失,源于“听故事”。周郢的舅舅虽然是个工人,但生长于书香之家,读书极多,肚子里装了不少从书里学来的故事;周郢的父亲,是全国知名的“故事大王”,又从事少儿工作,两人一商量,决定用“故事”引导孩子的兴趣,而爱听故事又是儿童的天性,所以周郢像其他学龄前的小朋友一样,在咿呀学语时即接受了“故事”的熏陶,他爱听故事,凡名人自学故事、历史故事、童话、民间故事他都爱听:听了之后,大人就鼓励他“复述”和“创编”;口述锻炼了他的口语表达,而“创编”则诱发他的创造思维。在大人的鼓励下,他把“构思”的故事讲出来,虽然“编”得不合逻辑,甚至胡编乱造,舅舅一概加以表扬和鼓励。并且指着外公高高的书架告诉他:“故事全在书里,长大了你可以看书,书里全是好听的故事……”舅舅的话常使小周郢遐想神往,他瞅着一摞摞的书往往久久发呆……
周郢的父母都是文化人,均在陕西汉中工作。当时生活拮据,不得不把孩子寄养在山东泰安的姥姥家。外公是泰山学专家,曾在大学教古典文学,舅舅是个“书迷”,也是一位业余作者,双方家境一般,但都存书如山,家人凑到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文学、戏剧、诗词,来家做客的亲友,也多为文艺界中人,这种“书香”浓郁的氛围,也让坐在小板凳上“旁听”的周郢受到熏染。
看到周郢的这些“征象”,父亲与周郢的外公、舅舅商量,决定以“读书”引导,舅舅响应最为积极,他工资不高,但买书从不吝啬。根据小外甥的年龄段,先买有字有画的故事书,继而跑旧书摊、废品店去搜罗“文革”前的连环画,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汉演义》、《东周列国志》他都买到了。果然,这些书有“制动”作用,周郢玩闹的“节奏”减弱了,他一个人,一本本地反复看,画看得懂,文字认不得,舅舅就给他念、讲。周郢没上过幼儿园,但“小人书”、“画书”,却让他识了不少字。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上小学后,周郢识字多了,读书的兴趣更浓了,读小说往往向大人提问许多“为什么”,舅舅就千方百计为他寻找《上下五千年》和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他自己也翻看外公和母亲的书,举凡四大名著,蔡东藩的通俗演义,《中国戏剧史》他都读,尽管是囫囵吞枣,但他都读得津津有味,甚至可以背诵《红楼梦》中的大段诗词。
但小周郢是班里的“差生”,不过,语文、历史、地理学得都不错,还在作文竞赛中夺得过“金牌”(奖章),挂在胸前回来向舅舅炫耀。但他对数学、外语等课,却味同嚼蜡,课本下放着童话、故事书,为此常被老师逮个正着,被拎着耳朵拉到教室外罚站。
按照当前的教育“标准”,周郢是个典型的“后进生”,初中阶段,文理两科严重分化。许多老师为周郢千方百计“纠偏”,但效果甚微,于是老师们发出了“此子不可教也”的喟叹!但父亲认为,“偏科”并不可怕,怕的是科科平庸,更怕是一无所长。
周郢从小就对历史具有很浓厚的兴趣,举凡唐史、宋史、明史、清史,甚至《史记》他都硬啃一气。一次父亲考他,他一气背诵了从三皇五帝到清代的朝代接续,甚至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均能说上个大致不差。11岁时,他读了《中国戏剧史》——“脸谱白兰陵王始”,他对照“田单大摆火牛阵”有油彩涂面一节,把“脸谱起源”问题向从事戏剧工作的母亲提出质疑。《中国戏剧史》是权威专家的论著,母亲无法解答。不知天高地厚的周郢,竟然写了“作文”,径自投向了一家权威性的专业杂志——《戏曲艺术》。这就是发表于1982年第一期上的那篇不足300字的“作文”——《脸谱形式不是从兰陵王开始》。主编陈培仲先生加了编者按,赞赏了这名“少先队员”的探索精神。
第一次见到“铅字”的兴奋,让周郢更爱上了历史,随即萌生了“著书梦”、“专家梦”……钟爱小外甥的舅舅更是投其所好,除了将外公的文学书、善本书,大量提供给小外甥之外,他还不惜血本地搞“智力投资”,省吃俭用,为其购买各种文史书和工具书,历年累计达万余册。周郢很少吃零食,给的零花钱、压岁钱,全用在逛书店买书上了。
按照当前的教育“标准”,周郢是个典型的“后进生”,初中阶段,文、史、地占绝对优势,但数、理、化,可说是一塌糊涂,文理两科严重分化。许多老师为了纠正周郢的“偏科”,苦口婆心劝导,千方百计的“纠偏”,但效果甚微,于是老师们发出了“此子不可教也”的喟叹!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家长、孩子都为升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往往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家长就要做升大学的准备,而周郢的现状,别说考大学,恐怕就是考高中都难入门。周郢的出路在何方?如何继续学习?成为父辈们为之思考的大事。一心想培养小外甥成才的舅舅更是忧心忡忡。曾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父亲,此时说出了自己的见解:青少年学习成长阶段,偏向、迷恋上某一学科,即形成了“偏科”,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偏科”并不可怕,怕的是科科平庸,更怕是一无所长。
在家庭会议上,父亲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受家庭、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影响,出现对某门学科或艺术的偏爱,这种“偏科”往往会转为“特长”,如果适时正确引导、培养,给予一定的条件,很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家庭会议开得很好,母亲、舅舅,包括目不识丁的姥姥都一致赞成。
这种教育方法社会上没有,父亲在一次教育会议上谈过,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他决定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做试验。
不过,辍学使周郢得到了“解放”,他卸掉了走“独木桥”的包袱,欢欢喜喜,轻装上阵了!
从12岁起,他便成为了一名社会少年,但他走的是一条自学之路。
泰安学者崔秀国先生写了一本(《东岳泰山》,周郢读后即提出了几点商榷,崔先生接到那封用繁体字书写的信,就写信约这位“老先生”来家面谈。开门迎客,这才发现“老先生”竟是一个“毛孩子”。
周郢放弃了中考,因为即使考也考不上!从12岁起,他便成为了一名社会少年,但他走的是一条自学之路。
周郢爱逛,爱玩,有了充裕的时间,他搞起了“玩中学”。他爱读有关泰安、泰山的故事,做记录,写笔记,再外出游览、采风,印证一些事实。他到岱庙玩耍,到萧家林参观,抄写碑文,还发表了一些“豆腐干”,包括民间故事,野史轶事。他读书细心,凡有关资料,详细摘记,光卡片就塞满了一只小箱子。
岱庙离家近,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听外公讲岱庙历史,讲建筑风格,讲壁画、碑文:跟舅舅登泰山,带他一路观景,一路讲故事——红门、斗母宫、五大夫松、晒经峪、水帘洞、步云桥、对松山、十八盘、南天门、天街、碧霞祠、无字碑、探海石、玉皇顶……舅舅是周郢小时候崇拜的偶像,他虽是个普通工人,但生长在“书香”世家,读书使他成了一名“杂家”。他对泰山景点如数家珍,加上一肚子娓娓动听的故事,在周郢小小的头脑中,撒下了泰山文化的种子……泰山文化诱导了周郢的“定向”,而一次汉中探亲,更成了他专业定向的“奠基石”。
长期以来,周郢与父母分居两地。母亲想儿子了,“邀请”周郢到陕西汉中探亲,顺便帮助她修改一出京剧剧本——《血泪丹青》。周郢从山东的泰山脚下来到秦岭之南的汉中,写戏剧的母亲,此时发现儿子钟情于文史专业,就把汉中文史专家陈显远先生的一本书——《汉中名胜古迹》送给他读。汉中是历史名城,西汉、三国都在这里演出过最精彩的活剧。历史、文化底蕴异常丰富,书中介绍的文物古迹、名人轶事让周郢着了迷。整个探亲期间,除了帮母亲修改剧本外,还探访了汉中的古迹,“专访”了汉中古代名人——张骞、蔡伦、张良、韩信、李固、诸葛亮……“专访”中查证碑文,不懂他就登门求教当地专家。其中他最崇拜的是陈显远老先生。陈老比周郢大几十岁,堪称“爷爷”了,他与“孙子辈”的周郢结成了忘年之交,常常彻夜促膝长谈,陈老也是初中学历、自学出身,其博学让周郢折服:陈老也很欣赏这个“毛孩子”,教诲备至。陈老带他去汉台研究十三品,去石门观瞻古栈道,龙岗寺讲梁山文化i还讲摩崖石刻,讲历史沿革,指导他搞研究,写论文,与周郢一道参加汉中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周郢的一些有关汉中的研究文章——《王辅臣与“宁略兵变”》、《伪蜀兴亡与安丙功罪》、《日本名人与蜀道》、《羊祉与<石门铭>初考三题》等,都与陈老先生辅导有关。在交谈中,周郢逐渐悟出了小说与史实的区别,演义和历史的不同,其研究方向渐渐明晰。
回到山东后,他更加刻苦自学,广泛搜集资料,凡与泰山有关的志书、典籍、历史,甚至小说、野史,他都要通读,都要做笔记。他特别注意史料中的悬案、疑点,再追根查证,向当地专家请教,或者外出亲自查证。从16岁到19岁,他基本上都是这样度过的。
由于周郢非“科班”出身,基础功薄弱,自学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因此也具有了另一种“优势”,他头脑中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很少有约束与限制,所以一开始就比较大胆地进入到“去伪存真”、“求证解谜”的治学之路。
基于这一点,他16岁与二位同行“点校”了《泰山道里记》,开本不大,字数不多,但这是他第一本研究“泰山学”的小书,对他激励很大。
17岁时,他开始对岱庙天贶殿位置与巨幅壁画《泰山神启跸回銮图》提出质疑。长期以来宋代天贶殿被认为位置即在岱庙,而壁画也是宋代作品。周郢经过认真考证,以原始资料为据,纠正了两则讹传。
周郢的研究立足点为泰山,但他不仅仅是“在山言山”,而是将视点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导。比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父曹頫获罪抄家原因,红学界向有“政治”与“经济”二种观点,长期以来形成“悬案”。周郢在《泰安方志》上查到了曹烦骚扰泰安驿站获罚的记载,从而佐证了抄家并非“预设政治圈套”之说。文章一经《红楼梦学刊》发表,立即引起红学界关注。清史专家张书才复函周郢——“你的发现,有助于对曹雪芹的政治思想和《红楼梦》的主题作出一个平实中肯的评价,所关甚巨,不可不辨。”
泰山是祖国一个“大文物”,泰山文化史料浩繁丰富,遍布群籍,攻读泰山学确非易事。诚如汉中的文化一样,从事这一“行当”的,几乎都是一批“老先生”。为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周郢广泛交友,虚心求教,博采众长。不过,他结交的多是爷爷奶奶或叔叔阿姨等长辈,几乎没有同龄人。
泰安学者崔秀国先生写了一本《东岳泰山》,周郢读后即提出了几点商榷。崔先生接到那封用繁体字书写的信,很为感动,就写信约这位“老先生”来家面谈。开门迎客,这才发现“老先生”竟是一个“毛孩子”。琼瑶女士亦是如此,与周郢关于一首诗出处的信函商榷,也误认为是一位“老先生”,她谦虚地感谢周郢的指导,尊敬地称他为“周郢老师”。
“忘年之交”让周郢受益匪浅。泰山学研究有一个庞大的学者群体,这些老一辈知识博深,且不因周郢是个社会青年而鄙弃,如泰山专家李继生先生,特别关心周郢的成长,热心辅导,倍爱有加,帮助选题,推荐参加“泰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诸葛亮学术研讨会”,每次周郢都是年龄最小的代表,尤其他一脸稚气未脱,尽管佩戴代表证,服务员小姑娘仍误认是某位代表带来的“小孩”,直至“小孩”上了主席台,小姑娘才大吃一惊。
周郢的研究眼界开阔,不囿于一地,他把泰山史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外古今进行辐射式的探索、解谜。从发表的众多文章中都折射出这方面的追求。如《羊祉(石门铭)初考三题》、《盛唐三大政变——在泰山鸳鸯碑上的反映》、《泰山地名话黄巢》、《王莽封禅玉牒索隐》、《唐宋玉册补考》、《泰山与中外文化交流》、《西方汉学家与泰山》、《泰山研究在日本》等等。为了存真求证,他常徒步或骑车走遍泰山周围村村落落,往返于各地文史单位和文物出土地,访贤问老。周郢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舅舅放心不下,每次外出,都陪同前往,充当“保镖”,一有发现,舅甥同乐。
一次他们到郊区探访一位乡贤后人,老者拿出一个油纸包包请他鉴别,打开一看,竟是一幅一米多长的康熙圣旨。一次从一户刘氏宗谱里,他找到了《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的画者,从而印证了壁画的创作年代……这样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从16岁到22岁,7年的“社会青年”期间,周郢没有虚度光阴,他遨游在“泰山学”的海洋中,未因自己的身份低微而自卑,他出版了六本书,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探索文章。一些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引起了史学界和媒体的注意。《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陕西日报》、《炎黄春秋》、《辽宁青年》、《中国人才》等报章杂志多次登发介绍周郢的文章……
“泰山学”研究的一批学者、政协委员们曾联名写“提案”向政府推荐,但因“文凭”、“学历”、“资历”均被卡在人事部门上。得力于泰安师专(泰山学院的前身)领导的赏识和诸多专家的力荐,27岁时,周郢被泰山学院“破格”调入,从事专门“泰山学”的研究。
周郢的社会青年身份,一直延续7年之久。多次“破格”才让周郢夙愿得偿,但也反映出周郢“就业”和攻读“专业”的艰辛。
16岁,周郢有过一次机遇:泰安某文史单位“聘”他当了临时工,每月40元,外出、会议费用不能解决,时隔不久,因“经费匮乏”被解雇。
“少年不知愁”,周郢继续写文章、出书,其间,“泰山学”研究的一批学者、政协委员们曾联名写“提案”向政府推荐,但因“文凭”、“学历”、“资历”均被卡在人事部门上,再加上某些人认为是“搞野史的”,周郢未能“破格”。
《中国人才》杂志舒风先生和何养明先生、上海《人才开发》、北京《戏曲丛刊》,发表过文章,推荐过周郢。舒风先生几次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未能成功……
考虑到“学历”是个关键问题,父辈们商量让周郢去上大学,以求获得一纸“文凭”。经过了大量准备,拍了著作照片,复印了全部文章,附上了恳切地“求学信”,向几乎全国所有高校申请。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承认成果,但不敢打破“规定”!家长转向全国知名学者专家求助——向周之良、费孝通、匡亚明、徐北文等老前辈发了信。虽均有回信,除表示了“爱莫能助”的无奈外,均予周郢以热情鼓励,希望他克服困难,走自学之路,终有希望……
但广泛投书也有效果。威海市委臧海强书记、上海师大顾吉辰教授,接信后热情相邀,不过周郢最后选中了熟悉的汉中。因为汉中的文化氛围很浓,领导中有“知音”,当时的专员杨吉荣爱才惜贤,甘当“伯乐”,他征得了当地老专家陈显远、王复忱、郭荣章的鉴定和推荐,特批人事部门“破格”录用周郢到文史单位就业。但过程并不顺利,个别官员“不信”,也有“搞野狐禅”一类说法,掌权者又以“不合程序”为由,使周郢处处碰壁,最好只能到一个县级文化馆“栖身”了。
文化馆与文史单位看似关联,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但所谓的“渠道”已打通,“程序”亦合法,得力于泰安师专领导的赏识和诸多专家的力荐(泰山学院的前身),没有经过太大曲折,顺利调入高校,至此周郢有了攻读专业的优越条件与环境,有了充足的参考文献。他如鱼得水,得到了又一次的奋取拼搏的机遇!
27岁,被泰山学院“破格”调入,从事专门“泰山学”的研究;
32岁,“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33岁,被评为泰安市“拔尖人才”。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韩愈老先生之名言良有以矣!周郢驰骋于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孜孜砣砣,乐此不疲。近几年他连续出版了几部研究泰山的专著,《周郢泰山文史论文集》、《泰山志校证》、《泰山与中华文化》等书中,《泰山志校证》是周郢重回泰山之后的一个“大部头”,历时8年,长达60万字。记者王姝涛、刘伟在《力破泰山谜》的长文中,给予了一定评价——“对志文进行疏解,补苴,考订,全书征引各种文献近千种,包括甲骨、简牍、卷子、档案、金石以及大量的中外典籍,从中辑录了众多珍稀罕见的研究资料,发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历载……”“揭秘无数,二百余条笺证将泰山文化勾勒得更加清晰……”称赞此书(《泰山志校证》)是一部空前“力作”。
周郢治学严谨,细心求索,勇于创新。胡适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得以印证。郭沫若先生的“泰山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更让周郢的视野拓宽。他在研究中提出泰山是“政治山、宗教山、文化山、民俗山,再到精神山的演进轨迹”,是颇有新意的,凸现了泰山文化的精神高度与内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此为基点,周郢在《走遍中国》(央视节目)中亮相,在《大众讲坛》上呼吁,做泰山的“宣传大使”,为“中华国山”而奔走、宣讲,表达了他对泰山文化的高度深情。
“天才出于勤奋”,周郢身上应该说是并无什么奥秘的。作为一辈子甘为“人梯”的舅舅,最为了解不过了。作为“知情人”之一的父亲,也比较清楚:对周郢的早期引导,家庭与环境的熏陶;人际的交往,追求的执著,特别是泰山文化浓郁的历史蕴含,让周郢在实践中体会到“解谜”的乐趣,逐步充实了自己的天资与悟性……
周郢自学的艰苦,就业的艰辛,联系今天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人才观”的误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是不是应该破除一些条条框框与清规戒律呢?本人是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希望党和政府能有所考虑!我是周郢成长的“知情人”,周郢也是我的一个“试验品”。我有发言权,因为我是周郢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