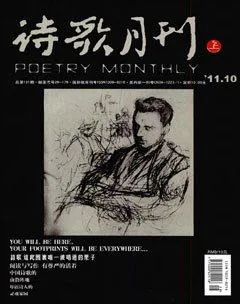那高大的身影依然清晰
收到北塔兄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悼念许世旭先生的文章,一看题目,我就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呢?于是上网搜索,先后读到了一些帖子,也读到白桦、熊辉、陆正兰等多位人士怀念许世旭先生的文章,我才知道许先生真的走了,而且是在2010年7月1日。我得到噩耗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后了,但我仍然觉得非常吃惊和突然。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么一个风趣幽默的人,这么一个把中国文化、中国诗歌作为自己精神营养的人,这么一个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不分你我的人,这么一个看重友谊受人尊敬的人,这么一个年龄并不算大而且还有许多事情想做的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呆在炎热的重庆,本来就使人烦躁,这可怕的噩耗更使我心神难定,一直念叨着一句话:怎么会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
在我的感受中,许先生是个奇人。他是地地道道的韩国人,但是,他却迷恋汉语,迷恋汉语文学,迷恋汉语诗,他的翻译、创作、研究、教学等等基本上都与汉语和汉语文学有关,是韩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这份深厚的爱首先源于他在台湾的长时间学习,源于他对中国文化、文学精髓的了解。上世纪60年代,许先生在台湾学习八年,先后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和当时的许多年轻诗人交往甚笃并保持着长期联系,后来,这些人都在诗坛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诗人已经成为文学史、诗歌史无法回避的名字。可以说,许先生是台湾现代诗的参与者,见证人,他在台湾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岁月,也因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我曾经在2002年11月就韩国诗歌、中国新诗等问题采访过许先生,在回忆起自己在台湾的学习、生活和交往时,他显得非常兴奋。下面是他说的一段话:
在1950年代末,我服完两年半的兵役,考取了到台湾的留学生,那是很难考的。我到台湾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60年认识了叶维廉,他也在师大读研究生,我读的是中文,他读的是英文。有一天,我正在桌上写一首很不像样的新诗,叶维廉来了,我不让他看,他一把就抓走了。在走廊上转了一圈之后,他又走回来,说诗写得很好,要推荐给《现代文学》发表。《现代文学》在当时很有名,是白先勇他们编辑的。过了不久,诗真的发表了。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直到现在仍然是好朋友。从那以后,我与台湾文学界的交往多了起来,与纪弦、洛夫、郑愁予等的关系都很密切,还接受过蒋中正先生的接见,拜访过胡适、梁实秋等文学界的元老。纪弦、郑愁予是我在台湾时最好的两位酒友。纪弦喝酒是很有水平的,而且他有一个习惯,倒完一瓶酒的时候,总要把瓶底朝天用手掌使劲拍击,使瓶里的酒一滴不剩地流出来。叶维廉也想喝酒,可是他身体不太好,不敢喝,每次都是看着我喝,甚至不断地给我斟酒。这些人的人品都很好,对文学、对诗非常投入。
在谈到与大陆诗歌界、学术界的交流时,许先生说:“我是从1988年开始与中国大陆的诗歌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是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的客座教授。我联系最密切的是西南师大,尤其是与吕进先生一直保持着通信、电话联系。我已经来这里三次,每一次都有美好的印象。所以我曾经对我的朋友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也在大陆出版了一些书,主要是在三联,包括一本个人诗集和一本韩国诗选。”我相信这话是真的,新诗研究所的师生,只要接触过许先生的,一谈起他,个个都会很兴奋。许先生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客座教授,不是那种仅仅挂名的。
许先生第一次到中国新诗研究所是1991年2月,方敬、吕进等热情接待了他,学校还聘任他担任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当年底,许先生再次到了研究所,呆了差不多一个月,为研究生讲课,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当时的研究生不是很多,除了上课,江弱水、王毅、徐伟锋(北塔)、莫海斌几个同学还经常陪陪许先生喝酒,甚至把课堂开到了缙云山上,边喝酒边讲课,据说每次都喝得不少,许先生说他甚至醉过,但他很高兴,也很放松,这也许是他把中国新诗研究所称为第二故乡的原因之一吧。许先生后来一直把这四个人称为“四个鬼”(酒鬼),足见新诗研究所及其师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我还在广西民族学院工作,1992年底才调回新诗研究所,没有能够与许先生见面,只是从研究所的刊物上了解了这些信息。但是在后来,我总是不断听到吕进先生和一些同学谈起当时的情景,谈起许先生的学识、人品。我想,一个不断被人挂在嘴上津津乐道的人,一个经常被人想起而且使人高兴的人,自然是在心中具有重要位置的人。
许先生经常应邀到大陆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2004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还专门举办过他的散文讨论会。我和许先生的交往主要是他到新诗研究所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讲学的时候。
一次是在2002年11月,许先生到研究所讲学一周,讲的题目主要是“中国新诗应当继承古典诗歌传统”、“海峡两岸诗歌发展比较”、“中韩诗歌比较”等,我聆听了其中的部分讲座,内容相当丰富,有些看法也相当新颖。如果没有深爱与深知,是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我好像和他一点都没有陌生感,我已经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介绍,也看过他的照片。许先生身材比较魁梧,相对于南方人,用“高大”这个词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他讲话总是中气十足,给人印象深刻。当时我刚刚担任新诗研究所所长,平常安排了较多的时间去陪他。我知道他的酒量不错,几乎每次都安排几位老师或者同学陪他喝酒,他甚至开玩笑说我给他设置了“陷阱”。我告诉他,确实没有“陷阱”,主要是希望他在新诗研究所过得开心,也以此表达我们的敬意。他每到一处就会增加一些新的朋友,因为到新诗研究所讲学,他与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诗人谭朝春已经非常熟悉,每次到学校,他都会问起,并且一定要找时间聚会一下。许先生离开的前一天,我就一些诗歌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在交流中,他一直把吕进老师称为“老板”,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新诗研究所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回国之后,我把采访文本打印后邮寄给他,请他过目并提出意见。采访稿的定稿上清楚地记着,12月28日晚上,许先生从韩国给我打来电话,说稿子很好,除了个别期刊名字,不需要修改,并要我转达他对吕进先生和新诗研究所其他师生的新年祝福。当时,十多位二年级的研究生正好在我家里,他听说后很高兴,还和罗文军、颜同林两位同学通了电话。几位同学都很吃惊,许先生居然能够叫出好多同学的名字。
另一次是在2004年9月,许先生应邀参加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他为论坛提交的论文叫《中国诗人,必须中国》。一个外国人,对中国诗歌那么关心,而且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任何一个热爱新诗的中国人都应该为此而感动。我曾经对许先生说,对于大人物,新诗研究所是要“雁过拔毛”的。论坛之后,许先生为研究所师生举办了题为“台湾军旅诗人的放逐意识”的学术报告。当年的7月26日是许先生的七十大寿,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中国新诗研究所师生在9月23日为许先生举行了迟到的生日晚会,烛光、鲜花、蛋糕、生日歌、诗朗诵使晚会充满温馨的气氛。吕进老师深情地讲述了他和许先生的友谊,谈到了他对许先生的敬重。许多同学以歌舞、演讲表达了对许先生的祝福。许先生在致辞中说,这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有意义的生日。我感觉到了,平常话语流利的他说起话来居然有些断断续续的,眼里挂着泪花。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后来在电话中,他还多次说起。
许先生是个很细心的人。每次到重庆,他都要为自己的朋友带一些小礼物。他两次都给我带来了高丽参茶,说是对身体有好处。其实我是不喝这类营养茶的,也许是舍不得喝吧,放在某个地方之后就忘记了。到现在,我的书架上还放着其中的一盒,早已过期了,但我没有扔掉,它好像在提醒我,那是许先生送的,代表着一种友谊。
许先生学养深厚,思想活跃,待人友善,但他在掌握现代技术方面却不是高手。他不会使用电子邮件,只有通过信件、电话、传真等传统的方式对外联系。所以,我们平常的联系并不是很多,不过他出版了新书,都会寄给研究所的老师。我读过他的诗歌论著、诗集、散文集,他对汉语、汉文化了解之深厚,是我们这些中国人都不得不佩服的。他的汉语也说得非常地道,每次到中国,开初两天也许可以从他的语调中听出他不是地道的中国人,但几天之后就分不清了,甚至连重庆的一些方言也能够听懂,在交谈中偶尔来上一句,使人大吃一惊。据吕进老师说,许先生有一次从成都乘火车到重庆,买的是国内乘客的软卧车票而不是外宾票,价格低一些。乘务员查票时,因为他的形象像中国人,又说一口地道的汉语,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查证件,当然也就没有发现他是外国人。许先生是个中国通,不只是了解中国的文化、诗歌,而且对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也非常熟悉,可以和我们交流他对中国的时事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看法。他的许多书是用汉语写成的,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一般人肯定会将他误为华人。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诗与散文当然不能叫华人文学,但是称为华文文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5年9月,许先生为即将迎来二十岁生日的中国新诗研究所写来贺文,题目叫《有山有水的校园里,我曾做过岛民》,写下了他和吕进先生及新诗研究所的交往,以及新诗研究所师生带给他的快乐,还专门谈到了他的七十大寿晚会,语多俏皮,但感情真挚,读后令人甚觉亲切。
在那以后,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许先生了,但仍然可以从和他联系密切的吕进老师和其他一些朋友如北塔那里听到有关他的信息,也可以在一些报刊上读到关于他的报道。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听到的却是他去世的噩耗。北塔在文章中说,许先生是因为肝癌去世的,不知道这和长期喝酒是不是有关系。看来,祸福相依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美酒给许先生带来过快乐,带来过灵感,甚至带来过友谊,但最终还是伤害了他的身体。
我几乎每天都要上网,主要是看看新闻,处理邮件,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看到许先生去世的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身边的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噩耗,甚至写出了怀念的文章,可我却茫然不知。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太过封闭的人,一个局外人,好多信息都没有了来源。尤其是没有在第一时间为许先生的去世表达自己的哀悼,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悲凉。但愿许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这迟到的回想。
在我心目中,许先生是大人物。这样的人,即使肉身消失了,但他留下了情谊、学问、作品、精神,他在人们心中、在文化发展的精神脉络里,是不会消失的。许先生2004年写下的《怀北碚》的旋律还在我心里回响:
雾浓的日子,总是舒适
仅见我走着的几步路
仅见我站着的一块地
仅见与我携手的人
连同行的鼻子也朦胧起来。
昏沉白日,染上了桌灯
淅淅霏霏的黄昏细雨中
步出专家楼的小院又拐几个角儿
远见袅袅的寒烟古驿
近见温馨的柳枝纱灯。
每逢四合薄暮时,我挥着马棒
风衣飘飘地带领“四条汉子”
解渴解颜,对酒当歌之后
就把踉跄身影印给泥路上的
那师生一伙的幸福岁月。
吠日的地方做客好
坡下有清瘦的高个子站着
供我一个夜也吃不饱的火锅。
风呼呼的清晨,电话响了
叫醒过正要步入天涯那边。
这首现代派风格的诗抒写了许先生与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关系,好多意象其实都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外人也许难以读懂,但我懂,新诗研究所的师生懂。新诗研究所在许先生心里,许先生高大的形象也刻在新诗研究所师生的心里,其中包括我。
2010年8月20日,重庆之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