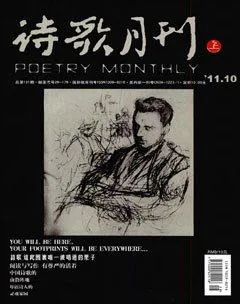当代诗歌场域的几个问题
唐诗宋词以后,我们总是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是郭沫若,还是艾青;是徐志摩,还是穆旦;是北岛,还是海子;是西川,还是韩东;是伊沙,还是杨健;是沈浩波,还是江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或许,在多元的时代,对于诗歌价值的认定也应该是多元的。然而,还是有一些人不放心他人的眼光,总是以君临天下的姿态,说诗歌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这种姿态极为可疑。我们大可不必理睬。然而,现代诗写到今天,除去文学史定义的价值文本,面对形形色色的诗章,我们该如何取舍,如何判断,确也是一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剥开表象,裸露生命的内核,透过技巧,直抵灵魂的现场。
诗歌不怕大,也不怕小。大到民族、家国、时间,小到个体的悲欢,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节拍和韵脚。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白,写大必须具有史诗的视野、胸怀和厚度;否则,大了就容易空,浮在空中,大词横飞,却言之无物,犹如“文革”中的口号和打油诗,分贝有之,但缺少应有的真诚和真实。而过于小,则容易油滑,似乎一切都可以入诗,诸如瘙痒、疥疮、鼻涕、大小便之类的东西都可以找到成为诗歌主体的堂皇理由,这样的小便有些随意,同样需要警惕。但对于大多数诗人,尤其是初学者,我觉得还是以小为好。小处着眼,小处立意,小处落笔,小的感觉,小的思绪,小的发现,个人的话语方式,常常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当然,往深里说,我所说的小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尚低,凡事都往裆部使劲,在私处意淫,而是主张关注生命的细节,思绪与感觉的微妙变化,生命对生存的环境、对时间、对时代的私人化反应及态度。这样的小则极有可能上升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比如北岛的《回答》和《献给遇罗克》,欧阳江河的《广场》,于坚的《零档案》等诗,并没有写祖国啊,民族啊,人生啊如何如之何,但因其中涉及了民族、时代风云在个体生命中的强烈反应,从而使得个人的反思和宣告有了时代的共性,自然而然从一己之小上升为时代的大。当然,这种转变绝非刻意为之,它应该是生命的自觉和灵魂的现场,来自真诚,源于血液。说到底,大小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只要生命有强健的心跳,有粗壮的血管,有饱满的情感,有对时代现场的指认与承担,即使写生命的细节,也自然有一种大的骨骼和力量;而只要有善于捕捉的眼睛,有善于感动的心灵,即使在时代最整齐的声音里,也能发现其中隐藏的差异,和个体生命细细的呼吸和掌纹,即使写时代的兴衰,也自然会有个体生命的疼痛和秘密。但是,对于醉心于小的诗人,必须时刻警惕“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写作状态。找到感觉,一发不可收拾,一天动辄几首甚至数十首,且首首都有值得玩味的东西,这种写作状态是难得的,但也是需要警惕的。因为,感觉是转瞬即逝的,任何一个小思绪,抓住它记录它便有诗歌的可能。然而,并非所有的思绪可成诗,正如石头与美玉的关系,所有的石头都可能蕴含玉,但并非所有的石头都是玉本身,有了可能的条件,并不是终极,还需要继续打磨。这是常识,用在诗歌上也同样合适。有些诗人写了一大堆,分开读,也觉得有些意思,可放在一起来读,却发现其中的感觉只有一个,无非是这首通过了鼻子,那首通过了眼睛而已。这样的作品便值得怀疑。不是说它不真诚,它甚至很真诚,但却有讨巧的嫌疑。退一万步说,在艺术中,真诚绝非艺术的惟一参数,更不是惟一的标准。可以说,这种讨巧的作品是可以复制的,可以成批成批地写下去的,它会使你的写作充满了流淌的快感,而没有艺术长期孕育和破茧的疼痛。然而,又是一个艺术常识:真正的艺术无法复制,更拒绝批发。我觉得,这是网络的弊病,缺少理性的思考和沉静的心态。说到底还是浮躁和虚荣,缺乏对诗歌的虔诚和尊重。所以,我主张在写作呈现加速度的时候,自觉地慢下来,甚至停下来,反思一下近期的写作都提供了哪些方向和哪些可能,看一看有没有对过去的重复,有没有继续的必要。静中生悟,此言不虚。当然,还有一种更为实在的办法可以预防这种惯性的“快”,那就是经典阅读,从时间中汲取力量,从缓慢中思考价值。
羞耻与崇高
和前几年的诗歌网络论坛的风起云涌、遍地开花相比,当下,纯粹的诗歌网络论坛越来越少,越来越荒凉,尤其是2010年8月底,几乎所有的诗歌论坛都被乐趣园莫名其妙地关闭。现在,虽然一些论坛已经重新运行,但却沉寂了许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网络论坛已经失去了昔日那种风风火火的劲头,几乎成为了朋友们相聚的会所和沙龙。或许,从没有边界的大开放到当下的有所顾忌的半封闭,从过去那种无序的自由到如今这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是诗歌网络论坛发展的必然,也是诗歌网络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著名的非著名的诗人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这块曾经风云跌宕的地方,退到了博客那片自留地。然而,网络论坛写作的一些弊病却留了下来,那就是随意、投机和噱头,并非有意回避承担,而是根本就没有承担,并非有意不去关怀,而是根本就没有关怀。在他们心中,一切都是表演,是为了获得一声喝彩声的手段,和诗歌无关,和情怀无关。然而,这样的文字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哪里脏写哪,什么无耻写什么。
苏珊·桑塔格说过:“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以前你几乎可以牺牲一切来掩饰你个人生活的秘密,现在你吵嚷着要求被邀请到电视节目上暴露自己的隐私。”(《关于对他人的酷刑》)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刻薄的,但却是当下文学现状尤其是诗坛现状的某种指认。在一切都进入市场,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似乎变得迟钝了,迟钝到丧失了昔日的那种敏感道德感和尊严感。为了所谓的名声和利益,什么自我贬低的手段都可以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其在缺少传统媒体审查的互联网时代,这种追名逐利更是愈演愈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两天的炒作事件层出不穷。一些诗人把无法在传统媒体发表的东西贴到网上,到处兜售那些诸如糜烂的私人生活,然后获得网络的围观和某种被看的满足。这样的写作是空心的写作,退一万步讲,即使有心,那也不再是正常的心,而是扭曲的,乖张的,变态的。它流露的是虚荣,是虚弱,是虚无,是茫然无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诲淫诲盗和对生命的仇恨。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氛围里,那些表达生存苦难和灵魂困境的声音是微弱的,因为它的沉重不符合娱乐至上的尘世要求,因为它的坚持不符合张扬个性的肉体放纵。正如安妮宝贝所说的:“人的生活中,优雅,清洁,美好,克制,自我反省的部分,已经被直接的、缺乏控制的丑陋所击倒。丑陋,很坦然。美,因此而羞耻。”(《清扫》)丑陋获得了权利,美因此而蒙羞。这是当代诗坛的诸多弊病之一。
在那种让美蒙羞的文字中,崇高是缺席的,尊严是遭流放的。然而,当我们在那种噱头中走出来,无聊过后,恶心过后,茫然四顾,却发现,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依然保留着对道德、尊严、崇高的某种诉求。灵魂深处的部分渴望清洁。我知道,艺术的道德之一是使读者知道这个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但艺术之外的伦理道德也自有其重要的普世意义。我们经历过消解崇高的先锋文学,但消解的是假崇高和伪道学。其实,崇高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表达家国情怀和捐躯意识,更不仅仅局限于那种民族的盛衰存亡,诸如特洛伊战争之类的史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的学者朗吉努斯对崇高的解释更符合我们对崇高的现实理解:“一切事物都含有一些天生固有的本质成分,因此自然而然,崇高风格的另一个源泉就是我们准确无误的找到最适当的本质部分,把它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论崇高》)崇高绝不等于那种形式上冲击力、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以及高蹈的政治话语,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说:“谨防主流意识的滥调和引语。”那种依附于政治的诗歌写作是危险的,也是虚假的,它们除了对运动的宣传有一定的作用外,没有文学价值。正如“文革”十年重批量生产的那些假大空的颂歌,就是经典的反面教材,它们只能封存在历史档案中。真正意义上的崇高不仅是形式上的,而是要求对事物本质最基本的准确和深入。从这个角度上看,那种叙述颓废、堕落、找妓女的日记式体,那些忽略生存艰难、精神困境的小情趣、小趣味书写,则无异于矫揉造作和无病呻吟,它们不是诗歌写作,而是文字游戏。这种文字可能有看点,但缺少关怀,可能有刺激,却没有灵魂。说到底,这种清浅的诗歌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们没有任何难度,像韩寒讥讽的那样,只要会用回车键便能写出来。这种说法虽然尖刻,但却切中一些诗人的脉门。那种口水化泛滥的写作,那种小情调自我陶醉的写作,那种情绪流水账的写作,那种凡事都往裤裆使劲的写作,那种追腥逐臭的写作,几乎消解了诗歌写作的尊严。这样的写作当然是没有难度的,因为,它还没有进入诗歌的核心,没有体认到生命与语言的尊严。所以,这种写作极容易进入一种混乱的、审丑的泥潭,流于烂俗的聚众沉沦。
真正的写作是有难度的,那种难度不仅仅来自于诗人自己对写作的虔诚,更源于诗人的现实关怀、灵魂坚守以及对世界的深刻体认与凝神雕塑。诗人的职责不仅仅是反映某种现实,揭示某种真相,更重要的是,诗人要有热情、有能力也有耐心拎出那种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有思想深邃者才能说出高尚的言词”( 朗吉努斯语)这才是难度的真实所在。而当下的诗歌现状是,许多诗人在网络论坛的刷新中迷失了自我,沉沦于点击率的眩晕中无法自拔,缺乏深入本质的定力,更缺乏基本的羞耻之心和敬畏之感。可以这样说,在善恶不明、黑白颠倒的写作中,许多人既丧失了理性判断,也丧失了情感的珍视,在虚拟的真空世界里,把诗歌写作当成了街头的表演。我们承认,诗歌需要锋芒,需要个性,好的诗歌不等于好人主义。然而,锋芒必须是有关怀的锋芒,个性必须是底线的个性,而不应是撒泼和无赖的锋芒和个性。这应该是写作的常识。我们尊重诗歌的个性,捍卫诗歌的先锋姿态,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诗人应该有起码的羞耻之心和敬畏之心。那些关乎人性之美、情感之美、理想之美、道德之美的东西不能遭到无限度的颠覆和践踏。这是人性的常识,写作的大道。
诗歌论坛“腐败”面面观
没有考察过网络上诗歌论坛是如何萌芽、又是怎样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这可能是个很好的话题,我真希望有心的朋友作出来,以飨读者。)当我由宋君晓贤介绍正式登陆这块土地的时候,各处的诗歌论坛已蔚为大观,按小鱼儿的说法,仅乐趣园一处即有一百多个。应该说,初次闯进这片领域,也确实为这里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及时的交流感动了一阵子。不管你的诗作如何,听到一两声赞赏或批评,总比寄往诗歌编辑部的稿子如泥牛入海要舒服一点。人非圣贤,虚荣心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在那段可以称作与诗歌论坛蜜月期的日子里,我可以在周末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电脑旁,在论坛上游弋或驻足,一点也不觉疲倦,满脑子都是关于诗歌争执和新发现的有特色的论坛,甚至也有一股自己申请一个论坛、聚集天下写诗的英豪来抗衡传统纸版诗歌期刊的强烈冲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热闹过后着手清点自己的时候,却发现,这片纪委、法院缺席的地方,原来也有那么多社会上常见的不正之风,我姑且称之为“论坛腐败”。现一一列举如下:
其一曰:诸侯写作,也可称为掌门写作——先用银子或通过关系申请一个坛子,然后四处发帖,请各路大仙加盟。一旦人马齐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镇中军大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代大诗人。此等“诗人”,会不会写诗、写不写诗、写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手中有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虽不能治你于死地,但可以删你的帖子,封你的ID或IP,可以联合十八路诸侯一齐讨伐,让你提前结束网络上的艺术生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再弄个纸版民刊,以集团军的阵势向文学史进军,间或再搞个诗歌托拉斯、把诗歌产业化什么的,那就更不得了。鉴于此,那些挂在名下的诸君,为了那伟大的梦想,自然会惟人家马首是瞻;而那些初出茅庐的“后生小子”,看着那名头自然也都眼晕,只有恭敬有加,不敢越雷池一步。退一步说,倘此等诸公真会写诗也就罢了,像有些论坛斑竹本身就是优秀诗人一样。但偏偏有的是东郭先生。当然,此等诸公偶尔也有应景之作,但也只是只言片语、莫名其妙,分行的文字而已。但因其地主身份,语句不通的文字,也依然博得满堂喝彩。久而久之,此等诸公也便自我膨胀,指手画脚,底气十足,俨然诗坛泰斗。其实,名其为诸侯写作,还是看重他的写的,若按其对诗人指画方略的劲儿,活脱脱社会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嘴脸。说到底,诸侯写作的背后,还是权钱二字。艺术不是权力的衍生物,也不是金银的寄生品,所以,在论坛苦苦经营的诗人们,需千万警惕这论坛上的第一大腐败。
其二曰:技术写作——网络论坛不同于传统的纸质诗刊,它的信息、技术的含量颇高。尤其是做网页,出网刊,离开技术,寸步难行。这就使得一些投机分子,仗于网络先登堂入室一步,四处献“技”,今天帮这路诸侯抓建设,明日帮那路诸侯搞清算,顺便搜罗一些“资料”,忙得不亦乐乎。然后,就可以四处以功臣自居,风光地游走于各个论坛,抽空子再把那些资料一抖搂,也真能让一些不明就里的新人钦佩一阵子。于是,这类技术工自然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论坛总管、诗坛权威。如果非要说他的诗歌写作,我觉得说技术写作都有点过分,顶多也就是投机写作吧。当然,这类写作大多还是各路诸侯的食客,人家毕竟还有一技之长,即使是腐败,也属于擦边球式的,算不上十恶不赦。况且,人家毕竟还是为论坛的繁荣做出过贡献,所以,在划分敌我矛盾的时候,还是应该团结的,条件是自觉地把技术头上的诗歌花环摘下来。
其三曰:人缘写作——这类人物大多有一个轻闲的工作,待遇不错,上班没事,办公室有电脑,上网不花钱。于是,他就可以半天半天地吊在网上荡秋千、搞公关:笑脸迎接各路诸侯,赞美送给四方大侠。虽然也有热脸贴在冷屁股的尴尬,但大多数国人还是遵从先辈礼尚往来的遗训,于是,一阵秋波过后,也会接到几个霸主的青睐和赏赐,值个班或驻个坛,先混个脸熟,天长地久,用不着改朝换代,也可以荣升、可以参政,也便当然地成为论坛红极一时的人物。接下去,就可以心安理得接受如他先前一样周游列国待沽者的逢迎和巴结。当然,这等人中也确有饱受传统诗歌机制压迫的才人,在世事洞明之后,顿悟了弥勒佛祖开口便笑的高明,故而低姿态入世的。此类情况自当别论。这些论坛弥勒不同于生活中的老好人。因为,老好人之“好”是但求无过,而此类人之“好”是只求有功。以笑脸换笑脸,以恭维换恭维,决不赔本赚吆喝,可谓机关算尽。讲人情是国粹,热情总比冷漠好。再说传统纸刊也有关系稿,在这个更自由、民主的论坛搞个把友情客串或许也不算什么,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怕就怕在这等弥勒善意的“就是好就是好”的颂扬声中,诗歌失去应有的艺术警觉,变成抽了大烟的瘾君子。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诗人颇似论坛上的“弄臣”,绞尽脑汁就为博君王权臣一笑,人格尽失,也让他人玩物丧志,想想也够可怜兼可恨的。
其四曰:撒泼写作——这类写作和人缘写作颇为相似,走的都是情感投资的路子。所不同的是:前者投入的是笑,而后者则偏攻骂。虽然算不上怒目金刚,但说像牛二还是很恰当的。他横着走在各个论坛,一百个不服,一百二十个不含糊,仿佛所有的诗人都不入他的法眼:他逮谁扁谁,尤其看好名家。他的舌头很皮实,绝不在乎风扇,什么大话都敢说,什么牛皮都敢吹,目的只有一个,让人在腻味中记住他。善良的诗人也许会替他难过——该不会有病吧。错了!大错特错。他比你明白,他整的就是这个景儿。当然,名人一般都比较大度,不会跟他计较,怕掉价儿。但他绝不气馁,而是执著地骂下去,直到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如若不行,则大加诋毁,大搞人身攻击,什么婊子、流氓的喊。终于有不堪其辱的诗人回击,甚至闹到删帖、封IP、ID时,他就逮着了,他四处张榜,告天下诗人名人与他如何如之何的,言辞慷慨,吊人胃口。中国人好热闹,尤其涉及名人的热闹,于是,大家都要去窥探一番。一来二去,人们都记住了这个敢于呵佛骂祖的英雄。他再玩几句诗,那就是反权威的新锐,肯定卖个好价钱。当然,这类诗人也有可爱之处,那就是有一个比脸还大的胆子,敢捅马蜂窝。有时冷不丁还真能捅到所谓的名人的痛处。但从总体看,这类人还是以骂为主,骂大于诗。用北京土话形容:整个一个矫情。
其五曰:闪电写作——这类人大多是本分汉子,既没有自己的领地,也没有一技之长,更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和心眼儿。他要在论坛上扎根立足,本钱只有一个——写。于是他成批成批地写,分批分批地发,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几乎每一天你都会在各处论坛的第一页发现他的大名。在流动、更新特别快的网络上,能保持如此高的热情,也的确不是那么容易。所幸的是,苦心人,天不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人被这种精神感动了,表示慰问,最后是越来越多的人送来了表彰,尤其是那些诸侯和总管之类也伸出了有力的手。于是他成功了。当然,和前几类相比,这类写作或许还算不上什么腐败,他毕竟还有诗产品。但这类“诗歌加工厂”,也确实有力地推动了诗歌论坛上的“浮夸风”和“大跃进”,让圈外人产生一种网络诗歌提前进入小康的错觉。这不能不让人担忧,毕竟,诗歌创作不能集装箱,它还是需要精品意识的。
当然,凡此种种,仅为我的一点上网感受,因笔力不足,只能泛泛而谈。更深层的根源,还得等方家阐述。至于所列现象,更是一家之言。再者,为避嫌疑,本来想列出的与此对照的出色的诗人朋友也只好隐其姓名了。但我相信,明眼的朋友心中都有一杆秤,一看便知,无需我赘言。或许,这样画像的惟一后果,就是开罪一些敏感的朋友,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但我不想开罪诗歌,不想开罪真正爱诗、视诗为精神呼吸的朋友。所以,也只有如此了。现在,“学术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新热点,也当然引起了知识界的自醒和自查。我真希望,我们的诗歌界——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网络的——也展开一场“反腐倡廉”运动,使原本该纯净的精神家园真正纯净起来。能如此,诗人幸矣,诗歌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