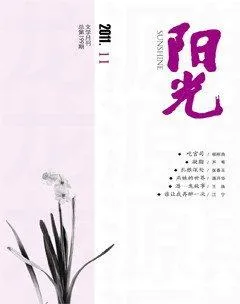树基沟:一个人的词典
北岔
北岔是一个坑口,因为在沟里的顶端,且北向延伸,故名。这是日本人勘探并开采的矿点,属于清原金铜矿的一部分。据说,清原金铜矿像一头牛,树基沟是牛尾巴,红透山是一只牛蹄子,其余三只牛蹄和牛头、牛身在哪儿,谁也不知道。也许日本鬼子的手里有一张矿脉图,但肯定已销毁或带回国。
北岔给我的最初记忆是:一九七一年,这里发生瓦斯爆炸,有人死亡。我的同学小文的父亲身埋其中。那时,小文只有五岁。若干年后,我与小文来到这个业已废弃的坑口,我们想进去看看当年的爆炸现场,却见里面汩汩冒水,探之,没膝。村人说,里面先是一条百余米长的巷道,然后是深不可测的竖井,井壁焊有铁梯,援梯而下,可见宽敞的硐室,室壁画有毛主席像和他老人家的语录。去年,坑口已封,我们永远也看不到这段历史了。
南岔
与北岔一样,南岔亦是一个坑口,当然,它在南面。如果说北岔是一条牛尾巴,那它一定是与南岔相连。
南岔比北岔开采得晚,以至我记事时,那里还是热火朝天的场面:工人们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肩挎炮药兜子成群结队地向这个沟筒子里走去。父亲就是其中一个。后来,父亲退休了,这个坑口也黄了,为了生计,父亲找到领导要求留在这里打更。其实,父亲的真实想法是白天去附近的山上砍柴,开荒种地,夜里宿在工房,既可以挣些补贴,又不耽误活计。领导允诺。从此,每天放学后,我就有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给父亲送饭。好在南岔离家不远,三十分钟即可走到。
火药库
顾名思义,火药库是储备火药的地方,是为矿山的掘进开采放炮所用。所以,它的位置就很偏僻,远离居民区,在沟里的一个半山腰上。
我对火药库的印象很深,因为父亲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摔伤了腿,康复后即被安排在这里上班,意思是活儿不累,如疗养。这样父亲就很少回家,每天抱着那杆三十八大盖(步枪)坚守岗位,即使不当班,亦不轻易下山,因为路远,且还腿疼。因为是在地表工作,单位不发保健(工作餐),父亲就在火药库旁边开块菜地,种上蔬菜,也从家中拿了米,索性自己在班上做起饭来。为此,母亲很是担忧,想方设法做些父亲不能做的面食,如糖饼、饺子,然后让我送去。这可是一个美差,因为给父亲送饭,不仅可以暂时逃避家里的活计,边走边玩,到了目的地还可以和父亲一同享受美餐。吃饱喝足,再翻箱倒柜,或许就能从哪个犄角旮旯蹦出个子弹壳来!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的东西,甚至超过毛主席像章。而火药库山下,正是同班一个漂亮女生的爷爷家,有时送饭路上,我们会不期而遇,虽然彼此并不说话,可我喜欢那种莫名的感觉。
二〇五
二〇五是小火车名,确切地说,我们故乡的小火车头是205型号,至于何年何月何地制造,则非我辈能知。但我知道,从树基沟沟里的始发站到北三家穿过山洞停在半山腰的终点,全程四十公里,中间停靠南岔、土窝棚、三道观、石头人、二道沟五个站。二〇五载着它两节绿色车厢,走走停停,晃晃悠悠,经过四十多分钟才能走完全程。如果是冬天,则会更久。
每一个故乡人,都是用这辆二〇五拽出沟的!无论官人,还是百姓。即使后来二〇五换成内燃机,人们还是习惯这种叫法。遗憾的是,随着树基沟镇的撤销,坑口的关闭,工厂的迁徙,学校的转移,二〇五也早已走出人们的视线,连同它脚下那两条瘦瘦的铁轨。
铁道
铁道是故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路线,铁道上的小火车即可载人,亦可拉矿,只要时间错开,就能各得其所。
铁道之于我,又不仅仅是出走或回归。更多的时候,是我在上面徘徊,彳亍,蹲坐或站立,手里拿着书本,也许什么都不拿地低头想着心事。天上云卷云舒,道旁花开花落。一个人,二个人,几个人待到很晚。童年,少年,青年渐渐老去;早晨,黄昏,深夜,日月更迭。如果问我故乡门前的那条窄窄的铁道带给我最深的记忆是什么?那么,我想说:就是与同学谷守红的彻夜长谈!那时我们初中刚毕业,面临中考,我们相互激励,相互迷茫,终于又迈进同一所学校。倏忽二十年,如今,我们已成老友,如一壶陈年的酒。
铁道南
粮站下边的铁道南是一块坡地,过坡地是连绵起伏的山,山外还是山。有若干条小道从坡地通往山中,细如羊肠,是人们上山打柴、采野菜和蘑菇的路径。那块坡地,平坦些的归农户所有,而一些边边角角,则是我们这些工人户开垦的,谓之小股地。小股地并不一定都种庄稼,很多是用来堆放柴火,一垛一垛连成排,很是壮观。
于是,铁道南成了我们这片孩子的乐园。只要放学,只要没有家务可做,我们就会尽情地在这里撒欢儿:钻苞米地玩打仗,进高粱地吃乌米,躲柴火垛捉迷藏,掰豆秆儿编刀枪……无不兴高采烈,乐而忘返。如果是春天,起风的夜晚,谁家的柴火垛被仇人点燃,就会一垛一垛牵连数家,使得我们这些铁道旁的住户,纷纷担上自家水桶,从水井沿到铁道南,往来穿梭,直至扑灭大火。
这时,失火的人家,妇人就会破口大骂纵火者不得好死,男人则是一边给邻人点烟,一边琢磨怎样再打一垛柴火。
三公里
三公里是一个火车站,当然也是指距离,也就是说从小火车的始发站即零公里处,向北三家方向行驶三公里,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靠着一个叫作土窝棚的村子,位于铁道下边不远处,隔着一片高粱地,一条河,一条公路和一片稻田。铁道上面则是西山,林木茂盛,百花绚丽,是春天采野菜秋天拣蘑菇的好去处。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村子,所以才在这里设了一个车站。但我们谁都不愿意叫土窝棚车站,而是一口一个三公里,潜意识里三公里是数学,洋气。土窝棚自然土,说起距离,也一定是几亩几亩的。这里的我们,自然也是指居住在树基沟镇上工人户的我们。
粮站前白房
粮站前白房也在铁道的北边,中间隔着菜园,凡是乘坐小火车的人,无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要坐在车上,面朝北窗,都会看到这座白房以及白房前园子里的蔬菜瓜果,仰面朝天的向日葵,甚至摇曳多姿的罂粟。如果是夏天,还可以看到房前晾晒的衣服,打开的门窗,站在院子里翘首眯眼的身影。
这一趟房一共住着四家,我家在最西头,向东依次是刘波家、孙朋家和小胖家。当然,我说的刘波孙朋小胖,都是与我一样的半大孩子,我们的身上身下还有哥姐弟妹,比如刘波二姐叫刘萍,孙朋哥哥叫双人子,小胖有个练武的五哥,在院子里打车轱辘靶子一连能打三个。这四家当中也只有我家没有女孩,或者说曾经有过,但最后都夭折了。所以我们家清一色是男孩,五个,我老四,身下还有个弟弟。但和我经常在一起玩的是刘波孙朋。孙朋与我同岁,刘波比我俩小一岁,我们仨亦是同学。每天上学,他们俩都要在家等我从西边过来,然后一起上铁道,走过窗前,我就将书包扔给刘波,告诉他左肩一个右肩一个,既平衡又威武,仿佛挎了双匣子(枪)!孙朋就在一旁笑。这小子是我们仨当中心眼最多的一个,虽然学习不咋地,光小学五年级就念了三年,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打基础。但他的长处,却是我和刘波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比如上山打柴,下地挑粪,比如那年冬天大雪封门,一只野鸡居然飞到他家门前的园子里觅食,这小子打开窗户,三蹦两蹦地蹿了过去,最终将野鸡变成那年春节他家餐桌上的美味!
其实,孙朋家是粮站前白房搬来最晚的一户。之前,那间屋住着一个李姓人家,且在门前的园子里打了口水井。有一年,他家的一个小男孩不慎掉进了井里,所幸没有淹死,被人用土篮子捞了上来。
下院
下院是指粮站前白房东边的几栋房,因为位置比较偏下,故得名。实际上,粮站前白房是一栋很孤立的房子:左为西壕沟,前为火车道,后面除一个园子外就是粮站大院的围墙,要不是东边挨着下院,有一条宽敞的胡同通往公路,简直难以进出。所以,下院不仅是我和刘波孙朋的交通要道,也是众多孩子们的欢场。
但下院的居民似乎不大稳定,搬来搬去的总。男孩也不多,除了丁宝武杨锁柱曹大军,基本也没有谁和我们玩。王贵富是个例外。
刘波经常给我背书包,孙朋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颠的,除了他俩之外,我似乎还管不了其他什么人,尤其那些学习不好经常逃课的小子,每每在下院遇见都想躲着走。这也不是说我和刘波怎么怕他们,主要是我们玩不到一块堆去,所谓道不合不相为谋吧。如果说淘气,我和刘波顶多是猫在房后画两张电影票,或是在铁轨上轧个钉子什么的自娱,而那帮小子完全不屑于这些,摘谁家沙果李子是小事,弄不好晚上点柴火垛亦是在所不辞。犯不上,跟他们。
但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我们就和王贵富好。因为王贵富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人高马大,勇猛威武,我们是同班同学,且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都在火药库上班,关系自然拉近了一些。这样,再和那帮小子碰面,他们就点头哈腰了。只是小学没念完,王贵富就喝敌敌畏死了,弄得我和刘波孙朋一度伤感,没着没落。
河套
出下院,过公路,沿着中学外的围墙向北走,不远就是河套了。这是镇上唯一的一条河,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反正是从沟里流出,由西向东,傍着山脚一路走来。仅管河面不宽,水流不急,每到夏天,这里仍是我们的乐园,亦是大人们洗衣裳放鸭鹅的地方。
但我最终没有学会游泳。虽然我也满头大汗地跟着哥哥们抬土垒坝,清理河床,将河面憋得老高,可我不会像别人那样畅游其间,无论仰面朝天,还是头埋水底,哪怕最简单的狗刨呢也不会,更甭说是脱光了衣服从河畔的山崖上纵身一跃了。所以,常常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小馆
小馆就是饭馆,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位于合社后身。草房,泥墙,窗户纸糊在外的两扇木格窗子,高高的门槛,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从屋顶吊下来,昏黄的灯光透过腾腾热气,散落在屋地面的三张木桌上。
小馆老板姓单,我们都叫单大爷。
小馆兼做豆腐。有脑,有块,有片,几分钱几角钱不等,也可以用豆子换,既经济又实惠。
小馆虽然对外开放,但大多数是公家未了客人才在此招待,比如矿上镇里工厂学校卫生所派出所,接待上级部门检查工作什么的。个人很少有去就餐的,即便家里来了亲戚,也顶多是买两三个菜用饭盒装回家吃,谓之待戚(音qie)。
合社
合社是指镇上的两个商店,一为综合商店,一为副食商店。为什么叫合社,是合作社的简称吗,还是说着顺口?我至今不得而知。
应该说,合社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尤其是春节前夕,不仅大人们背着兜子提着篮子来这里采购,就是我们这些穷孩子,也要把一年中积攒的零花钱悉数花掉。鞭炮,糖块,小人书,恨不得一网打尽。即使囊中空空,也愿意趴在柜台玻璃上窥视个把钟头,不肯挪动一步。
那时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香烟,白糖,鸡蛋,布料,尤其是猪肉,一年到头,似乎也只有到了春节的时候才能多买一点儿,且人山人海往前拥,满脸堆笑地央求手握砍刀一脸胡须的店员,想尽量割些肥肉,以便回家能炼出油来!
忠字门
忠字门在小火车终点站下面一点的大道上,在站台上一眼就能看见那两个高高立起的铁架子门柱,门柱上面搭一弧形门楣,楣内楣外均镶有红色五星。门柱上则是红底黄字标语,什么内容已经忘记,大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之类。
我虽然生在“文革”期间,但记忆中却不曾见过人们是如何在忠字门下手捧《毛选》舞之蹈之口中念念有词的。但每每路过那里,还是会不由得联想起电影中的某些镜头,尽管遥远,亦如昨天。而忠字门,似乎也成为镇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谁谁对谁说:今晚我在忠字门下等你,不见不散。谁谁告诉谁:我家住在忠字门旁边那趟白房里。
粮站
同合社一样,粮站也是国营单位,且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因为位于我家房后,靠近公路边,我家也被通常叫做粮站前白房——白房,就是白灰抹面的房子。
如果不走铁道,走公路,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粮站,都要侧头目睹那些涂着黄油漆的窗板和门板。上学时间,它们还没有开启,那些窗板上就异常醒目地写着几个红色大字:以粮为钢,钢举目张。不知何意。但放学的时候,这些窗板早已拉开,门板戳立两旁,人们进进出出,或提油或扛米或背面。米是玉米高粱米,面是苞米面,至于大米白面,都是要凭票供应的,很多人家不到过年是不会轻易领取的。
后来,粮站有了一台12时黑白电视机,是镇上不多的几台之一,且离家近,晚饭后,我和邻家的孩子们就蜂拥了去看,终于惹烦了白发苍苍的打更老头,无论我们在外面怎样叫喊,怎样使出吃奶力气摇晃大铁门,老头就是不开,急了,还会丢出一两块砖头——因为我们当中不知哪一个,喊了老头的外号——白毛子!至于砖头是否擦破头皮还是砸在铁门的栏杆上擦出火星,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晚的电视甭想看了,尽管门缝里飘出《霍元甲》的主题歌。
一百零四户
镇上的工人户大致分为三个片区,即小火车终点站一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沟里,然后是合社附近的道南道北两片,再就是我们粮站下片。所谓一百零四户,就是居住在合社后面的一百零四户居民,因为靠近合社饭馆和菜市场,故也是镇中心。至于究竟在什么时期是一百零四户或一百零五户一百零三户,无从考据。
我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那里住着我的两位同学,一位是老五明,一位是海头。另一个原因是,镇上唯一的一家邮局就设在这些住户当中的某一趟白灰房头,靠近饭馆前小广场的边上,这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寄信,取信,发电报,收电报,或是订阅报刊杂志,顺路都可以去那两位同学家转转。
沙台后沟
沙台后沟是比沟里还沟里的一条小沟,且后。沙台是坑口回填用的沙堆,沙堆后面的沟口住着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我的另一个同学王有金家,一户是刘波二姐的同学邱振海家,另一户可能姓毛。别小看这几户人家,邱振海是这个镇上第一个大学生,一度成为家长们教育子女的范本。当然,我的同学王有金跟我一样,不仅没拿范本当范本,而且几乎成为反面教材。
一次政治课上,老师在台上提问问题,说这个问题很难,请咱班学习最好的同学来回答。王有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能问到自己的头上,仍是在一旁眯眼犯困,但老师还是叫了他的名字。
懵里懵懂,王有金在同学们的笑浪声里站了起来,一边手擦口水一边顺嘴胡诌。老师说:差不多,差不多,再想想,再想想。可怜王有金云里雾里哪知道老师的伎俩,一个粉笔头打在他冒着虚汗的脑门,然后说:不对!坐下!
莫日红
莫日红是树基沟一带最高的山,海拔一千多米,在清原县属于第三高峰。每当夕阳落后,山顶仍返照红光,故得名没日红,亦写成莫日红。
我对莫日红最初的印象,不是它的山高水长,云遮雾绕,也不是它的皑皑白雪,晚阳夕照,而是电影——驻扎在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开着绿色军车来我们镇上放映电影。军民一家,鱼水情深。那时小镇上的广播喇叭总会隔三岔五播送放映电影的消息,每到这时,我们就会知道:莫日红山上的解放军又来演电影了!而第一次上莫日红山,则是中学以后,学校老师和山上的部队要打一场篮球赛,要我们跟着去当观众。谁输谁赢,业已忘记,但从此知道了山上的营房、岗哨和防空洞,甚至小型飞机场。
也曾跟随哥哥去莫日红山上砍柴,那里有很多原始森林,二缸粗的菜板都能伐到。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以后的某年某月,驻扎在山上的部队也不知不觉地撤走了。
俱乐部
俱乐部是整个镇上最大的房子,或者说是唯一的楼房:因为房子里面的后半部分搭有看台,两人多高,与楼梯一样都是木板结构,走上去咚咚作响。
俱乐部除用来开大会外,也经常演电影、二人转或革命样板戏,当然这要根据当时的形势。记忆中有关俱乐部的故事太多太多,比如开地痞流氓批判会,将那些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的青年男女赶往台上,当着千百观众削发剪裤;比如毛主席去世,整个镇上的工农学商排队到这里向老人家遗像告别默哀;比如一九七五年早春二月,海城大地震突然来临,正在这里看电影的人们惊慌失措,落荒而逃;比如俱乐部里的谈情说爱、小偷小摸;比如我和刘波没有电影票,偷着在彩纸上描画一番,就想乘夜色朦胧之际蒙混过关,甚至拿了燃着的油毡纸沿地下管道摸进大厅——当然,成功率总是很低。
七十年代后期,俱乐部就很少使用了,偶尔走过那里,只会看到墙上白漆写就的革命标语,还有门前广场上立着的孤单的旗杆。
菜窖
镇上的人家除了居住的房屋、储藏粮食和杂物的仓房之外,几乎每家都有一个菜窖,在房前屋后,或附近的山坡。这是东北的特色,因为气候寒冷,刚一入冬,人们就要将白菜、土豆、地瓜、萝卜,甚至留作过年的苹果猪肉下到窖里,以保吃时新鲜。
因此,挖菜窖成了每个家庭的一项主要活计,虽不是年年挖,但也绝非一劳永逸,而且要选择干燥不易出水又不会塌陷的地方。也不能离家太远,太远拿取不便,还会招来贼人。
小学
小学校是两栋歇山式瓦房,位于小火车终点站的上面,也就是南山坡下。从大道可以上去,从小道也可以穿去。因为放学时老师往往要求站排走,所以常走大道,但上学时,我和刘波孙朋是坚决走小道的。小道快,也有意思。
没有意思的是,整个小学孙朋念了八个年头,为此到初中时,我和刘波就失去了这个要好的伙伴。更没有意思的是,我和刘波、孙朋、王贵富、侯振刚、刘刚、韩朝中、王玉久、姜宝石被班主任评定为“八人帮”,而我,居然又被认为是“八人帮”的头,比王张江姚四人帮似乎还狠。现在想来,这事虽然一直如鲠在喉,但我似乎也并不十分冤枉,因为我的确是很团结同学,包括当时站在教室黑板前的这八位同学。但刘波一直是班中学习成绩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且平时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的主儿,怎么忽然就成了害群之马呢?
老师说:刘波是被我们利用并拉下水的!
这场风波过后,刘波还是愿意和我们玩,起码一起上学放学。而我也并不总是这么倒霉,三年级后,就开始帮学校少先队出墙报给广播站写表扬稿了,当然,也知道暗恋班中那个扎小辫穿黄色衣裳的女同学。
中学
中学在粮站对过儿,中间只隔一条马路。
中学的事情太多了,不想说了。包括一直还想着那个扎小辫穿黄色衣裳的女同学(虽然初二时她已经转到了更大的矿山读书),也一直和刘波团结着,还有霍绍文、谷守红、郭鸿。墙报仍然在写,稿件已经投到了矿报市报,书法作品开始参加展览,开始拜见文化名流,开始厌烦理科喜欢文科,开始阅读大量文学与艺术书籍,开始知道什么叫手淫。
作为故乡我的最后一个名词,中学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几间房屋,靠北边的白杨树和南北墙,课本和足球,早自习和晚自习,物理老师曲家庭的长筒手电,数学老师鞠淑芝的三尺教鞭,等等,应该都是一种助跑或注脚,虽然我没有跑多远,还时常崴脚。但记忆不会断裂,不会忘却雨雪轻扬的那个上午,出树基沟那条公路旁的山岗上埋葬了我的恩师孟德义先生,不会忘记先生在我的诗稿上的批注,以及无数次的开怀畅饮,彻夜长谈。
作者档案
程远: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于辽宁,现为某报编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全国报刊杂志及网络,部分作品收入文集或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