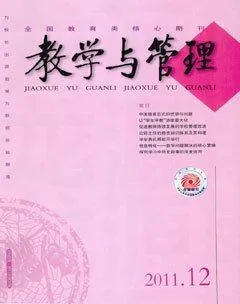我国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困境及其成因
教师惩戒权是教师(个体或群体)为维持教育活动正常秩序、履行教书育人职责而对违反学校学习、生活规范的学生进行惩处的一种权利与职责,惩戒主体是教师,惩戒对象是有违规行为的学生。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基于其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一种强制性权力。然而,这么一种关涉学校、教师及学生三方重要利益亦普遍为人所认可的职业权力,一旦将其置于法制视野下考究,它却显露出某种尴尬、艰难的窘态——因为当前我国教师惩戒权无论在法律根据上还是在具体行使过程中,都陷入了一定的法律困境。笔者认为,揭示其法律困境、认清其“入困”成因,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教师惩戒权的行使与救济问题,进而为可能的教师惩戒权立法打下必要基础。
一、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困境的征象
1.法律依据不够坚实
目前,与“教师惩戒权”相关的法条除了《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外,大多集中在《教师法》。比如,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教师享有“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的权利;第八条第五款规定:教师要履行“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的义务;第九条第四款规定:“有关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支持教师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制止义务与管教学生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教师要有效指导、评定学生品行,显然离不开教育惩戒的有力支持。因而,粗略地看,《教育法》与《教师法》的相关法条似乎可以视为教师惩戒权的基本法律渊源。但细致推敲上述法条,教师惩戒权主要来源于学校对学生实施奖励和处分的权利以及教师“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的权利,换言之,法律在陈词中只是给予学校、教师以一定内容的“权利”、“义务”,并没有赋予其职业特点应有的“权力”。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并未明确授予教师惩戒权,教师惩戒权的法律依据不够坚实。
2.法律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
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中虽未明确授予教师惩戒权,但与此同时,诸多法律法规却闪现出与惩戒密切相关的诸如体罚、惩罚、变相体罚等法律名称。譬如,《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侮辱、殴打教师,禁止体罚学生”;《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学校和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教师法》第八章第三十七条还有对实施体罚者“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之规定,等等。显然,一部良好的法规必然会对其中出现的重要法律概念作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以免在法规的执行中造成无的放矢。但当下的法律条文却在这方面并未做到这点,对诸如“体罚”、“变相体罚”等重要的法律概念未作必要的阐释与界定,造成广大一线教师在认知与操作层面都陷入难为和茫然之境地,进而致使现实中许多教师被迫随意推定、个性化理解那些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以至于造成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践指导意义的丧失。
3.具体的操作性标准缺失
一部良好的法律应明确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可以怎样行为、不可怎样行为等,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让法律更好地调整社会关系,进而为社会生活服务。然而,透视诸多与教师惩戒权相关的法律条例,都存有具体的操作性标准缺失问题。比如,我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暗含有授予教师惩戒权的同时,却没有具体规定教师实施惩戒的条件、程序及程度等,以至于教师在惩戒学生方面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此外,有如前述,相关法条虽都明确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但却未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于体罚、变相体罚,合理惩戒与体罚相互转换的临界点或判定标准亦未必要的阐释。韩国早在2002年便制定了“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该法案对惩戒的对象、缘由、部位、器械都作了详细规定,并对实施的程度、时机、方式作了严格限制。比如,规定老师绝对不能用手或脚直接对学生进行惩戒,实施惩戒的场所要避开其他学生、在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实施惩戒之前要向学生讲清理由等。
4.惩戒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们对教师行使惩戒权的监督存在较大的漏洞。即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行政部门都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往往是辖内出现社会反响大的教师惩戒失范案件才得以被重视,而教师的日常教育及惩戒行为则难以随时监控。其实,教育教学中发生的许多教师惩戒失范案件,往往都是因为缺乏即时的监督制约机制而积聚爆发的。此外,虽然我国《教师法》第七条明确授予教师六项权利、六项义务,第三十九条还明确指出:“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人民政府提出申诉”;《教育法》亦分别在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了受教育者的五项权利和四项义务,其中,在第四项权利中指出,受教育者“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表面上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拥有申诉、诉讼的权利,似乎能较好地实现权利的救济。但从实际来看,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申诉的范围、内容、程序等并未作出详细的规定,且由于某些“人治”思想余毒和官僚作派恶习的惯性影响,即使在某些部门规章里写有相关规定,也很难保证申诉处理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快捷性。更何况,学校本身就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出于为学校管理大局考虑,一般也会站在支持学校这一立场,从而容易导致师生权利的维护运行不畅,这对教师惩戒权行使亦是不利的。
二、教师惩戒权陷入法律困境之成因
造成上述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困境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两个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
1.主观因素:相关法规制定者未能彰显法律预测功能
前述法律困境暴露了我们相关教育法规的法律滞后问题。我们深知,法律预测活动属于人的认识活动的一种,而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性的。由于事物发展具有随机性、任意性和非线性等特点,因而法律预测功能表现出某种脆弱性是正常的。而且,我们亦认同“没有滞后性就没有法律,也没有法律的发展;企图就法律滞后性作‘永恒性’移植手术不仅绝不会成功,而且会使法律的发展失去客观动力”这一观点[1],但尽管如此,就教师惩戒权问题的法律预测问题而言,相关部门、相关法规制定者无疑有着较大的努力空间——在我国近20年立法实践中,尽管肇始于法律条文欠明细而引发诸多实践问题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然我们相关教育法规的制定者即预测主体,仍没有很好关注到这一社会现实,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对于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缺乏足够的估测。除了预测主体的缺陷外,上述法律困境亦折射出相关人员预测信息的偏失、狭窄以及预测方法和手段的落后,在此不一一赘述。要指出的是,法律预测的机制是由预测主体、预测时象、预测信息、预测方法和手段等组成的。法律预测机制的不健全必然容易造成法律预测功能低下,进而招致法律滞后问题突显。
2.客观因素:惩戒实践情境复杂
虽然,我们都知道没有善意惩戒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然而,许多教师缘何谈“惩”色变而唯恐戴上“体罚”的高帽?其实,教师对“惩戒”之所以投鼠忌器、存有畏惧与谨慎心理,乃主要缘于目前尚无相关法规对教师实施惩戒的条件、程序与方式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进而在惩戒实践中不能做到理直气壮,更难以做到有的放矢。那么,相关教育法规又缘何未对教师实施惩戒的各个环节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这恐怕与惩戒实践情境的复杂性不无关系。我国教育惩戒行为实践可谓复杂多样。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惩戒的根由复杂多样。比如,可能因在德、智、体、美、劳中的任一领域的不良表现,而触犯了班级管理方面的规定抑或有违学校管理方面的制度。而那些规章制度显然是分门别类、千变万化的;二是惩戒的主体多元复杂。实施教师惩戒的主体有校领导、一般管理人员和众多普通教师等,这些人员也是千人千面、复杂多样的;三是惩戒的内容及方式芜杂不一。比如,可以是自主学习某些规章制度,亦可以是进行队列训练;可以是书面检讨亦可以是短时的面壁思过等等。总之,教师惩戒可谓内容丰富、方式多样、程度不一。教师惩戒权未能在法律法规层面获得明确、具体的支持,教师惩戒实践情境复杂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
教师惩戒权作为自由裁量权较大的一项职权,有如学者所言,“其行使不能不受到法律的约束……其来源、权限范围、行使手段都应有相应的法律限定,惩戒后果必须有一定的救济手段加以补救,教师惩戒权将逐步摆脱传统的至上无边的特点,开始有明确的边界限制,并将在合理的法律干预下施行[2]。虽然,根据前述分析,我国教师惩戒权当下陷入法律困境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国教师惩戒权不能跳离法律困境。事实上,此类问题已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随着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制建设的推进,我国教师惩戒权跳离法律困境是大势所趋,亦是理所当然。
参考文献
[1] 殷冬水.法律滞后三论.行政与法,1998(2).
[2] 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