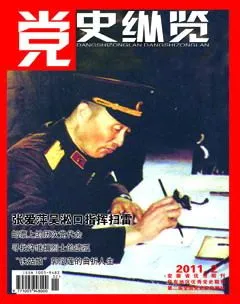桂林栖殚精竭虑推行责任田的前前后后(下)
2011-12-29 00:00:00江鲲池
党史纵览 2011年2期

推 行
桂林栖对推行责任田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多次在全省性会议上代表省委所作的主旨讲话。在讲话中,他对责任田的性质作了精辟的阐述,对推行的方法、步骤、措施作了具体部署,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细的解决办法。特别是1962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指斥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时候,桂林栖以巨大的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继续推行责任田。
1961年3月14日晚,曾希圣到广州开会之后不久,桂林栖主持召开了全省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针对有人认为“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是分田单干的情况,果断将这一办法改叫“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这一提法虽然是“犹抱琵琶半掩面”,但确实消除了不少人的思想负担。桂林栖特别强调凡试行责任田的社队一定要坚持“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并对“三包”、定产、划分责任田、定工、耕畜饲养、大型农具管理、肥料、种子、育秧、打场、照顾困难户等12个问题,逐一作了分析,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个讲话,对解除一部分同志思想负担、解决实际问题、推进责任田的试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61年9月12日,在省委召开的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桂林栖就进一步推行责任田问题作了专题讲话,主题是总结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强调一是要通过总结经验,训培干部,使他们真正做到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通过他们正确地推行;二是奖赔一定要兑现,着重是超产奖励;三是要特别照顾好困难户,如果我们不特别注意照顾他们,有劳力的户“各顾各”,就会使困难户在生产、生活上发生更大的困难;四是大农活一定要包工到组;五是要加强对大农活质量的监督。为此,要特别抓好“五统一”。
1961年9月21日至22日,桂林栖在省委整风整社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半年来全省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作了阶段性的总结。桂林栖在报告一开头就兴奋地说:“今年3月份以来,我省各地推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到目前为止,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已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74.8%。没有实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不少群众也要求实行。半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对加强社员责任心,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桂林栖说,为了更好地推行责任田,必须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三通”:思想通、政策通、办法通。在长达19700多字的报告中,桂林栖全面地讲述了继续推行责任田的4个重要问题:一是要正确认识责任制的重要意义;二是要正确执行政策;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队、组领导;四是要认真做好各项具体工作。
在讲述第一个问题时,桂林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结合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实际,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必要性,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责任制。桂林栖说:这个办法是吸取了合作化以来特别是高级社包工包产的经验,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把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结合了起来,把包工包产结合了起来,把生产成果和计算奖赔结合了起来。因此能做到责任明确,人人关心产量,讲究农活质量,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高。
桂林栖在讲话中,特别针对责任田推行中有争议的几个焦点问题,作了明确回答:
第一,有些人曾经认为,这个办法是分田单干。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看问题不能看表面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办法的中心内容是加强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形式,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大农具仍然归集体所有;并没有改变产品的分配办法,包产以内的产品收入仍由大队统一分配,社员仍然是按劳取酬。
第P1XcC5d/D9IALjOrSna1pgRBya22p7s0zNW9J4arkck=二,有的人顾虑,这办法可能引起一部分人越来越富,一部分人越来越穷,形成两极分化。从实际情况看,这种顾虑也是没有根据的。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不会因为实行这个办法而扩大。因为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虽然工分会做得多些,超产收入也可多些,但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劳力少劳力弱的困难户,他们的收入比劳力多劳力强的户要少些,但不会少于原来的收入,原因是田间管理工作都是按他们自己的劳动能力来承包的,又有许多照顾。在得到照顾后,还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困难户,则从公益金中给予帮助,或从救济款中给予补贴。他们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第三,有的人担心实行这个办法可能会加重社员的私心和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也是没有根据的。社员包了责任田,一心种好、管好,争取尽量多得超产粮,这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这是私心的话,那么,这种私心与责任心是分不开的,对增加生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要加以教育引导,就能使大家把生产积极性与社会主义积极性结合起来,并能增强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爱护心理,而不会导致对土地的私有观念。
第四,有人认为,这个办法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怕搞了以后再变。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办法是不是要变,要看实际效果来定。如果这个办法确能调动积极性,增加生产,不仅不会变而且要作为一个好的经验,加以普遍推广;如果这个办法不能增产,不利于社会主义,那就不能不变。根据现在各地试行的情况来看,这个办法群众非常拥护,有的大队干部不愿意实行,生产队就偷着实行。有的县原来不实行,现在群众对领导施加压力,不实行不行了。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既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促进生产,是完全应该坚持实行的。
指 导
在大力协助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的全过程中,桂林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推广群众的实践经验,指导推进责任田的发展。
桂林栖为了在他的蹲点县——桐城进一步推行责任田,有多次到桐城说服县委胆子要大一些。他明确指出:“你们县委是否真正承认桐城有‘五风’,如果有,那么实行新办法(即责任田)是克服‘五风’最根本的办法。”一开始,县委对省委的指示进行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面积种植双季稻需要大协作,搞新办法与种双季稻有矛盾。只按桂林栖的要求,在古井、龙潭两个公社搞了责任田试点。在早稻生产过程中,桂林栖到试点的两个公社检查,回县城后,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县委:“桐城在实行新办法方面有点保守,龙潭、古井搞了新办法,早稻长得很好嘛,并没有什么矛盾嘛。”为了用事实说服县委,早稻登场时,他叫县委派一个调查组,省委派一个调查组,同时到一河之隔、条件基本相同的搞了责任田的龙潭公社龙潭大队和未搞责任田的老梅公社老梅大队,进行全面周密的对比调查。省委调查组由省委办公厅李守璋、女作家菡子、副省长黄耀南夫人言行、省科委秘书长曾于等组成。为期10天的调查表明,新办法与老办法谁优谁劣,泾渭分明。搞了责任田的龙潭大队比未搞责任田的老梅大队,早稻单产增产幅度高达27%,事实说明了一切。
不久,桂林栖和曾于又来到桐城。在座谈会上,性情直率的曾于对张安国说:“桐城不大胆搞新办法,我看就是你张安国同志的思想问题。”桂林栖说:“老曾,你的说法有片面性,桐城双季稻面积大,老张有顾虑,可以理解嘛,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嘛!”张安国此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思想认识滞后,故在“双抢”后放开手脚,大力推行。后全县有75%的生产队搞了责任田,当年的午季作物全部包到户,并决定1962年水田旱地全面推开。但这一决定因七千人大会批判责任田而未能付诸实施。
8月初,桂林栖到太和县,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8月7日口授提纲,由秘书吴敬贤起草了《关于太和县推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情况报告》,上报省委。《报告》所述材料,具有广泛代表性。《报告》说:“太和县有81.4%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经过夏收、夏种、夏管的考验,明显的表现是:1、劳动力充分利用。社员说,过去干活是干部挨门找,社员装病老,明是去干活,暗地去睡觉;现在是干活不用邀,个个头里跑,老少都下地,家家闲人少。不仅整个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2、耕畜、农具显著增加。全县实行这个办法4个月时间,已购买耕牛4200头,其中1200头是群众自筹资金买的,大小农具也增加不少。社员说:去年农具往外丢,今年农具往家添。要不是实行这个办法,哪有心肠添加这些东西。3、生产面貌大大改变。一是种得多。去年全县抛荒29万亩,今年除留2万亩晒垡地外,其余耕地全部种上庄稼。二是管得细。秫秫普遍锄了五六遍;黄豆据说1957年只锄一遍,1960年未锄,今年一般锄了两遍,部分锄了三遍;红芋都进行了补苗、拔草、冲垄、翻藤。在解决了大田与自家争肥矛盾以后,各种作物施肥量显著增加。不少地方还发现社员自动出钱买肥施肥、买种补种、买药灭虫。三是长得好。我们在160华里沿途看到,庄稼长得都比较均匀,没有草荒,秋粮作物中秫秫长得最好。往年这里秫秫穗头的基部都是壳多粒少,而今年从上到下都是粒粒饱满。连70多岁的老农都说,是40年来所罕见。山芋秧苗多数也生长茁壮。”
桂林栖的《报告》还说:“开始尽管有几种办法同时并存,在太和县曾经有老办法,有包产到组的办法,有责任田新办法。但实践显示出包责任田确比其他办法有更大积极作用,干部推行这个办法的态度也就由摇摆转为坚决,原来的多种办法也就自然趋向于单一的即包责任田的办法。”《报告》最后说:“从阜阳全区来看,对执行包责任田新办法,凡是抓得早搞得快的地方,夏季生产都搞得较好。亳县因抓得晚,6月下旬才布置全面推行,就很被动,生产搞得较差,全县抛荒21万亩,草荒40万亩,与太和县庄稼生产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现在,亳县县委已感到吃了亏,下定决心全面推行责任田新办法,力争在秋种中摆脱现在的被动局面。”桂林栖这份调查报告,热情讴歌责任田,对增强安徽省委推行责任田的信心和决心,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1962年批判责任田时,这份有重大价值的调查报告则被指斥是“刮单干风”的铁证,桂林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坚 持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议指出安徽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在这个关键时刻,桂林栖于2月3日,以超人的胆识,丢掉一切私心杂念,主持召开了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大胆地与七千人大会唱起了“反调”,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去年在贯彻六十条的前提下,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的办法,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生产发展,增加社会粮食总产量,这是个客观事实。如果说这个办法搞错了,搞坏了,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应该肯定它的作用,既要总结搞得好的经验,又要看到执行中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他明确提出:“凡是已经采用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在抓好‘五统一’的前提下继续试行。”在中央斥责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的风口浪尖上,桂林栖仍然在全省性会议上提出继续推行责任田,这与曾希圣2月9日在七千人大会安徽大组会上婉拒检查责任田有错误一样,充分反映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
桂林栖推行责任田是坚持到底,死不改悔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改组后的安徽省委于1962年3月20日作出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同日向各地、市、县委、公社党委发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通知》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通知》下发后,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争论,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反对改正责任田的意见,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时任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钱让能,他以惊人的胆识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钱让能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报告,正是由桂林栖转到中央的。
1962年7月29日,省委召开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央监察委员会对1958年反右派中被错定为右派分子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平反的决定。我随同桐城县委第一书记张安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天晚上,我陪张安国一起来到桂林栖家中,向他汇报桐城县甄别平反的情况。汇报刚结束,太湖县委第一书记谷志瑞、望江县委第一书记沈去非、宿松县委第一书记彭小聚3人一起也来到桂林栖家中。在大家先后汇报了甄别平反情况后,谷志瑞向他汇报了一个重要问题。
谷志瑞说:“对责任田问题,现在省委下了文件强调要改正,我们想不通,有不同看法。我们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同志对责任田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老钱原来是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有较高的理论水平,随我一同下放到太湖改造落后队,来太湖县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推行责任田时他很积极。现在对改正责任田他很反对。他通过直接推行责任田的实践,认为这是一个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适合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次听到省委改正责任田的决议,他又下去调查,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理论上作了分析,认为责任田不是方向性错误,因此,写了一份给毛主席的报告,请求停止改正责任田。”桂林栖说:“那好嘛,对改正责任田问题我就持保留态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嘛!”接着问谷志瑞:“你们那个老钱报告写好了没有?”“写好了。”“你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我们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共3份,我想交给新任书记葆华同志,但葆华同志刚来,我不熟悉,能不能请桂政委转交给葆华同志?”桂林栖立即说:“可以嘛,你现在交给我,我明天交给葆华同志。”于是,谷志瑞便从口袋里把3份复写的报告拿了出来,交了一份给桂林栖。桂林栖看了标题后,便说:“这个标题做得好,保荐两字用得好。”接着,他又对谷志瑞说:“再给我一份,今晚我要仔细看看。”谷志瑞便又交给桂林栖一份。这时,桂林栖又问谷志瑞:“你看了没有,你是什么看法?”谷答:“我看了,我当然支持老钱的观点和做法,否则我就不会带来送给你了。”后来,大家都围绕责任田问题议论开了,几位县委书记都认为责任田是个好办法,不存在方向性错误问题。大约在晚上10点钟左右,我们辞别了桂林栖。他把我们送到楼下,一再说:“老钱这个报告我明天送给葆华同志,请葆华同志转呈中央、转呈毛主席。责任田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嘛,是真理就要坚持,是错误就要纠正。责任田要由历史来作结论。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嘛!我对责任田还是持坚持态度。”后来,钱让能的报告由桂林栖交给李葆华,后由李葆华转呈毛泽东。
桂林栖对责任田问题坚持到底、死不悔改,还表现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揭安徽盖子”过程中。桂林栖因积极支持和组织推行责任田而遭到批判,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的问题是跟着曾希圣,大搞责任田,要他尽快转弯揭发曾希圣,批判责任田,并作深刻检讨。桂林栖不为所动,拒绝揭发批判。他在1962年4月23日写的2400多字《我的检讨》中,关于责任田问题是这样写的:“我积极推行‘责任田’的办法。曾希圣同志提出‘责任田’的办法我是支持的。我接连开了几次电话会议,积极推行。以后到阜阳地区去还劝涡阳、蒙城推行这个办法,批评亳县不实行这个办法。到怀远说服他们搞典型试验。”只字未提他推行责任田是什么错误。
由于桂林栖拒不承认和拒绝检查推行责任田的“错误”,1963年,他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被调离安徽,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任副院长,被降职使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推行责任田的“重大罪恶”惨遭迫害,被反复揪斗,于1971年8月28日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桂林栖14岁参加革命,效命工农44个春秋,逝世时才58岁。1980年,中央在安排省部级领导班子时,曾对桂林栖推行责任田的情况有所了解的邓小平问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桂林栖现在哪里?”宋任穷说:“1971年被迫害死了。”邓小平听后说:“死早了,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