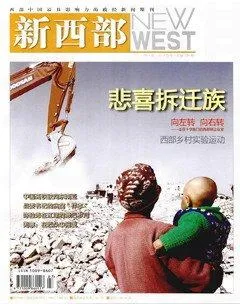任正非:华为还有没有冬天?
对未来的焦虑,近来一直困扰着华为掌门人任正非。
去年年底,一篇题为《传华为“地震”,任正非10亿送走孙亚芳》的报道,引爆了大陆财经界。报道称,任正非为了让儿子顺利接班,以10亿元人民币的“分手费”逼走公司董事长孙亚芳。向来低调的任正非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华为不是我个人的企业,不会走家族模式。”
与外界对华为接班人的传言相比,一番关于任正非对于业务转型的感言,却显得语重心长。“我们已经走到了通信业的前沿,要决定下一步如何走,是十分艰难的问题。我们以前靠着西方公司领路,现在我们也要参与领路了……”这是任正非去年11月底在“华为云计算发布会”上的讲话。
实际上,从2010年初开始,任正非就已经低调地在内部发动“华为20年”经验和教训总结,他的目标直指下一个10年——未来的华为怎么走?
而更为精确的提问应该是:没有任正非的华为怎么走?
“接班人”将会是谁?
可以确定的是,华为下一个10年,“接班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命题。
有人说,若把华为比作一条船,那么任正非就是这条船上经验老到的船长,为华为探方向、定航道。任正非之后,谁带领华为续写传奇?对现龄67岁的任正非而言,接班人问题已成为华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
近期业界对华为“子承父业”传闻风波的广泛关注即是体现。虽然华为已发布严厉声明予以辟谣,但舆论对华为治理结构的关注,并未冷却“接班人”问题,因为这的确是华为需面对的“现实焦虑”。
可能连散播流言者都没有注意到,一则标题为“如果任总退休了,华为的好日子还能继续下去吗”的帖子,从去年初开始就高悬在华为内部论坛热帖头条位置,至今已经一年有余。
其中一条跟帖发布者“达文西”发出追问:“中国企业通病就是没有好的接班人,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到现在也没有很合适的人选,希望华为不要走这条老路。”“达文西”还引用GE韦尔奇启用伊梅尔特的例子,表达了自己作为华为一名普通员工对公司接班人问题的谨慎和担忧:“当别人问及韦尔奇说他对接班人有何评价,他很简单地回了一句‘要是选错了就瞎了我的眼睛’,希望华为也能够这样。”
接班人的问题,让华为曾经坚不可破的“左非右芳”也逐渐出现裂痕。“芳”当然是孙亚芳,她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华为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其主管的市场和人力资源部门对华为的贡献最大。孙亚芳举止优雅,说话和风细雨,讲求平衡,善于沟通。1999年,任正非宣布孙亚芳任董事长时曾说,孙亚芳的最大功绩是建立了华为的市场营销体系。
2010年10月27日,媒体传出消息称,任正非提出让其儿子任平做接班人,孙亚芳因不满离职,华为则赔偿孙亚芳9亿元(还有一说是14亿元)。当日下午,华为发表声明,称这些消息“纯属凭空捏造的谣言,与事实完全不符”。
孙亚芳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任正非。公司虽然还有其他几位常务副总裁,但大家在称呼孙亚芳时都是尊称为孙总。有时在公开场合,任正非也是称她为孙总;而在一些人员任命和文件签署上,只要孙亚芳看过,基本就能通过。
共事16年,任正非与孙亚芳二人合作默契。孙亚芳担任华为董事长已长达12年之久,曾被外界视为任正非最有力的接班人。而在《福布斯》杂志2010年10月6日公布的“最有权势女性”年度榜单中,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荣居榜首,惟一上榜的中国女性正是孙亚芳。
当初任正非提议孙亚芳做董事长,负责外部的协调,自己做总裁,专心做内部管理。孙亚芳在华为的地位和贡献可谓巨大,但“接班门事件”却在任和孙之间竖起了一堵厚厚的墙。
而到底谁是华为未来的接班人,一直都是华为内部颇为感兴趣的话题。
“如果李一男没有与老任分道扬镳,现在会怎么样?”一位已经离职的华为人士说,李一男当时在华为绝对是一个光芒四射的人物,而且年轻,惟一缺乏的是更高层面的经验和历练。
两天时间升任华为工程师,半个月升任主任工程师,半年升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被提拔为华为公司总工程师、中央研究部总裁,27岁坐上华为公司的副总裁宝座——李一男曾被认为是任正非指定继承人。但在2000年,李一男却出走华为,创建港湾网络公司。当时流行的说法有二:一是说李一男出走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任正非的扶持也可以做好”;二是说李一男早已意识到任平将接掌华为。当年有人问李一男,“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怎么会想离开华为呢?”李一男一笑:“哪里轮得到我呀。”
华为内部也在流传另一种说法,任正非正在培育家族势力,儿子当然是他最希望的接班人。
目前,任正非家族有5人在华为任职,其中任正非的弟弟负责华为公司的物业管理,妹妹在1999年之前曾任公司的财务总监,女儿孟晚舟在1995年前后就加入华为,之前任华为财务部副总裁、华为香港公司销售总监、财务总监等,近日接替华为元老之一的梁华成为CFO。其儿子任平在没有被曝光前在华为的最高职务是华为下面一个做配套的子公司老总,如今也渐渐浮出水面。他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先后在华为的市场部、采购部等多个部门锻炼,但缺乏研发和市场管理经验,如今在后勤部门任职……
据传从2007年开始,任正非就不断在公司高层会议上谈及提拔任平的问题,引起其他管理层成员的不满。在去年10月的一次高层例会上,任正非又表示要将任平引入管理层,再次遭到强烈反对。
对于种种传闻和猜测,任正非曾做出回应:“华为有近7万名员工……他们将集体决定公司的命运,怎么可能由一个人决定这个事怎么做呢?华为从创立那一天起,确立的路线就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他还罗列数据说,目前华为主要是由61457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说了算,他们持股98.58%,他自己只占有1.42%的股份。
但谁都知道,任正非才是这家电信巨头的实际控制者——华为没有上市,没有任何大股东和投资者可以约束他。
《华为基本法》对接班人的要求中说:我们要制度化地防止以后公司的接班人腐化、自私和得过且过,华为公司的接班人是在集体奋斗中从员工和各级干部中自然产生的领袖。
产生于1996年的《华为基本法》恰好是华为从创业阶段向发展阶段过渡之时拟定的。有人说,《华为基本法》体现了不少对企业发展阶段的思考,但似乎带有比较明显的决策者个人理念的色彩,甚至有“家法”的意味。不过,在接班人方面,《华为基本法》还是能反映当初华为元老和整个管理层的意愿的。
如今,华为迎来辉煌,此法约束力是否依旧?面对领袖难寻,管理层的用人之道是否应当有所转变?对于如今处于风口浪尖的华为和任正非来说,这些都是很严峻的问题。
惟一能确定的是,华为能否继续它的辉煌,与未来的接班人息息相关。
跻身国际主流供应商
曾有人如此描述华为:“如果你想打电话,就得用程控交换机;如果你想发短信,就得用基站和电话预付卡;如果你想上网,就得用路由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任正非的华为。”
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电信设备,涵盖移动、宽带、电信增值业务和终端等领域。如今它的年销售额已达1491亿元人民币,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为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提供服务,使全球1/3的人口受益。2009年,华为成为继联想集团之后,成功闯入世界500强的第二家中国大陆民营科技企业。
2010年冬,经过10年飞速发展的华为已经跻身为国际电信市场的主流供应商。
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期间在重庆邮电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参与了多项军事通讯系统工程的技术发明。
1987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借了两万元钱,与5位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华为”的公司。公司自主研发出一种交换机,卖给一家香港公司,赚得“第一桶金”。
当时,大陆电信企业为抢占市场而展开了恶性竞争,拥入中国的国际电信巨头则图谋打垮所有中小企业。任正非不动声色地进军“一片蛮荒”的农村,当众多电信企业在厮杀过程中一个个倒下时,华为却慢慢壮大起来。
国际化曾是任正非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成为华为保持高速增长的不二法门。他说,华为不尽快使这些产品全球覆盖,其实就是投资的浪费,机会的丧失。
任正非带领华为走向国际市场还带有强烈的民族情结。他表示,华为必须进行大公司战略,泱泱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通信制造产业。“我们不仅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要走向世界,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希望。”
与国际接轨,实现全面的国际化,是当年华为二次创业的主要任务。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任务要求华为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等等全面提升,达到国际水平的过程。同时,华为的国际化是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为前提的,在与众多国际巨头结成广泛合作时,华为因其技术的先进性,摆脱了对国际巨头的技术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华为与之缔结的合作才是真正平等的、双向的,才是真正的优势互补。“企业的技术能力代表着与合作企业交换许可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技术是华为国际化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该分析人士说。
华为国际化成功的标志是在欧美发达国家立稳脚跟。2003年,任正非做出了一个改变华为命运的重大决定——进军主流市场与主流大公司正面交锋。2004年12月8日晚,美国CNN财经新闻破天荒地接连播发了几条有关中国企业的新闻:联想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华为将为荷兰移动通信运营商Telfort建设第三代(3G)网络,并将为美国NTCH公司承建CDMA2000移动网络。
此前,中国产品在欧美市场主要以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通信信息类高科技产品一直无法进入。华为3G产品在欧美市场成功商用,对欧美通信界和财经界的震动显然非同小可。
“在华为成为全球规模的移动解决方案供应商的道路上,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签字仪式上,任正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华为大规模挺进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实现了在国际各大主流市场的全线突破。2010年,华为销售额突破1500亿美元,国际市场继续成为其最主要的销售来源。
据说,已经67岁的任正非如今仍然奔波和忙碌于全球市场上,他的日程表上时常有一两天内往返于东西或者南北两半球的安排。或许,对这位仍显精神矍铄的老人而言,退休还不是最紧迫的问题。
企业转型最紧迫?
那么,对华为而言,什么是最紧迫的呢?
任正非最新的一次讲话,表明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电信行业正步入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云计算:“如同IP改变了整个通讯产业一样,云计算也将改变整个信息产业。未来信息的广阔包容,规模无比,覆盖天涯,蓬勃发展,风起云涌,烟消云散……多么变幻无穷,多么像云一样不可估量……获得信息需要技术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创新,它的特性决定了,任何人都无力独揽狂澜。”
任正非认为,华为未来1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自身。“过去华为的发展模式相当封闭,即作为面对单一客户的信息设备提供商,但是未来市场瞬息万变,电信业、IT产业、互联网业难分彼此,电信设备商将如何适者生存?”
在任正非看来,一方面,运营商正在面临业务转型,从打造,“电信平台”到打造“综合信息平台”,作为设备商的华为也必须搭上这趟车;另一方面,在电信市场内成长起来的华为,其企业基因、自身资源禀赋等特性将遭遇天花板,如何从“单一制造商”,转型成为“多元制造商”?如何从“电信设备提供商”转型为“信息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商”?都是华为转型所要解决的难题。
“我们愿意积极合作,我们期待基于开放的云平台和各行各业应用服务合作伙伴携手共创未来信息产业的发展。”任正非说。
但开放竞争谈何容易?
回看华为走过的20年,可以说华为胜出的关键在于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跟随者”到“超越者”的角色。但是,未来的华为是要扮演“领路人”的角色。
“领路是什么概念?就是‘丹柯’。丹柯是一个神话人物,他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用火点燃,为后人照亮前进的路。我们也要像丹柯一样,引领通信产业前进的路。”任正非说,华为未来面临最大的挑战是,“领路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对未来不清晰、不确定,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正因如此,华为未来10年的每一个选择,比如接班人问题,比如转型问题,都显得极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