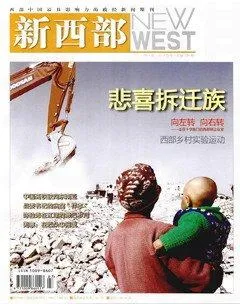嬗变中的中庄村
香泉镇中庄村,这个甘肃定西偏远的山区小村,不经意间两次与国际性气候会议发生了关联,因为贫穷,因为气候灾害。三年前,乐施会在中庄村实施了一个“以社区为本的洪灾和泥石流等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开启了中庄村的变迁之旅。
“要是往年,到这会儿至少下过两场雪了。今年冬天到现在还片雪未见呢!”大巴车司机一边抱怨,一边把一条湿毛巾搭在车内空调的出风口上,说这样能增加点水分,人不会觉得太干。
这是本刊记者去年年底在前往甘肃定西香泉镇的车上看到的情形。
一条近10公里的砂石路,是通往香泉镇中庄村的惟一一条路。这条路还是三年前在香港乐施会项目的帮助下修筑的,此前中庄村村民外出,必须走过一个干涸的河床。
当然,对以“助人自助,对抗贫穷”为宗旨的慈善机构乐施会来说,他们在这个村子想要做的事情显然不只是修路。
断流的魏家山河
“如果一直不下,到明年开春,人畜饮水就是个大问题。”中庄村支部书记马占林显得有些忧心忡忡。
中庄村272户人家,其中有60%住在山上。山上有的人家的井里已经没水,必须到外边拉,一个月花费四、五十元,而这个村全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500元。
时间如果退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泉镇这地方随便往下创个坑,就能见到水。可是,现在有的地方打井,要打到100多米才有水,这还需要借助好运气,不然花费二、三十万元,得到的还是个“黑窟窿”
中庄村人不敢指望还能用井水种庄稼,全靠老天,干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
“干旱对农业的影响非常明显。一般情况下,玉米能长一人高,而中庄村的玉米只有半人高,结出的玉米棒也只有正常的一半大。”乐施会志愿者肖欣对记者说。
肖欣是南开大学政治哲学硕士,主修环境政治,长期关注气候变化议题。她作为乐施会“Ido”使者,2009年两次到过甘肃,亲身感受到干旱对这个地方造成的影响。
而让马占林忧虑的是,近十多年,中庄村的旱象像是越来越厉害了。原来的山上有树有草,除了白杨树,还有少量的杏树、梨树,但现在大部分树都枯死了。
在马占林的记忆中,最近10年发生过四次大的旱情,其中后5年就发生过三次。“我小时候,绕村而过的小河一年四季流着清澈的水,现在只有夏季发洪水时才有,但也只有几个小时的黄泥汤而已。”马占林说。
马占林说的这条河叫魏家山河,过去村里人吃的、用的水都是取自河水,现在只是一条干沟,已断流十几年了。随着这条河的断流,地表水消失了。
水少了,但泥石流却照样有。中庄村一年降雨量只有400毫米,不多的降雨却多集中在秋季,还常常是暴雨。暴雨引发山洪冲向河道,导致泥石流的发生。
但中庄村遇到的自然灾害还不止这些。乐施会在一份评估报告上这样描述:中庄村每年都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主要包括春季的霜冻、干旱,夏季的洪灾、冰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2007年,我们村人均纯收入只有683元,那一年先是旱,收获期又遇上冰雹,几乎没什么收成。”马占林说。
近年来,中庄村先后有100多户移民去了外地,有去河西走廊的,有去新疆的,有的在附近乡镇做生意,开牛肉面馆的最多。
“每家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不可能在这么苦的地方呆着。”乡上的包村干部喇玉虎对记者说,中庄村人均纯收入的20%来自外出打工。
村里来了乐施会
2007年,香港乐施会选定中庄村为援助对象。
当时还有一个村也在争取乐施会的项目,乐施会经过综合考虑后,最终还是将项目落在了中庄村。正像乐施会项目报告中描述的那样:中庄村是香泉镇最贫困的行政村,现有(指2007年,编者注)绝对贫困户15户,59人,低收入家庭73户333人。当地社区村民的生产、生活及当地生态系统都相对脆弱,大多数家庭因受贫困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非常脆弱。地理位置偏僻,一般的国家扶贫政策项目很难争取到,获取外界资助的机会相对较少……
乐施会项目组认为,中庄村以回族居多(占总农户的58%),族群联系紧密,同宗问有相互帮助的传统,村民愿意投工投劳改造村社道路,参与项目的积极性高。加之安定区政府及区能源办正在大力推进以沼气、节能灶为主的环保型能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个项目与政府的意愿能结合起来。
“慈善机构做项目,从项目评估时起就特别注意吸纳村民的需求。”喇玉虎对记者说。
起初,乐施会项目中并没有修路这一项,但村民却希望能加进去,因为修路需要资金多,靠村民自己解决不了,急需外界的援助。
乐施会项目组召开村民大会,给村民每人发5粒豆子,让他们投票选出最急需解决的五个项目,最后确定的是:修路(与防洪堤结合在一起),建50个暖棚,配套50个沼气池,荒山造林1000亩,给村民100个太阳灶。
当时,有80户村民报名参与项目(建暖棚和沼气),经过村民大会的讨论,最后确定了50户。
项目组特别尊重村民的意见,建沼气池、暖棚时,修建标准和补助金额都是经过村民大会商讨出来的。“选择太阳灶类型,也按村民的意愿办。”喇玉虎说,“政府项目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有什么做什么,只能执行,不能改。经过与乐施会的配合,政府也开始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也在改进。”
随着项目的推进,中庄村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在村民赛文华家门前,有一个60立方米的氯化青储池,里边储存的秸秆够他家的牛、羊吃半年。赛文华说,当地人养牛养羊主要喂秸秆,氨化后的秸秆和干草比,养分不会流失,育肥效果好。
青储池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酒香,切碎的秸秆还能看出一些绿意。“牛呀、羊呀,吃了这个长得好得很!”赛文华的父亲说道。
“最关键的是这项技术简单,只要把玉米秆等秸秆切碎,在一层一层压实的同时,淋上按一定比例配置的尿素液体,再密封上30天就行。”马占林介绍说。
赛文华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他在高处建了一个蓄水池,用管子把水引到牛槽上方,龙头一开,水就直接注入到牛槽里,不用费力气。
“我腿有残疾,担不了水,所以……”赛文华解释说。
2001年的一天,赛文华去山涧拉水,那时家里还没有打井,拉水的路都是陡峭的土路。一个不小心,他摔了下去,家里惟一的男劳力就成了残疾人。村里像赛文华这样的残疾人有好几个,都是因为拉水摔残的。
赛文华家的标准暖棚里养着5头牛,2010年卖掉了一头牛犊。为了节约地方多养牛,他还把木立柱和木梁都换成了钢结构。
赛文华还养着12只母羊,一年能下20只羊羔。一只羊羔能卖300元,一年下来能收入6000元钱。这样的收入在中庄村就算富裕户了。
但赛文华拖累也很重。“现在供学生费钱得很,一星期光饭钱100元都不够。”赛文华有两个儿子,一个上高三,一个上高二,吃饭都是在外面买着吃。
“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天天和牲口打交道。”赛文华的理想是把儿子都送进大学。
赛文华是中庄村第一个加入乐施会项目的农户,因而更多尝到了项目的甜头。为了多挣钱,他还在地里搞起了试验——种大棚菜。2010年种的西红柿、辣椒、黄瓜都长的不错,自己家吃菜不用买了。他的想法是让村民不出村就能买到菜,自己也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马占林的新期待
“乐施会刚开始在村里搞项目时还是很难的。”马占林说。
起初,召集村民开会都是一个问题。有村民不愿意去,马占林甚至要用自己的摩托车把他们接到会场。现在,村民一旦得知有什么项目,没有不积极争取的。
在二队一个姓陈的农户家,记者看到有几个人正在盖牛圈。陈家的主妇告诉记者,前几年乐施会在村里搞项目时,他们没参加,现在看到改了圈的人家,牛羊冬天也长膘,能早出栏,正好今年政府在村里搞“一池三改”(建一个沼气池,改厕、改圈、改灶)项目,他们家这次争取到了。
建这样一个宽6米、长10米的圈,需要投资3DOO元,政府补贴300元,在贷款上还有一定的优惠。沼气池则由政府全额投资,建一个需要7000元。
陈家原来用的是土厕,现在改过的厕所,地上贴着瓷片,比原来干净多了。
记者在已经改过灶的村民家看到,用沼气烧一壶水只用十多分钟。一说话就有点害羞的小陈说,用沼气做饭干净卫生省时间,还可以把秸秆省出来当做饲料,过去的秸秆都被当作燃料烧了。
小陈就是当初马占林用摩托车硬拉到会场的村民之一,如今他已是乐施会项目培养出来的典型。用马占林的话说:现在小陈是只要有项目就参与,2010年做了青储和地膜玉米。
最让马占林高兴的是,中庄村因为乐施会的项目也渐渐得到政府的重视。“在乐施会这个项目之前,村里基本上争取不来什么项目。现在政府的项目也开始有了。”马占林说,2009年,村上争取到了一些小项目:20座沼气池,20座圈舍改造;2010年已建成了30个青储氨化池。
2009年,中庄村还争取到一个300亩梯田的政府项目。有一段时间,推梯田项目停了,舟曲发生泥石流后又恢复了。“梯田的好处是产量高,利于机械化操作。现在,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外出打工,也需要机械耕作了。”马占林说。
通过这个项目的锻炼,马占林2010年还考上了公务员,虽然工作性质没变,还是中庄村的支部书记,但每月能领工资了。
“这个村要有大的发展,必须借助项目拉动。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这是全村上上下下的一致看法。”马占林告诉记者,他现在考虑的主要事情,就是怎么给村上争取更多的项目。目前他们申报的大项目有硬化进村道路和退耕还林。
砂石路把原来的土路修宽了,但遇到暴雨还是容易被冲毁。水泥路1公里投资需要20万元,10公里路就是200万。同时,村民耕种的90%耕地都是70度的陡坡地,所以就向上面申报了3000亩退耕还林项目。
“希望不大吧。”项目能否申报成功,马占林没有多少把握。
在马占林看来,实施三年的乐施会项目给中庄村带来不少变化,但有些工作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如果有后续项目,效果就能更好一些。”马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