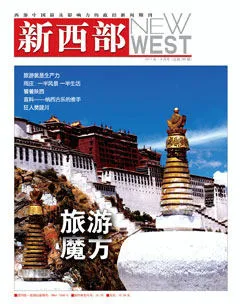狂人樊建川
他用一辈子的收藏,读懂了一场战争。
当有钱人收藏明清家具、宋元字画的时候,他却在收藏这个民族曾经的苦难和精神。
他把多年经商所得全部砸进“民间博物馆”这个无底洞,建起了中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在和数以万计的抗战文物默默交流的过程中,他对这场战争有了亲历似的感觉。
“用一辈子的疯狂和野心,成就终身的良心。”樊建川曾在朋友面前这样坦诚心迹。
抗日战士后代的心愿
一个援华美国老兵,看了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非常激动。走进专门介绍美军援华的飞虎奇兵馆,他嚎啕大哭。轮椅里的美国老兵90岁了,泪腺早已萎缩。那种没有眼泪的干嚎给樊建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樊建川一不小心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抗战博物馆馆长。
在其丰富的人生履历表中,收藏是贯穿始终的线索。他最早的收藏是幼儿园老师的评语。9岁那年他收藏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1979年考入军校后,他“捡到的”最多的藏品是毛主席像章和语录,还有从朋友家“讨来”的一枚八路军臂章。毕业时,他有了几大纸箱子的“财产”。
樊建川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曾有11年的兵龄。这使他对于战争有一种天生的关注欲望。他说:我的父辈是在面对面的拼杀中认识“皇军”的,我们这代人是通过电影《地道战》、《小兵张嘎》认识“皇军”的。而我的女儿,正享受着日本的科技产品,至于“日本鬼子”似乎只是个遥远的传说。人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祈祷和平,樊建川则选择了“收藏战争”的方式。
他的抗战藏品,有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透过文物那僵硬的躯壳,他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对那场战争有了亲历似的感觉。
“听听樊建川讲他自己的故事吧,那是一部传奇。”作家魏明伦如是说。占地500亩、四个大系、30个展馆的建川博物馆如今正是这个传奇的实证。“他以一己之力,倾心挽留历史的背影”。樊建川的合作伙伴这样说道。
为和平收藏战争
2008年4月,崔永元路过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他在门口买了票,悄悄进去参观。夕阳西下,站在壮士群雕广场上的崔永元,面前一个由202名抗日将士的铸铁雕像组成的方阵让他觉得非常震撼。这支威武之师是由国军、共军、地方军,共同组成的。有一个瞬间,崔永元觉得广场上那些抗日将士好像都活了。
54岁的樊建川曾经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若干年后,他最看重的仍是自己的“士兵”身份。“后来的许多身份都是附加在当兵的这段经历上的。”他坦言道。
1976年12月,两支驻守内蒙古边防的部队来川征兵,在宜宾近郊插队当知青的樊建川坐不住了。据说因眼睛近视,他在征兵时蒙混过关后被人检举,他不甘心,找到接兵军官,毛遂自荐表演了一番吹拉弹唱手艺,又被奇迹般看中带走。
内蒙古的军旅生涯异常艰苦。樊建川颇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机会。不但成为特等射手,还当上了学雷锋的标兵。他收藏的1978年10月14日星期六第三版的《解放军报》上,记录了自己当兵时的光荣:“一个来自四川宜宾的小战士,樊建川,他父亲当年在贺龙部队当炮手,小樊入伍时,父亲对他说,你去的正是我和我的战友战斗过的地方。那儿艰苦,你要是个软蛋就去哭鼻子,不过,我希望你能做个坚强的战士,到风雨里闯一闯。可是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在家连面包都不想吃的小樊,现在吃起馒头五、六个,体重由一百零几斤猛增到130多斤。他晃起紫铜色的臂膀,一气能打200多锤。他学雷锋,做好事,立了功,戴上了大红花。”
转业后,樊建川因在国家级学术刊物连续发表文章而被上级看中,5年内完成从基层办事员到宣宾市常务副市长的升迁。官至宜宾市常务副市长时,他却挂印而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官的收入养活不了收藏”。
樊建川收藏抗战文物的激情其实是被一部《血战台儿庄》的电影点燃的。
1986年,杨光远导演的《血战台儿庄》由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宜宾的年轻人樊建川看到了它:中、日血战的战场上,一座监狱被打开,长官喊“你们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有种的,跟着我杀鬼子去!”犯人们冲出监狱,抓起武器,向日军杀去。川军师长王铭章率7000名川军死守藤县,王高喊“中华民族万岁”壮烈殉国。樊建川热血沸腾,他决定搜寻和考证川军事迹。
当樊建川爬梳史料,得知在八年抗战中,川中有300万名将士出川御敌,国殇64万名的悲壮往事时,他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开始了一项寂寞的工作:寻找抗战川军遗留在世的实物。他找到了很多。有刘湘、刘文辉赠给下属的佩剑,有川军的烟袋杆子,有川造手雷,有一个抗日的国民党老兵在1966年遭遇不公正对待时烧制且题满文字的粗陶杯……
此后,樊建川不只是对川军,进而、对所有与抗日有关的文物都必欲获之而后快。
樊建川形容这个“越陷越深”过程就像:“一个蚂蚁围着一只苹果转,刚开始不知道苹果的滋味,咬个洞就进去了,越吃越香就吃到心里去了。”
没有硝烟的战场
35岁辞官下海的樊建川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企业。最辉煌时,他的公司曾做到全省前几名,上过中国富豪榜。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国最富的500人里就有樊建川一个。腰缠万贯后,他开始大规模地收藏抗战文物。
樊建川形容自己早年跑文物市场“如手枪歼敌,一个个瞄准、放倒”。后因力不从心,遂发展线人“机枪扫射”。他在全国建立起由几百人组成的寻宝网络,一有值得收藏消息,他就在第一时间前往。
“很多文物,我第一个看到,第一个接触到,然后每天都会有多人打电话,告诉我哪儿又发现了八路军的什么资料,哪儿又发现了什么汉奸的照片。”这种闻风而动的状态,伴随了樊建川十几年的收藏生涯。
1996年,樊建川旅日时购得上千本二战画报《支那事变画报》、《武汉陷难画报》、《跃进之日本画报》以及上千张日军明信片。这些资料让他大为振奋,其中披露了大量人们尚不知晓的真相,于是他发动在日本的线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把日本人称之为“二战品”的文物集中收购,造成了日本文物市场上抗战文物在短时间内忽然大规模消失。“与日本人争夺抗战文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樊建川义正言辞。
2002年冬天,樊建川去了一次靖国神社。这次经历给他带来了强烈的震撼。靖国神社是一个丰富的战争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诸如大炮、战刀、自杀式飞机甚至潜水艇等战争文物。“其中还有完整的近300份军人遗书,当时中国死伤了那么多战士,但是今天想找到300份遗书是很难的事,我们遗忘的东西太多了,需要找回的东西也太多了!”这次亲身经历,让樊建川坚定了从事抗战文物收藏的决心。他想通过收集文物,展示文物,拯救文物,让世人记住战争的刀光,血腥,惨烈。
多年的收藏生涯中,“常有意外惊喜”,樊建川视为“冥冥中的缘分”。
樊建川很早就听说天津有个叫王襄的老先生收藏了一套完备的“鬼子战地日记”。这部日记是王先生的父亲留给他的,68个春秋风雨变故,“鬼子战地日记”完好无缺,密密麻麻记了8大本,与日记内容互证的还有他自己的影集,共有208张照片,是日军留在中国的血证。王先生一直想把它卖给卢沟桥抗日战争博物馆,博物馆也非常希望有这份珍藏,可惜,价钱谈不拢。得知樊建川正筹建全国最大的抗战博物馆,老人便托人主动与樊建川联系。
樊建川当晚就飞到天津。多年的收藏经验告诉他,这些东西是真品,而且旷世难得。樊建川当即掏钱买下了。他不想让这批最真实最直接地反映抗日战争的东西再流浪。“我不知道它会再漂到什么地方去。”樊建川说。这部《荻岛静夫日记》后来被国家文物局鉴定后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金银铜铁木头,纸片,床单,报纸,镜子,我全部都要去看,几十年我看了这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经验,很多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面对每件文物,他能迅速估量其价值。这方面樊建川流露出商人的精明本色。
如今,很多人愿意为樊建川的博物馆增添新证。重庆的李幼霞老人捐出了一套陪嫁品和梳妆台,这个梳妆台见证着李家在重庆大轰炸中失去的三条人命,它上面有三处弹痕;四川省广电局捐出了川军抗日名将邓锡侯将军的办公家具:原日军第59师团45中队军营盐谷保芳第15次来华谢罪时,向建川博物馆奉上了一把日本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和三件军服;2003年9月,陈纳德将军遗孀陈香梅来川看援华美军旧物,她唱起了《满江红》,并向樊建川保证:“我会丰富你的收藏。”
每一件文物的归来在他都像迎接久别的亲人。樊建川经常激情四溢地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动情之处,泪洒衣襟。夜深人静时,他常常一个人独自面对那些文物。“它们带着那场战争的印记和气息,来到我面前。我仿佛能看到它们要张口说话了。”樊建川不止一次表达他的这种感受。
为藏品找一个家
“我会盖房子,而且我也有藏品。博物馆不就是把藏品装进房子里给大家展示吗?”
2004年是樊建川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为了给自己收藏的诸多抗战文物找一个家,这一年,大股东樊建川力排众议,由集团公司投资两亿元,在大邑县安仁镇开建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
大邑距成都市区约五十公里,曾以大地主刘文彩蜚声蜀地。为了打造“建川博物馆聚落”,他将镇上二三十座旧时地主的豪宅大院,一口气买下了10多座。如今这里最大的“地主”是樊建川,他的“庄园”比刘文彩当年的庄园要大很多倍。
“开始没有想过要办个博物馆,觉得不可能。”2000年,樊建川在省博物馆办了个抗战文物的展览,2001年他把这个展览拿到卢沟桥抗战博物馆去。卢沟桥是纪念中国抗战顶级的殿堂,在那儿他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他们的好,这才有了自信。
2005年8月15日,一座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博物馆在四川大邑安仁镇向世人开放。建馆初期,资金、经验都缺乏,费用比预期增加了两三倍,花了5个亿。因为没有先例,前后经历了20多遍审查。所幸,有关部门开明地让樊建川揪心的5个馆全部开了,特别是大陆第一个国民党军队抗战馆开馆,赢得了海内外广泛赞誉,连战、马英九后来都为该馆亲笔题字。
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有8个分馆,每个分馆主题鲜明,风格各异,由国际知名的设计大师“捉刀”设计。日本籍国际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主动请缨设计侵华日军分馆。矶崎新早就想设计一个建筑物来表达因日军侵华,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歉意。他对樊建川表示:“你不给钱我也做。”他说:“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有好的未来,需从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博物馆是沉默的沟通使者。”
通过壮士广场矗立的雕像,安仁镇上的少年开始记住了国共两党抗日将领的英名。创作之初,雕塑家的年轻助手们已开始研读和感悟那些本不该被冈尘遮掩的民族英魂。建这样—个壮士广场,樊建川当时心中的范本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阵仗”。
大部分参观者对建川博物馆群落的海量藏品所震憾。参观8个馆,要步行10公里!如同在看一部抗战大片。馆内,处处有细心的提示:“嘘!别盖过历史的声音!”、“我们不说话,让历史说话!”
同样带给参观者视觉冲击力的还有樊建川策划的“手印广场”,他收集了3500个抗战老兵手印印在玻璃钢上。半个多世纪前,就是这些普通庄稼人的手,挡住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
“当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压缩为一个个数字时,这是可悲的。抗日战争‘国殇3500万’,‘重庆大轰炸死伤26万’,这都是些什么概念?那都是人命,都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悲惨故事啊!”樊建川希望自己的博物馆能通过丰富的馆藏,让这段悲壮的历史不停留在形容词上,变得真实可感。
让民营博物馆“活”
在房地产市场的上升期,樊建川把钱和精力都投到了博物馆上,对他人而言多少有点不明智,但他却从未后悔:“因为时间等不及了,等我再赚更多钱来完成时,那些历史的印记,那些老兵,那些一件件令人心痛的记录就再找不到了,记忆消失是很快的……”
博物馆刚建立时的确困难重重。当时,樊建川已经砸进去了3.5亿元,几乎耗尽他下海经商十多年来的全部收益。而他持股50%并任老总的成都某房产公司,年利润为5000万。弹尽粮绝之时,他甚至卖掉了7000平方米的公司办公楼。
樊建川的博物馆也遭遇过门可罗雀的尴尬。最夸张的一天,一张门票都没有卖出去。负责经营的主管跟他说。“要不他自己掏钱买张票吧?”很多人质疑他的做法,怀疑他的目的。有人说他是“樊傻儿”。一个私人老板建这么多博物馆干什么?纯粹“烧钱”。
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一度担忧自己会死在博物馆盈利之前。“儿子还没学会谋生,老子怎能放心阖眼?”这种忧虑折磨了他很久。2007年,50岁的樊建川立下遗嘱,身后将把博物馆遗赠给政府。“从那刻起就不怕死了,因为我死了博物馆也有人管,它们有生命、有意义了。”多年的收藏将有更为久远的藏身所在。这让他觉得“心安”。
“我们不能牺牲,我们要做榜样,国家能建博物馆,民间也能建:国家靠财政运转,我们靠市场也能运转。”樊建川在暗中跟自己较劲儿。
惨淡经营多年后,从2009年起,博物馆终于开始实现盈亏平衡,“能养活三百多人,商业模式做出来了。”现在这个博物馆可以和文化产业相结合,可以和旅游产业相结合,它已经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它能够自己谋生了,甚至还略有盈余可以继续发展。这样交给国家时,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不是包袱。
让樊建川最感欣慰的是:他发现好多年轻人会来这里。一些情侣自驾游到这里住两三天,一天看两个馆,然后大家摆龙门阵、喝茶。当建川博物馆以中国“文革”、抗战、民俗和地震四大主题裂变为30个分馆,更多的馆带动了更多的商业空间。客栈、餐厅、夏令营、古玩店、旅游商品店等等,樊建川设想的“以商养馆”的模式正在逐渐形成。
樊建川最看好的还是自己那800多万件文物,他认为那是垄断性的资源。“虽然暂时看来我们退出房地产行业少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我把博物馆做成了一个拒绝竞争的行业。我挖了一个很大的沟,别人都靠不进我。”
“博物馆‘活’好了,才能指望它发挥功效:让所有国人多看看,多想想,对那场战争遗忘得慢些,再慢些。”樊建川理想中的博物馆更像一个szzDyAAeQCk/IgDkmc0nMag7wKXNDkEtTppOS5aYHmQ=超市。去掉一些神圣化,他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将它看作是一个平常的东西。“平均每一个馆花7块多钱,真的是价廉物美。”
收藏民间记忆
一个人有自己的记忆才能不断成长。小时候母亲告诉樊建川:铁烧红了别摸它,很烫。但他不相信,非要摸,被烫得不轻,以后他就再也不摸了,这就是一种记忆了。
别人热炒古董,樊建川的目光却被现代中国牢牢勾住。他收藏的民间记忆大多带着一些惨痛,教训,启示,和不能遗忘的重量。他想办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时机一直不成熟。“离‘文革’结束时间还太短暂,就像拍照时太近无法对焦,无法把眉目看得清楚,所以恐怕要再等二十年才能理智客观地看待‘文革’。”
他先建了一个“文革艺术品陈列馆”。其中包括1个广场和12个分馆,分别是“记忆”(1966-1976)雕塑广场和“文革”瓷器馆、像章馆、票证馆、镜鉴馆、座钟馆、知青生活馆等。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博物馆”,但仍以一种不那么尖锐的方式,首开先河,开始正视和记录那一段历史。
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121件。在他那20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堆满了目前还不能展示或陈列的藏品。其中有近百吨的“文革”期间报纸和以吨计算的“文革”传单,几万本“文革”日记、几十万份检讨、十余万张照片、上万部电影拷贝、上万个座钟、百万枚像、几百万票证等。当人们大量丢弃旧物,销毁文革记忆的时候,樊建川却在拼命捡“破烂”,一捆一捆地捡回来。
《唐山大地震》开拍前,冯小刚专程来借道具,一进库房就乐坏了:“比电影道具厂还要丰富得多!”最终,他运走了整整两个集装箱。
“将来要想看这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还得到我们的博物馆聚落来!”樊建川雄心勃勃地说。
54岁的樊建川依然奔忙在自己的博物馆具体事务中。员工们说,从文物、装修、陈列到找钱,他都亲力亲为。对自己曾遇到的困难他轻描淡写,“所有困难与我享受到的喜悦比,微不足道。”
如今,他的收藏每天都在增加,古旧的物件他收,新发生日意义重大的他也收。
“别人看到那么多文物,头大,但我看到这些东西就很幸福——每天我到壮士广场上走一圈就会有使不完的劲。”最艰难的时候,樊建川也会失眠,也会有承受不了的感觉。“但当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那种阳光的感觉就会使心里很亮堂。”
在他的规划中,建川博物馆还将有十几座新馆相继落成,届时,整个安仁古镇将以世界级博物馆小镇的形象傲然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