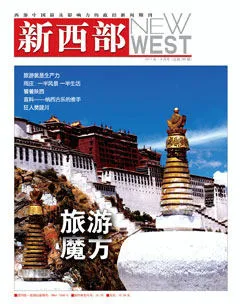周庄:一半风景一半生活
鼎盛之时,弹丸之地的周庄一日之内数万游客鱼贯而入,“就像拥挤的火车”。以政府为主导,引导老百姓积极参与——周庄保护古镇的模式,值得西部人多多借鉴。
23年前,为了保护周庄的古建筑,庄春地干起了“旅游”的活儿。
那时正是东部乡镇企业起步阶段,庄春地的做法被指为“不务正业”。但是,他带着一股子傻劲儿,硬是趟出了一条被称为“周庄模式”的古镇保护与发展之路。
“说我是疯子也好,说我是神经也好,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支撑我的一个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要把古镇保下来。”庄春地说。
古镇保卫战
62岁的庄春地从未怀疑过的是:没有旅游,就没有如今保存这样完整的水乡古镇周庄。这位前周庄镇镇长,也是周庄旅游公司的掌门人,现已退居二线,担任名誉董事长职务,但周庄人仍然喊他“庄镇长”。
周庄的旅游业是从修复沈厅开始的。
沈厅是明代巨富沈万三的旧宅。据说沈万三富可敌国,曾出资帮助大明皇帝朱元璋修复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墙,后因富获罪,落得个流放边陲、客死他乡的下场。
“1980年,我当上周庄镇文化站站长,因为工作的缘故,结识了一些文化人。一天,一个戴深度眼镜的人看完周庄后跟我说:‘那个沈厅不亚于孔府!要保护起来。’这句话在我心里重重地撞了一下。”庄春地说的那个“戴深度眼镜的人”,便是山东大学教授潘群教授。
庄春地决定修复沈厅,可是,这个昔日闻名的豪宅,正轮番被各种各样的乡办工厂占用,已是一片破败,连一扇完整的门窗都没有。
“更让人伤脑筋的是,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站长,怎么可能有钱去保护沈厅?”庄春地像个乞丐一样,到处去“讨”钱,从犄角旮旯里到处寻找匹配的瓦片门窗,从苏州购置拆迁废弃的木料。当别人都在想着如何发财致富时,他却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修复这些破烂玩艺,这让周围很多人感到无法理解。
1986年,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阮仪三第一次到周庄来考察时,带着6名学生,坐长途汽车到“芦墟”,没赶上当天的船,第二天又遇上风大,船不开,第三天才到了周庄。
这7个人住在一间连厕所也没有的小旅馆里,庄春地把他们接到了镇文化站。阮仪三惊喜地发现了周庄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向周庄镇政府提出了“保护古镇、建设新区、发展经济、开辟旅游”的十六字方针。庄春地如遇知音,和专家们一起用皮尺量地,作出了“保护老区、开发新区”的具体规划。
1988年,在新任镇党委书记朱兴农的支持下,庄春地出任周庄镇旅游公司经理。他一方面跟文物部门争取资金,另一方面通过门票和旅游收入来保护古建筑。
1989年,修复后的沈厅卖出了第一张6毛钱的门票,周庄旅游迈出了第一步。
繁荣与困惑
没用多长时间,周庄就从一个破败的村镇变成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也成为将旅游、经济、古镇保护结合的典范。许多人把周庄的兴起概括为“周庄模式”。
鼎盛之时,弹丸之地的周庄一日之内数万游客鱼贯而入,庄春地将其形容为
“就像拥挤的火车。”游客则向他抱怨:
“我现在要进周庄看一个景点,将近一个小时还没进去。我脚下踩的一个砖头、石头,什么材料我都不知道。”
在庄春地看来,周庄模式的核心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古镇,用旅游来保护古镇。“必须要动员老百姓来保护古镇。”也就是说,允许老百姓开店铺,进行商业性开发与维护。
开发初期,有钱的周庄人不愿住在
“四面不通风,到处黑通通,方便用马桶”的老房里,没钱的老百姓无力维护既有的旧建筑,只能拆拆改改。庄春地意识到,古镇保护和发展必须要跟百姓的切身利益相结合,而只有通过旅游经济拉动,才能使老百姓意识到古镇的价值所在。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周庄的老房子真的变得值钱了,当地人也渐渐培养起一种自觉的保护意识。“中国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三年不抹油要毁掉的。屋顶也是,麻雀要筑窝、老鼠要吃麻雀、猫要抓老鼠,它们都在屋顶上活动,一年不捉漏,房间进水变潮湿,滋生白蚁,房子就塌了。抹油、捉漏,这些维修用的钱,都要从旅游收入里来。”庄春地说。
1998年初,周庄所有景点实行联票制,一张30元的联票可以游完整个周庄古镇。
“里面有老百姓生活的地方,你们怎么能卖门票?”虽然质疑声不断,但从这一年开始,周庄的旅游收入每年都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4年,周庄仅门票收入一项就突破了6个亿。
不过,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商业化渐渐给周庄带来了烦恼。“现在人多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什么商业化啊,污染啊……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我认为,当商业味出现了,就说明你保护得好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去了,这样才有钱去保护。”对于诸多因爱而恨的批评,庄春地也吸纳,也改进,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旅游的错。他始终相信,是旅游保住了周庄古镇的面貌。“中国的古城镇保护,必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哪个古镇如果没有商业味,那这个古城镇保护就毁了。”
曾有人问庄春地,周庄的未来会怎样?庄想了想说:“周庄不会永远搞旅游,它最终应该是一个最适合人居的地方,一个永远的‘中国第一水乡’。”
在风景中生活
周庄的老人依然生活在他们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里。
弄堂口,古旧的木门上,漆着两行白色的字:“居民住宅,游客止步。”生疏的字迹,默默讲述着周庄人如今的尴尬。
起初,周庄人颇不适应这样的生活:走过的游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你正在笑还是在哭,他们都“咔嚓、咔嚓”全部拍下来:你刚想坐在家里清净一下,突然之间一个团队经过,导游摇着旗,在喇叭里对着游客大喊,一帮人走后又是一帮人……
梯云桥下居住着一位老人,走过的很多游人,都要冲着他喊一声“喂”。大多时候,他都是闷声不搭理,偶尔瞪着眼睛提醒闯到面前的游客:“你是不是应该喊一声‘老先生’?”
老人身边的梯云桥被导游改了名字。“这是‘外婆桥’,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是在这里拍的。”每当桥头传来这样的声音,老人在心里默默纠正一遍:是梯云桥。尽管如此,“梯云桥”这个名字还是慢慢被人忘记,就连桥下的饭店也挂上了“外婆桥”的招牌。
周庄人渐渐习惯了这样的日子。
兴致好的时候,外婆桥下的老人会热情地向年轻的游客推荐自己心中的“经典镜头”。他指着门前的小路,叮嘱游客一定要从斑驳的白粉墙和清澈的小河夹击的角度取景,那青石砖铺成的小路是一条婀娜多姿的曲线。他学着导游的口气对年轻人说:“没到过这里就没有来过真正的周庄。”和大多数周庄人一样,老人年轻时从门前这条小河乘舟而上,外出谋生,退休后回到家乡,过起了怡然自得的生活。在他黑洞洞的老屋里,传出江南戏曲独特的曲调。
只有在清晨,周庄人才依稀回到过去的日子。街面上大多数的商铺还没有开门,穿着背心裤衩的原住民,拎着小菜从悠长的小巷深处走来,拐过一座小桥,消失在对面的窄巷里。对原住民来说,那是一天中最安宁的时光。
吃完早饭,70岁的朱三官悠闲地漫步到隔壁的“周庄人家”客栈,像旧时走街串巷一样。不同的是,他现在是在“上班”,被旅游公司“雇”来打理这家集体客栈。他每天和游客聊聊天,闲时在小院里唱唱苏州小调,晚上还要在一台大型演出中亮个相,这是老人一天中重要的娱乐活动。“我演了5年了,在《荡湖船》里客串一个船夫的角色。”朱三官说。
住在一条僻静小巷的朱蓉初老人,是周庄旅游公司第一代讲解员。退休后,他和老伴儿在家门口摆了个卖“熏青豆”的小摊。不大的两层小屋,电风扇兀自转着,墙上挂着一副颇有意境的周庄夜景图——暮色幽深的小巷里,那个坐在巷口拉琴的年轻人,竟是当年的自己。原来,周庄旅游公司当年搞摄影大赛时,朱蓉初给一位摄影家当过模特,照片获了奖,摄影家便送了他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个性开朗的老人和游客一攀谈起来,便忘了自己的小生意。老人说,“下次来,你到门口给我打电话,就说来看朱蓉初老爷爷的,不用买票。”
“周庄有你在,真好。”
周庄的变与不变,在三毛茶楼里一目了然。
张寄寒是土生土长的周庄人。1989年春天,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到周庄,那时张寄寒是周庄镇文化站的干部,由此结缘。“周庄有你在,真好。”当年三毛在信中的一句话,老人如今用一辈子来守候。
张寄寒曾写过一篇《三毛在周庄》,在海内外发表后,一个台湾青年把他的文章和信送到台湾去。三毛给他回了第一封信,后来是第二封,第三封……就这样,他们结下了友谊,直到1991年1月三毛去世。3年后,张寄寒在周庄开了这家纪念三毛的茶楼。
旅游给周庄带来的变化,张寄寒都看在眼里。
“三毛来的时候还是摆渡,桥还没修好。她看到这个摆渡开心的不得了,而且渡口的两岸正好油菜花盛开。她摘了一把油菜花,捧在脸上,闻了好久好久。”张寄寒回忆道。
在周庄,4条河道交叉形成“井”字形,将古镇分割形成8条街道。在“井”字形的河道上,有15座式样不同的石桥。“以前的河道就像现在城里的马路,那时,通行在河道里的船,船夫卖菜、卖鱼虾、卖稻草……夏天,一出家门就可以在市河里游泳,水清澈见底。”
上世纪90年代,张寄寒在文化站专门接待从全国各地来拍电影的人。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到老百姓家借东西,有时候忘记还了,老百姓便说,“不要紧的”。5年后就不一样了,要借一把壶,老百姓说,“可以的,一天十块。用一天算一天。”
随着旅游开发,张寄寒感觉小镇淳朴的民风在一点点消失。他时常感叹:“三毛现在活着的话,不要来周庄了。”
尽管如此,老人依然每天开店门,关店门,端茶倒水,从窄窄的楼梯跑上跑下。只是为了能守住这个茶楼,这片净土。他说,想把三毛的精神永远留在周庄。
和每个周庄人一样,张寄寒也希望周庄能保存得更好,更古老,没有商业气息。他听到周庄老百姓时常埋怨,河里水脏了,道路不宽了。但是有的时候,张寄寒看看楼下那个很老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出来,晚上6点才回去,坐在家门口卖拨浪鼓,每天收入几十块钱。“不搞旅游的话,她有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韩俭康的选择
周庄旅游公司副总经理韩俭康向记者介绍,整个周庄镇从事旅游服务行业的总共7000多人,有300家饭店,200家工艺品商店,200条小摇船。最让他自豪的是晚上的大型实景演出,200多人的演员队伍中,一半来自当地农民和渔民。在他看来,整个周庄旅游倡导的是一个大的和谐,这跟其他景区是完全不同的。
韩俭康总是把周庄比喻为苏州的“女孩”,娇小玲珑,十分端雅。然而,2005年,这个“女孩”却让他一度失望地离去。
“人太多,游客的满意度肯定就差了。但每一届政府都强调这个景区多少人次,好像大家都不愿意从游客的舒适度去考虑。”
这正是曾经让韩俭康头疼的事情。他认为,周庄的价值不应仅仅体现在游客的数字上。“如果200万人在周庄的消费超过300万人,当然200万人更好。但是这个靠什么?靠自己的产品去吸引人。”
但是,这种转型的思虑,韩俭康无法靠一己之力达到,重压之下,他产生退意。2005年3月1日,他递了辞呈,出走乌镇。
“周庄掌门人跳槽乌镇。”一时间,媒体炒的沸沸扬扬。第10天,周庄遭到旅行社集体抵制,老百姓开始骂街,时任周庄镇党委书记压力很大,“三顾茅庐”找到韩俭康。20天后,韩俭康重新回归周庄。
“我当时走这一步,真是乌镇的理念吸引了我,不是他们给我钱多。”韩俭康坦言。
出走,回归。韩俭康收获了一个新的眼光。打造多年的周庄品牌尽管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内在的生生不息,却是周庄最宝贵的财富。“老百姓的生活,无法复制也无法编排。周庄能够到今天,我非常庆幸。”韩俭康说。
如今,周庄又开始悄悄改变自己的格局,推出了《周庄古镇保护实施细则》,投资2000多万元将电线、光缆和电话线下埋,统一古镇房屋的外观风格,兴建反映古镇传统的文化街。
“我们在富安桥上开了个咖啡厅,如果开饭店那是最好的位置,一年收50万元肯定有人租。但我们开了个咖啡厅,虽然没有饭店红火,但这样的改变是值得的。”
在韩俭康的设想中,周庄还会有更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