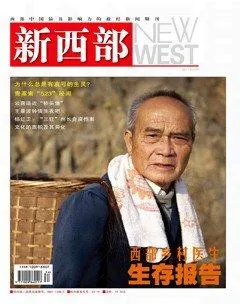青蒿素“523”秘闻
青蒿素不仅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而且至今还是全球最佳抗疟药物。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获美国拉斯克奖而名扬天下,但在屠呦呦背后,却是中国几代科研人员为青蒿素研究而付出的艰苦劳动,其中云南、四川等西部地区的科学家更是为此做出突破性的贡献。有研究者说,“青蒿素是一个奇迹,一个波谲云诡的传奇,它只会在中国发生……”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发明在诞生近40年后,终于赢得世界的承认和赞誉。
2011年8月,屠呦呦获美国拉斯克奖之前,美国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那一行到中国了解青蒿素的发明史。他问曾经担任云南“523”项目办公室主任的傅良书:“‘文化大革命’那么乱,你斗我、我斗你,为什么你们这个工作不能停?”80岁的傅良书答:“因为‘523’是一个紧急战备任务,是毛主席亲自批的。”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中国只有两项科研工作没停,一个是“两弹一星”,另一个就是“523”。
青蒿素的发明,正是源自“文革”期间这一代号“523”的军事秘密科研项目。毛主席亲自下达的任务
傅良书是“523”会议的亲历者。
1967年,是“文革”中连开会都找不到一个安静地方的时期。当年5月23日,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饭店联合召开会议,会上布置了一项秘密的科研攻关任务。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传统治疗药物氯喹等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在越南战场上交战的美越双方,都深受抗药性恶性疟疾之苦。寻找对付恶性疟疾的办法,成为决定越战胜负的关键因素。越南迫切希望中国伸出援手。
于是,中国领导人决定兴举国之力,研制抗疟新药,支援越南。这项战备援外的紧急军工任务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保密代号,称为“523”项目。
云南当时去了3个人。除了傅良书,还有昆明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和科研所副所长。两位领导因为回去还要受批判,所以他们在会上就对傅良书说:“这个事情回去只有你去张罗了,我们都无能为力了。”
按照军科院制订的规划,“523”项目分为几个研究组,包括临床研究协作组、中医药协作组、化学合成药协作组以及媒介、免疫、药械等研究组。听到这个庞大的规划,傅良书心想:“到处斗得一塌糊涂,回去怎么搞啊?”
“但接受了任务就得搞啊!”回到云南,傅良书先去找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对他说:“我们厅长都被抓起来了,说是什么叛徒啦,我还准备着挨斗呢,你们去找各单位的造反派吧。”
傅良书就去各单位找造反派头头。造反派一听,“毛主席批示的我们咋能不参加?”于是,各个被选中的单位迅速成立“523”课题小组,由昆明军区“523”项目办公室统一布置任务。
据傅良书回忆,云南省前后组织了30多个科研机构、320多名科研人员“参战”。那时候科研单位的老专家大多“靠边站”了,“参战”的大多是中青年研究人员。“云南的组织工作就这样慢慢落实下来。所以‘文化大革命’我一天也没参加造反派的活动,就忙这事了。”傅良书说。
云南属于恶性疟疾高发区,与越南毗邻,因此一开始就成为“523”项目最重要的验证现场之一。“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全国各地的科研小分队都跑到云南,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护卫下,深入疟区现场验证,就地开展试验。鼎盛之时,云南全省16个地州的30多个县的1400多个生产队都涉及该项目,“523”工程的盛况可窥一斑。
据“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助理员施凛荣回忆:这场轰轰烈烈的举全国之力的科研大协作项目,聚集了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就有五、六百人,加上中途轮换的,参与者总计有两、三千人之多。
但是,自1967年5月至1972年底,5年多时间过去了,国内虽然也发现了鹰爪、仙鹤草、陵水暗罗等10余种重点抗疟中草药,云南药物研究所也找出了对疟原虫有明显抑制作用的马兜科植物金不换、管兰香等草药,但遗憾的是,这些草药又都具有无法克服的毒性。草药筛选工作迟迟没有突破。
1972年3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523”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屠呦呦作为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中药所)的代表,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报告了该所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引起“523”项目办公室的重视。
项目办公室立即安排对这一提取物进行临床试验。北京和海南的试验结果显示,提取物对恶性疟疾的治愈率达到90%以上。消息传来,大家深受鼓舞。
根据项目办公室的要求,北京中药所开始进行青蒿有效抗疟成分的分离,1972年底分得了三个单体成分,其中1个命名为“青蒿素Ⅱ”。但恰恰就在这一步,问题出现了。动物实验发现,青蒿素Ⅱ对实验动物的心脏有明显的毒性。尽管有疑虑,青蒿素Ⅱ的人体临床试验,仍然很快在海南岛展开。
遗憾的是,带去可治疗14个病例的药物,只试用了8例便终止了临床观察。结果显示,青蒿素Ⅱ对恶性疟疾疗效不佳,并出现明显的心脏毒副作用。
“523”项目办公室不得不面临一个抉择:是否就此否定青蒿素?
云南药物研究所的偶然发现
就在青蒿素Ⅱ研究面临困境之时,“523”项目组研究单位遍布全国的大协作方式发挥了作用。
1972年年底,傅良书到北京参加全国“523”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傅良书记得,在这次会议上,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一直在批评北京中药所:“底下各个地区都在积极地做,你们为什么做着做着就不做了?”
从北京回来,傅良书向科研人员传达时提到,北京中药所发现青蒿的粗提取物有抗疟作用,但该所已停止研究。他命令云南药物研究所(简称云药所)集中精力开展对本地蒿属植物的研究。“我们云南是植物王国,中草药很多,我们为什么不搞呢?”
“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若干年后,原云药所“523”课题组成员罗泽渊回首往事,仍止不住心潮澎湃。“文革”期间这一秘密战备任务,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相当于一次救赎,对罗泽渊更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她说,“当时我们觉得参加这个工作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罗泽渊一开始并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有6年时间,她没有工作,饱受歧视。1972年,她加入“523”课题组时,这个项目已经有点不景气了。很多年没搞出成果,大家的心理压力都很大。一些研究人员纷纷离开,搞别的项目去了。
当傅良书把筛选蒿类植物作为硬性任务布置下来时,云药所并没人愿意搞。罗泽渊正好没什么工作,课题组就让她来做。
罗泽渊立即开始在研究所附近采集植物,制备样品,以鼠疟为模型进行筛选。她把昆明附近、单位附近凡是蒿属植物都一一找来做实验。
1973年春节,罗泽渊去云南大学探访朋友,在校园内发现了一种一尺多高、气味很浓的蒿属植物,当下采了许多,带回所里晒干后进行提取。她不认得是哪个品种,研究植物的刘远芳告诉她这是苦蒿,在四川农村很多,夏天用来薰蚊子。
当时云药所对过筛样品有一套成功的制备模式,每一植物共筛5个样品,以避免遗漏。经过对苦蒿5个提取物进行鼠疟过筛,奇迹出现了:满天星似的原虫感染血片中,疟原虫竟荡然无存!
罗泽渊用柱层析法从活性粗提物中分到了大约五、六种单体,逐一进行鼠疟过筛,随后确定了能使鼠疟100%转阴的有效成分——“苦蒿结晶Ⅲ”。
黄衡是罗泽渊的爱人,多年从事抗疟药筛选工作。当他看到“苦蒿结晶Ⅲ”的过筛结果时也非常惊讶,“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他惊喜之余,又冷静地提醒自己。但多次试验结果重现后,他激动了,“这不是偶然,我们真的找到有效的抗疟成分了。”
依照国际天然化合物命名原则,云药所将“苦蒿结晶Ⅲ”命名为黄蒿素。
云药所的研究成果引起全国“523”项目办公室的高度重视。为了对黄蒿素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523”项目办公室要求云药所采集大量药材,制备更多的黄蒿素单体。当时已是1974年6月初,昆明的大头黄花蒿大多已花谢叶枯。正当大家为药源发愁时,研究人员戚育芳告诉大家,四川用的青蒿也是黄花蒿,花期比云南晚,说不定到四川还能采到。
戚育芳和课题组成员詹尔益马上赶赴重庆。当他们得知重庆市药材公司有一批当年采收的因有叶无花而“不合格”的青蒿正待处理时,真是大喜过望,一口气买下500公斤运回所里。经鉴定,这批青蒿学名为黄花蒿,产自四川酉阳,分析结果证明,其黄蒿素含量比大头黄花蒿高出10倍以上。
优质药源的发现,大大地支持了云药所黄蒿素的研究,也加快了全国青蒿素研究的进程。数十年过去,当年的一个意外发现,使酉阳这个川东最贫困的地区,成为远近闻名的“青蒿之乡”。
“青蒿素的故事里面的确有很多巧合。”回首青蒿素研究往事,罗泽渊至今激动不已。
耿马成功与全国大会战
1973年秋,全国“523”项目办公室主任周克鼎到云药所检查工作,对云药所取得的成果既吃惊又欣喜。
罗泽渊当时正怀有身孕,周克鼎一次次地嘱咐她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了。罗泽渊听惯了工宣队粗鲁的呵责,当她听到这位儒雅的领导给她说出温暖人心的话语时,不由得眼睛湿润了。
临走前,同来的北京中药所张衍箴说他们正在分离有效成分,向云药所索取黄蒿素对照品。罗泽渊有点儿不大情愿,受到工宣队队长的批评:“白求恩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支援革命,你这一点点算什么?”罗泽渊只好拿样品瓶装了100毫克分给了北京中药所。
1974年9月,云药所将分离到的数百克黄蒿素制成片剂,交由黄衡和陆伟东携带奔赴脑型疟高发区进行临床试验。从思茅到西双版纳,从云县到耿马,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恶性疟、脑型疟的高发区。
由于云药所临床验证人员的力量跟不上,“523”项目组再次发挥大协作优势,由当时正在耿马开展凶险型疟疾救治的广州中医药大学“523”临床试验小组的李国桥医生协助云药所进行临床试验。
“数不清的人得疟疾,地里金黄金黄的稻子成片成片倒下,烂了都没人去收,到处都是哭声,绝户的情况屡见不鲜。”回想起当时耿马爆发疟疾的悲惨场景,黄衡记忆犹新。
1974年1 2月,经过18例恶性疟临床观察,李国桥认定,从黄花蒿中提取的结晶对治疗恶性疟疾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试验表明,仅仅0.2克结晶,就能像炸弹一样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其安全、低毒以及杀灭恶性疟原虫的速度,都是氯喹等传统药物望尘莫及的。
成功的消息传来,云药所整个课题组沸腾了,一群30多岁的年轻人,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又哭又笑。
云药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一扫北京中药所青蒿素Ⅱ失败的阴霾,引起了全国参与研究的同行的关注。北京中药所刘静明主任带着助手来了,山东中医药研究院的魏振兴也来了……
青蒿素的后期研究工作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75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全国“523”会议作出了“集中全国抗疟药研究的力量,攻下青蒿素,向毛主席汇报”的决定。一个更大规模的协作开始了,更多省、市,军区和科研单位加入了青蒿素大攻关的行列。
四川省中药所的万尧德就是当年加入大攻关行列的科研人员之一。
万尧德告诉记者,当时四川动员了40多个单位参加了“523”项目。从1975年至1978年短短3年,全国“523”项目组临床验证了6550多例病例,其中四川省占了5300多例。在这5300多例中,万尧德一个人就完成了650多例。
“我们是地方所,分配的任务我们就拼命去做,全力以赴地做。”万尧德说,唐山大地震那天,半夜3点多,他还在宜宾南部高场给病人看血片,灯泡甩来甩去,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第二天听广播才知道是唐山大地震。
1978年11月,全国召开青蒿素成果鉴定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青蒿素鉴定书》的送审稿,当时有100多位专家签了字。
万尧德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青蒿素鉴定书》。出现在鉴定书上的6家主研单位中,四川省中药所排名第五。但让万尧德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后,他们命运逆转。
1979年9月,国家科委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广州中医学院6个单位颁发了“抗疟新药——青蒿素”《发明证书》。四川中药所从6家主研单位中被“勾掉”,取而代之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一种药物的成功在于药理、药化和临床,三者缺一不可。青蒿素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它能够对疟疾有效,这才是最关键的。可是当时的专家说临床那些都不重要,把我们一笔勾销了。”万尧德对此耿耿于怀:“当时都不讲名利,也不准哪个去争名利。可正是因为我们没争,后来所有的‘523’会议都不来找我们了。”
其实,在青蒿素鉴定会上,与四川省中药所一样命运陡转的还有云药所。
当时,北京、云南、山东三家研究单位都提取出了青蒿素单体,虽然有人对这些单体是否为同一种物质提出过质疑,但并未得到当时管理者的重视。研究者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实验记录,显示当时三家提取的晶体为同一物质。
而且,当大多数科研人员一致认为叫黄蒿素更名副其实时,作为中央部属单位的北京中药所的意志最终发挥了作用。青蒿素的成果鉴定会上,北京中药所提出“按中药用药习惯”,“将中药青蒿原植物只保留黄花蒿一种,而其抗疟成分随传统中药定名为青蒿素”。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向世界证明祖国医药的伟大,课题组成员怀着难以割舍之情服从决定,将黄蒿素统一命名为青蒿素。”罗泽渊不无遗憾地说。
持续数年的发明权之争
与中国青蒿素诞生大致同时,美国投入数亿美元筛选了几十万种化合物,也研制出抗疟新药甲氟喹。但这个千挑万选的甲氟喹依然与以往的抗疟药类似,疟原虫很快就适应了它,上市不久就出现了耐药性。
此后近30年,虽然有关的国家政府、基金会和其他组织投入数十亿美金,却仍然在重复着过去实施的老办法,全球遏制疟疾的效果仍不显著。世界医药史上于是长久地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是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口死于疟疾:另一方面却把中国的抗疟神药青蒿素束之高阁!
直到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开始将源于中国“523”项目的复方蒿甲醚等青蒿素类复方药物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据当时统计:全球感染疟疾者多达3到5亿人,每年有将近100万人因感染疟原虫而死亡。历经多年的调查和实践后,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尽管西药的科研力量十分雄厚,但治疗疟疾的最大希望来自中国的青蒿素。青蒿素类复方药物在大规模的使用后依然维持的高治愈率令世界惊奇!
美国《远东经济评论》称:“中国的青蒿素研制者们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这项科研成果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
2011年9月,81岁的屠呦呦获得美国拉斯克奖,这是中国发明青蒿素30多年后获得的国际承认的最高奖项。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时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
但是,美国拉斯克奖为中国青蒿素赢得了国际声誉的同时,也重新在国内点燃了青蒿素的发明权之争。
1981年,大协作的抗疟新药研发计划按照预定的轨道胜利谢幕,但一切并不像最后那份文件所希望的“排名争议达成一致”。当年很多“523”研究小组的专家作出的牺牲和让步,让这段历史在此后几十年依然扑朔迷离。
1986年,屠呦呦和北京中药所用所有发明单位共有的研究资料单独向国家卫生部申请了新药证书。此事立即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另外几家发明单位向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写报告抗议,后来还打了官司,但最终不了了之。
这场官司被认为是青蒿素历史中“一个极不和谐的杂音”,对国内艰难起步的青蒿素产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原来大协作群体内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上世纪80年代,周克鼎到重庆出差,专程去看望罗泽渊夫妇。他对他们说:“‘523’不会忘记你们对青蒿素的贡献。”但罗泽渊没有想到,当年“523”项目的老领导、老同志为澄清这段历史真相,会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2005年,万尧德给科技部写了一封信《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据他回忆:1975年大会战的关键时期,屠呦呦曾通过“523”办公室派了两个同志到四川中药所来学习。短短21天,化学室的刘鸿鸣协助北京中药所提取了800克的纯青蒿素。紧接着,他们又花一万块钱到四川中药所买了一公斤青蒿素。此后仍三番五次通过“523”办公室向四川所索要青蒿素。“四川‘523’办公室的领导都是老革命,教我们不能有自私之心,人家要我们就给人家。说老实话,知识分子都是有所顾忌的。”
回首往事,万尧德有些愤愤不平地说,“既然屠呦呦早就提取出来青蒿素,为啥要派人来学,又求爷爷告奶奶地买?这不是开玩笑吗?”
2006年,张剑方、周克鼎、傅良书等老一辈“523”战士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一书问世。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讲述了青蒿素的发现及研究过程,讴歌了数以千计在“文化大革命”中无私奉献的知识分子,告诉人们如今享誉世界的青蒿素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军队和参加此项研究的“523”战士。“我们是组织者,也是实际参加者,如果我们不编这个书,对不起整个参加‘523’的同志。”傅良书说。
其实,屠呦呦获奖前,美国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那在公开场合说: “青蒿素的发明是一个接力棒式的过程:屠呦呦第一个发现了青蒿提取物有效:罗泽渊第一个从菊科的黄花蒿里头拿到了抗疟单体青蒿素;李国桥第一个临床验证青蒿素疗效。”这一说法得到在场大多数“523”老科学家的认可。
而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推荐拉斯克奖的提名人时,李国桥推荐的是罗泽渊。李国桥认为:“青蒿里面有7种结晶,只有一种结晶是青蒿素。”他多次表明,“我是用云药所的黄蒿素完成了首次临床验证工作的。”
没想到几天后,拉斯科大奖的结果公布于世,这三个相互传承的“第一”全部归功于屠呦呦一人。
对于屠呦呦获奖,当年亲历者大多心情复杂。“你问我到底感受怎么样?我说一点不难受是很虚伪的。我难受的不是我没有得,我是觉得奖一个人太不合理了。”罗泽渊说,“如果这个奖给我,我也承受不了,它的确是一个集体的创造。”
对于自己在青春年代能与青蒿素的发明结下渊源,罗泽渊始终感到自豪。1979年,云药所完成承担的青蒿素任务后,“523”课题组基本解体,组员纷纷调离,罗泽渊夫妇也调到位于重庆的四川省中药所工作。
云药所成立50周年时,罗泽渊应邀做了一个关于青蒿素的专题报告。“在场很多‘523’课题组老同志都流泪了,因为那是大家亲历过的往事。”罗泽渊说。
屠呦呦获奖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说:“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宿,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
有研究者说,“青蒿素是一个奇迹,一个波谲云诡的传奇,它只会在中国发生……”
而在傅良书看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国家没有正确对待,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这个事情”。
“现在都扯不清了!”老人的一声叹息,充满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