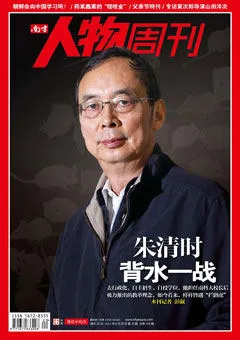“你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地图”
2011-12-29 00:00:00羽戈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20期

父亲老了。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似乎从未年轻过。
他大半辈子,只为扮演两个角色,在奶奶面前是儿子,
在我们兄妹三人面前是父亲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白居易
父亲诞于农历二月初二,故乡流传俗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故父亲的名讳有一个“龙”字。今年此日,恰是父亲60岁寿辰。他早早就说,你们兄妹日子过得都不易,不要庆寿了。家里大小事宜,多由母亲发号施令,他极少主动要求什么,既如此说了,我们则不便违拗。
记得那日是周末,我为时事所羁绊,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直至夜深才忆起父亲的生日,打电话都迟了,一时无语凝噎。青灯如豆,打开电脑,想为父亲写一点留念的文字,凝思半晌,却始终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此前,我写过一次父亲,不足五百字,短促如这个时代的噩梦。那是我的第三本书《百年孤影》的志谢,前二书充满了种种缺憾,我不敢拿来敬献给我的父母,惟恐玷污了他们的声名,他们平凡至极,但他们之于我的生命却是伟大至极。写《百年孤影》的时候,埋首迷雾氤氲的史料丛中,我常常神思恍惚,眼前飘出父亲消瘦的身影;修订此书最后一稿的时候,父亲与我的距离仅三五米之遥:
“……2010年春节,近六十岁的父亲不远千里从皖北来到浙东。每日上午,我陪他出门逛公园和广场;下午与晚上,我闭门修订书稿,他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卤菜的香气弥 散于日益陌生的乡音,空气渐渐潮湿,窗外雨雪纷飞,烟花漫天,令我恍惚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眼前的父亲背越来越驼,白发越来越多,眼神越来越每况愈下。我写的前两本书,他都未能读完,有些地方,更是似懂非懂。但在我心底,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为他所代表的那一种力量与情感而写。哪怕他的眼神再不济,仅仅能看清书名。只要他在看,我就感觉充实,就有勇气继续提笔,讲述百年中国的白云苍狗,风雨激变,谎言对真相的压迫,正义像故园老屋后的那一条河流,越来越脏,越来越瘦,最后枯涸为一滴孤独的眼泪。然而,我们终将走出困境,走出黑暗,如同很多年前,父亲怀揣借来的几十块钱,拉上一家五口,离开了那个贫瘠的乡村,我的出生地,从未回头。
没有什么礼物,比这本以历史为主题的书,更适合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他流逝的峥嵘岁月。”
写完这些文字,不知费了我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是那么善于制造文字垃圾,轮到书写生命深处的爱恨却往往无力举笔。一字千钧,然而我不时陷入如潮涌至的疑虑,我们的书写对于所书写的对象到底有多重呢,正如对于书写者自身到底有多重?
我从未以此问题叩问沉默惯了的父亲,并非不愿,而是不敢。因为父亲轻轻一个答案,就可能摧毁我书写的全部欲望。同样,父亲从不主动和我谈论我的书,尽管他一直在读。他只是缓声说:你写这么多,不要累倒了。
假如我不写他,父亲一生,注定与文字无缘。
他幼年失怙。7岁那年,我的地主爷爷病死在江苏某农场,尸骨无存,至今不知魂归何处,那个浪荡子,也许鬼魂都如飘萍。可怜奶奶含辛茹苦,要以一己之力,拉扯三女一子。我最小的姑姑,曾因家里养不起,被迫寄人篱下。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遭遇了家庭与时代的双重病变,在凄风苦雨之中颠沛流离,辗转求生,实无一丝欢愉可言。
他断断续续读到了五年级,到15岁那年,“文革”开场,像他这样的出身,便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罪过,于是被发配下乡,从此与学校作别。待我记事后,偶尔听他叹息:他的成绩一向极佳,若能继续读书,那该多好。只是叹息,并无怨天尤人的意思。父亲一生淡泊,对于命运的百般磨难,真正做到了顺其自然,或可说是逆来顺受。
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1985年,举家返城,身无长物,连路费都告贷于亲友。与其说还乡,不如说从一重困境逃亡到另一重困境。那年我3岁,尚不记事,后来听奶奶话旧忆苦,才知当时的窘困。一家五人——两年后添了一个妹妹——寄居于两间破败的老屋,聊避风寒。因地势低洼,外面下暴雨,屋子便要进水。家徒四壁,仓惶度日,在我读大学后才搬离。搬到新房后,父亲特意买了一幅字挂在中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他未必知晓此言出自他经常提及的诸葛亮之口。
此后二十余年,他们干过各种苦力,做过各种生意,目的只有一个,供我们读书。我以县文科榜眼的成绩考上大学,父母欣喜若狂,因他们对我的期望,能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便足矣,不想我却能考中县人梦寐以求的西南政法大学——那时西政的招牌,还不像今日之臭名远扬。只是父亲对我学法律专业,颇有些耿耿,却说不上所以然。我后来推想,大约在父亲看来,以我的头脑之笨拙、性情之耿介,进不能匡扶正义,退不能混迹官场,学法4年,最怕一无所成,连吃饭的破碗都保不住。大学毕业,我弃法律而从新闻,家人颇多怨言,惟父亲的姿态无可无不可。这或不是先见之明,知子莫若父,父亲朴素的希望是,我未来的路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尽量少一些颠簸。用他所喜欢的诸葛亮的话讲,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曾拿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给父亲阅读,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干律师。父亲读后感慨,他未曾如小说作者的父亲那样悲剧,为筹学费而卖鸡和蛋,被公安局冤枉抓了,以至误了儿子的一生。我每念及此节,都忍不住大恸:
“……198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
“做个好人”,永远是我今生的标杆。然而我终无法与法律彻底绝缘,就像我无法避而不闻这个世界此起彼伏的罪孽与邪恶。某一天我提起笔,冲决文学与哲学的罗网,参与公共事务,写关乎政法的时论——这大抵是一个犬儒的法律人曲线救国之路径——我对父亲解释,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父亲沉默了半晌,便也释然。
父亲老了。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似乎从未年轻过。他大半辈子,只为扮演两个角色,在奶奶面前是儿子,在我们兄妹三人面前是父亲。2008年秋天,奶奶去世,送葬那夜,寒雨纷飞,我背他下车,第一次感觉他的身体如此之轻,只有一把被榨干了精髓的硬骨头。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心里的负担如此之重;第一次领悟了那句刻在心底的箴言:父辈的苦难就是我们的原罪。
到宁波工作后,我并不经常回家,而是希望父母多来玩。他们的劳碌岁月,没见过什么繁华世面,连像样的馆子都未下过。可是他们每次来,都急匆匆要赶回去;每次外面吃饭,都怨声载道于菜价的昂贵。我给父亲打开珍藏多年的泸州老窖,他却托辞牙疼,更喜欢喝三块钱一斤的糯米酒;我问他什么菜最好吃,他说是沸腾鱼——那家使用地沟油的小小的川菜店早就关闭了,如今改作棋牌室。父亲,我们何时能再吃一次?
我的好友,诗人宋尾,写过一首《给父亲的信》。其中两节,我一览成诵:
你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地图。
我们每天都从那里经过
几十年,从没去勘探。
你把几十年的狂暴
都埋在了那里
安静得像我的孩子
我却如父亲那样的悲恸。
我依然记得我的悲恸。2010年清明前夕,我回家乡给奶奶扫墓。临别前一晚,与3位表哥喝酒,喝到一半,担心我喝醉的父母来了。父亲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语不发。我不敢看他瘦骨嶙峋的脸,只顾埋头喝酒。那晚我自觉并未喝多,却不知为何,语音哽咽,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