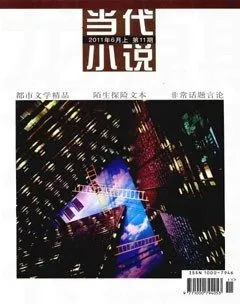大河汤汤
我从车上下来还没站稳,公交车就一溜烟远去了。我怔怔地站在路边,觉得还有许多未尽的心事丢在了车上。这是王家岭小站,设在后山脚下。娘曾多次找人转折捎信给我说,香香啊,村里通公路了,回来吧。刚出去那两年,每次听到这话,心里就被咯噔撞一下。撞着撞着,我就觉得心鲜血淋淋了。我经常坐在那些肥壮的或瘦弱的男人的腿上,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娇媚地说,赶明儿送我回家吧?每次都是满桌子的响应,行行行,说说家是哪里,哥哥们一定包接包送。在一片哄笑中,我努力地想自己的家在哪里,可是脑子里一片混沌,一会儿是酒吧里的莺歌燕舞,一会儿是茶园里的翠绿阑珊,一会儿是娘和弟坐在炕头上开怀大笑,一会儿是我和蚂蚁站在村前坝上打闹嬉戏……有次想着想着,我呜呜地哭起来,我实在想不准确哪里是自己的家了。我的哭泣令客人恼怒而去,我当月的收入也成了零。从此,我鲜血淋淋的心收了起来,结成了硬生生的疤。
今天是我进城六年来第一次回家。我发现,不只路边的花草树木垂头丧气,茶园里的茶树也居然是一片褐色。我惊诧不已,正是采春茶的季节,茶树怎么成了冬天的颜色?我不顾一切地奔进茶树丛,受伤的残脚一阵钻心的痛。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蹲下用手抚摸茶树,这棵,那棵,抚摸得心里惶惶的。我四处张望,见不远处有个四五岁的男孩,背着一个打药的喷雾器,正好奇地盯着我,细长的眼睛里冒出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警惕,他胡乱指了指远处说,你敢!我奶奶在那儿,我奶奶在那儿。说着说着,转身跑了。喷雾器如一座小山背负在他身上,压得他跑起来摇摇晃晃。男孩细长的眼睛让我心里一紧,我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很久很久。
采新茶时,茶园里除了村里的姑娘,不允许其他人进。天刚微明,我们就洗手净面,背起背篓进到茶园。那时茶园里露珠悠悠,翠绿浓浓,弥漫着无边无际的清香。我们叽叽喳喳如小麻雀般在园子里散开,手里采着茶,嘴里还要不停歇地逗笑唱歌。每次唱歌都是我开头,因为我知道蚂蚁这天也来山上干活了,就在不远的沟谷里。听到我们的歌声,鸟雀儿扑棱棱飞起,落下,落下,飞起。就这样,唱着笑着,就该吃午饭了,唱着笑着,太阳就落山了。这时候,蚂蚁就会在村前大河的坝上等我。看到我们从远处叽叽喳喳地走来,他红涨着脸,局促地东望望西瞅瞅。伙伴们就把我往他身上推搡。蚂蚁憨憨地摘下我背上的茶篓,跟我一前一后往村里走。空气清凉洁净,飘荡着大河清冽幽然的气味,让人心醉神迷。我故意站住不走,看着旁边的大河。蚂蚁也跟着停住了,香香,快走哇,天要黑下来了。蚂蚁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让我心里暗暗生怨。黄昏笼罩四野,把大河染成了金黄,我和蚂蚁身上也染得金灿灿。突然,蚂蚁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里溢满了汗水,热得我的心像撒欢的小鹿咚咚直跳……那是我最幸福的日子。而今,我看着这片死去的茶园,褐色的忧伤席卷而来,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滚落。
熟透的太阳,把天边烧起一片橙红。我坐在路旁,卷曲的头发被风吹得零零碎碎,腿上的短裙张张扬扬。风中飘来稻草灰的香气。我不知道该怎么见娘,见弟,见村里人。我的手在坤包里摸来摸去,摸出一个化妆镜和一袋湿巾。我对着镜子认真仔细地擦着脸上的浓妆和泪水,镜中便露出了我的真面目:蜡黄的脸色,青黑的眼圈,曾经水一般的眼睛变得黯淡无神。这是我吗?我把镜子远远地扔了出去,又从包里掏出丝袜香烟打火机,一样一样狠狠地往远处扔。我一阵嚎啕大哭。
天黑透了,王家岭沉浸在绵软温润的暗色里,偶尔的几声狗吠鹅鸣让我心惊肉跳。我贼一样,跛着脚,尽量快速地穿过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当推开我家斑驳的大门时,堂屋里溢出的橘黄色的光晕,让我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娘站到了我跟前。香香,是香香回来了么?娘的声音发颤,手在我的头上摩挲。我紧紧抱住娘的腿使劲点头。娘一个趔趄,轻飘得如一片老茶叶子,差点歪倒。娘,娘!我搂紧了娘。娘扶我起来,手紧紧握住我的胳膊。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娘的头发花白稀疏,面孔苍老憔悴,身子仿佛低矮了许多。娘抹去我脸上的泪水,说,你弟考到镇上去了,我们这个家还有指望,你回来就别再走了。我不走了,娘,我就是为了不走才回来的。娘长长叹了一口气,就是茶园里的茶都冻死了。眼泪从娘的眼角慢慢渗出。那片褐色的忧伤又漂浮过来。团团包围了我,让我心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酸疼。
我没有出门,我不想见任何人。可是到我家来的人却特别多,借这借那的,问长问短的,跟娘经常来往的,从不跟娘来往的,都跑来了。他们的目光涌现出的不屑,让我感到局促不安:他们话语夹杂着的嘲弄,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他们鄙夷的笑容,又让我怒火中烧。这样地一天,两天,我终于不能再忍受。我决计撕破罩在心头的耻辱,不再像老鼠那样地躲躲闪闪。在娘古老的梳妆镜前,我手不颤心不慌地描眉画唇,搽粉施黛。然后高昂着头,站在了王家岭明晃晃的日头底下。
我第一个碰到的是村主任,他铮亮的秃顶被我晃出了一片惊慌失措。他嘴上语无伦次,目光不知道停哪儿好,最终在我绵软的笑颜里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大街上一片空寂,有几扇门打开又瞬间关上。我好像看到了门后那些或白或黑的眼球,心里涌出了无限的悲哀和仇恨,我不由想到了他,混帐蚂蚁!
我来到茶园的时候,天已近中午。细眼睛男孩也在这里,他依旧背着喷雾器,在一埂一埂的茶间穿梭奔跑,样子乐不可支。那个孩子如果不打掉,现在也该在这里奔跑了。见到这个细眼睛的男孩,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古怪的念头。看见我,男孩停止了奔跑,把喷雾器往上托了托,龇牙笑了。于是,眼睛也就更加细长。你叫什么名字?我审视着他问。他一梗脖子,我不认识你!话未完又跳跃进茶埂间去了。
男孩似乎很快乐,喷雾器随着他的奔跑跳跃有节奏地捶打着他的脊梁。太阳越发炙热起来,我感到头晕目眩,便慢慢躺倒在了茶埂间的阴凉里。眼前无数的金星闪烁,男孩似乎变成了蚂蚁,迈着长步,在我跟前晃来晃去。六年前的那个春天,蚂蚁就是这样地迈着长步,领我进城的。我怯怯地跟在他身后,蚂蚁边往火车上拽我边说,我们要到城里去挣钱,买房子,过上城里人那样的好日子!我只顾笑,鼓胀起来的心航行在蚂蚁营造的美好的海洋上,欢快甜蜜。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进城没到一年,蚂蚁不但爬出了我的视线,而且越爬越远,爬进了那个城里女人的怀抱,凿洞筑窝,当上了城里蚂蚁。
我永远忘不了蚂蚁跟我说分手时的样子。那日在工地的伙房里,刚呕吐完的我无力地坐在凳子上,心里忧喜交加。怎么就怀上了呢?蚂蚁这个坏东西!穿着保安服的蚂蚁就是这时急急地窜进来的,他的脸窜成了紫茄子。我惊喜地迎上去,蚂蚁,是你来了?蚂蚁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制鞋厂干保安,那身保安服衬托得他精干俊秀,看得我心里美滋滋的。蚂蚁的嘴唇发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傻人,你不用来,我今晚就去你那儿;不不不,你应该来,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端来水让他喝。他摇摇头推开了碗。那是饿了?我忙从笼屉里拿出两个鸡蛋往他手里塞,蚂蚁仿佛被烫着一般,跳到了一边。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蚂蚁的眼睛盯着胸前的扣子,始终没有看我一眼。看着蚂蚁傻乎乎的样子,我心里有些好笑。真是个呆鸟!我把他拽到一把吱呀作响的破椅子上,那就坐下,看我干活。说这话时,蜜水从我脸到全身细细地回绕流淌。蚂蚁慌忙拉住我的手,香香,等等,先别急,我有话说。我抬头看了看外面,太阳把亮光撒播得到处都是。我低头笑起来。蚂蚁的手变得修长白皙,比我整天泡在汤汤水水中的手喜人多了。仿佛被我的目光灼伤了一样,蚂蚁把手缩了回去。我找个矮凳坐在蚂蚁身边,用手抚着肚子,我在等他说完,好告诉他肚子里的秘密。我眼角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
蚂蚁嘴里绕来绕去说个不停。我盯着蚂蚁,心里有些纳闷,蚂蚁本来是不善说话的,他这是……蚂蚁却竟说出了出乎我意料的话:难得能在城里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她说她家里什么也不缺,就是缺干活的,只要入赘到她家,给她父母养老送终……我没听懂,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蚂蚁忽然哭起来,眼泪鼻涕一齐奔流,我,我也不想那样啊,可是,我实在累了呀香香,凭我们这样干,这辈子也攒不够买房的钱……蚂蚁的哭声越来越大,就跟那晚他从我身上下来时哭得一模一样。那晚,他哭得一塌糊涂,香香啊,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听着那些声泪俱下的誓言,我仿佛看到幸福正扇动着翅膀朝我飞来。可今天,在炽白如炬的阳光下,那双翅膀硬生生地折断了。我的手从肚子上垂下来,穷尽全身力量朝他甩了一记耳光。蚂蚁松着肩,垂着头,一动没动。香香,你打吧,只要你解恨。我狠狠啐了他一口,转身走了。
凛冽的寒风中,我一步步丈量着这座繁华斑斓的城市。等脚底渗出了殷红的鲜血,我才明白过来,这座城市里,原来有那么多不费情感的欢颜和莺歌。我觉得心痛无比!我去医院打了胎,一头扎进了那些欢颜和莺歌的氛围里……
鼻子里钻进一股强烈的农药味。我睁开眼,看到男孩正用喷雾器替我遮挡太阳。我挣扎着坐起来,头痛欲裂。男孩见我坐起,就把喷雾器又背到了肩上。为什么要背喷雾器?重重的!我看着眼前这个细眼睛男孩问。男孩一凛,他瞅了我几眼才说,这是蚂蚁买的!我的脑袋轰的一声,无数的碎片崩裂出来,片片让我疼痛欲绝。是的,孩子的细长眼睛跟蚂蚁的眼睛如出一辙!蚂蚁是……你爸?男孩点了点头,嘴撇了撇,我们全家都叫他蚂蚁。我笑了,我一下喜欢上了这个男孩,蚂蚁还爱哭吗?我这话让男孩变得兴奋无比,你怎么知道蚂蚁爱哭?他经常被我妈训得哭。我觉得心一下轻快得飞上了蓝天:又忽地直直坠到了谷底,他训你妈吗?他训你吗?男孩摇了摇头,蚂蚁从不训人,蚂蚁只会干活。男孩的脸上显出了与年龄不符的忧伤。我得回家了,奶奶该找我吃饭了。男孩站起来,朝坡下走去。你下午还来吗?我站起来追问。男孩回过头来上下打量着我,蚂蚁说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我跛着脚急忙跟上去,我不是陌生人,我是你姑姑。我甚至讨好地说,我下午买棒棒糖你吃!男孩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回家这段路我走得断断续续,残脚的胀痛让我不得不时时停下。远远地,娘挎着挖草药的篮子疾奔而来。娘的头发被汗水粘在脸上,胳膊上被树枝划出的细纹隐隐渗着血珠。我决定和娘说实话,我的脚趾彻底废了,什么药也治不好了。我告诉了娘,那个金光四溢的黄昏,在城里的大街上,那条最繁华最热闹的大街上,我是怎样犯傻,跟着一个酷似蚂蚁的背影,两眼空洞地一个劲地跟着他。那是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酷似如此熟识的背影。我跟定他,走啊走啊,我的一只脚不知怎么就走进了车轮底下。我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娘,娘泪流满面。娘不相信地攥着我的腿,指甲陷进了肉里。我却微微笑了。其实,我没有全部告诉娘,当我的脚被碾在车轮下时,我居然没有感觉到一丝疼痛。我还是执拗地寻找那个背影,在一片混乱中,那个背影从人群外挤了进来。是蚂蚁!真的是蚂蚁!蚂蚁老了,蚂蚁的脸上不再精干俊秀,蚂蚁的头发不再乌黑发亮,眼睛也浑浊不堪了。可他是蚂蚁!如同在沙漠里遇到绿洲,我眼睛贪婪地盯住他,我甚至扬起手朝他挥了挥。可是他盯着我车轮边上雪白的大腿,受惊般跳到了一边,那双细长的眼睛游弋不定,眼神空洞陌生,里面甚至带有一些局外人的兴奋。是个鸡!我听到他小声对旁边的人说。霎时,我听到了脚趾骨咯吱咯吱的断裂声,声音清脆尖细,直奔我内心深处,我知道了什么叫万箭穿心!我闭紧了眼睛,不再看他,灌满眼眶的泪水随之纷纷滚落。那是个混乱的黄昏。我想像得到,脸上的浓妆一定被泪水冲刷得五花八门,从此生活也被我揉搓得五花八门了。
娘挟着我回到家,径直到屋里,掀开炕脚的柜子,拿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包。塑料包四四方方,用红绒线扎着。娘解下了绒线,一层一层敞开,里面包的原来是钱,大到百元,小到一毛五毛,整整齐齐地摞了几沓。娘把钱放在炕上,这里面有你每年捎回来的,也有我在家卖茶叶的,除了给你弟交学费,还剩这些,你拿去吧。娘把钱往我跟前推了推。你爹死得早,娘知道,家里家外多亏你。这些钱你带着,不管是治脚还是嫁人,都随你。娘一天比一天老,陪不了你们几天了。一缕头发松松地垂下来,盖住了娘的脸。我没能看到娘的表情,可是娘的话语让我悲伤。那些五颜六色的钞票用嘲弄的眼光看着我,我几乎能辨认出那些都是谁给我的。我突然感到了恶心,张着嘴干呕起来,趴在炕沿上,呕得胆汁外流,呕得上气不接下气。
下午,在人们怪异的目光里,我买下了小卖店里所有的棒棒糖。我举着它们朝茶园走去,走得很急,走得很焦灼,也走得很兴高采烈。男孩早就在茶园里等我了,他不时提提背上的喷雾器,朝坡下张望。我朝他高高地挥舞着棒棒糖,来到他跟前。男孩从我手中接过棒棒糖,剥开一块,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阳光下,棒棒糖如一颗珠子,随着男孩欢欣跳跃的舌头,散发出透明纯净的光泽。这个下午香甜无比,我们一起吃了所有的棒棒糖。男孩把最后一块放进了口袋,我要留给蚂蚁吃。他说得真情实意。我不转眼珠地看着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男孩是让我牵着手回到村子的。临别时还意外地说了声“再见姑姑”。我感到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甜蜜。却不想,我刚到家坐定,大门就被推开了。蚂蚁的大姐,一个高大冷峻的女人牵着男孩的手走进来。她的眼睛环视了一下屋里,最后聚焦在我身上。我是来还钱的。女人的声音如同滚烫的白开水,灼热而寡淡。娘一愣神,拿眼看了看我。我疑惑地来到屋门口。女人盯着我,从裤兜里摸出一卷钱,这是棒棒糖的钱,我去小卖店问过了。女人把钱放在了一边的腌菜缸盖上,又推了推男孩的肩膀。男孩扭动着身子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一根棒棒糖,放在了我面前的门槛上。棒棒糖一路滚动,来到了我的脚下,男孩刚要弯腰去捡,却被女人硬硬地拉住,头也没回地走了。娘小心地随送,脚步惶惶。我扶着门框,咬着嘴唇,看着他们离去,一声没吭。
此后,我更加强烈地想念那个打掉的孩子,他的鼻子,他的眼睛,他的身子,在我的脑海里一天比一天丰满,直到举着棒棒糖立在我面前时,我才发现,他就是背喷雾器的那个男孩。
再一次见到男孩是在大河边,那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河汤汤,如同一匹巨大的绸缎,在阳光下闪耀着深邃璀璨的光芒。男孩背着喷雾器沿着河边欢快地跑来跑去,弄得满身泥水,满脸汗珠。看到我,他站住了,细长眼睛里充满了怜悯。我笑了,你怎么还背着喷雾器?他晃了晃身子,这是蚂蚁买的!你想蚂蚁吗?我问。男孩低头用脚踢着脚下的土,不大工夫,踢出了一个小坑。你要是见到蚂蚁,让蚂蚁来接我吧。男孩抬起脸说,脸上是乞求和渴望。我缓缓蹲下身子,替他把脸蛋上的泥抹掉,妈妈对你好吗?男孩看着我,咧了咧嘴,她叫我死鬼。姑姑,什么是死鬼?我一愣,脑海里出现了那片死去的茶园。那片褐色就是茶死去的鬼。我喃喃地说。男孩耸了耸背上的喷雾器,笑嘻嘻地说,我懂了!这个喷雾器就是我死去的鬼。男孩的声音尖细悠长,如同抛物线,在大河边这片柔软绵实的土地上,划出了一道美丽忧伤的弧形,稍纵即逝。我心里一沉。喷雾器在男孩背上散发着刺鼻的农药味,阴阴地看着我。我伸手就去男孩背上摘喷雾器。男孩惊异地扭动身子,不许摘,不许摘,这是蚂蚁买的!太阳火一般流淌,我跟男孩在太阳底下激烈地争夺,喷雾器贴在男孩背上躲来躲去。我被激怒了,箍住男孩的胳膊,把喷雾器一下褪了下来,颠着脚跑到大河边,扬起胳膊把它甩了出去。喷雾器呼啸一声,带着呛人的药臭,飞向了大河深处……
男孩夺命般的尖叫随之响彻河床,这,是,蚂,蚁,买,的!随着喊声,男孩如同一只觅食的水鸟,纵身一跳,追向了水中的喷雾器。水花溅起,深邃璀璨的绸缎裂开了一个沉重的漩涡,瞬间合拢如初。
我的灵魂似乎也跟随大河而去。直到喷雾器从水底浮上来,飘荡在河面上,我才醒悟过来。
我仓惶地奔向河中,惊悚地大喊:蚂蚁……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