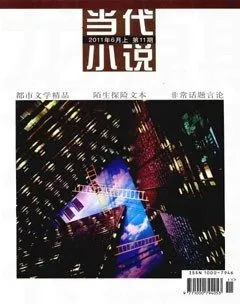一字之祸
今天与往日一样,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毋庸说,傍晚时分又将从西天徐徐落下——一天天,一月月,时光凝聚成岁月,人也就在这岁月中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老去。
任老师五十五了,满打满算,还有五年就告老还乡,和妻儿团聚。任老师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又害怕这一天真的到来。盼,是因为他厌倦了这种走钢丝般的生活;怕,是因为他喜爱孩子,留念校园,他不知他一旦离开校园,离开孩子,还能做些什么,活着是否还有意义。
在教工食堂吃过早饭,别的老师都回宿舍去,等待预备铃声响起再去上班。任老师没有回去,他穿过两排教工宿舍,直接到办公室去,他要把昨晚备好的课再温习一遍。任老师从教三十年,教的又是低年级,可以骄傲地说一句,他不用准备,闭着眼睛都能上课,而且一定上得很好。但是任老师不那样做,也不会那样做,他三十年如一日,把每一节课都当成新课,精心准备,认真备课,把他讲了无数遍的课讲得新意盎然,趣味横生。
任老师热爱他的工作,他的学生也热爱他。
任老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他供职的学校是淮县中心小学。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知道,淮县师范学校和淮县中心小学是挂钩单位,每学期都派数名学生到中心小学实习。名师出高徒。跟谁实习,首推任老师,学生也以能跟任老师学习为荣。任老师既要教学,又要带实习生,每天忙得跟陀螺似的,少有闲暇时间。而同年级或是其他年级的老师,除了上课没别的事,倒也落得清闲自在。
任老师也想过一过悠闲的日子,就像其他老师那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这个念头刚出现,就被任老师连根掐掉。
老师的职责就是授业、解惑,不该有其他杂念。
任老师今天上午有两节课,一节语文,另一节是作文。
今天的课,上的是《太阳》。听课者除了五十名学生,还有二十名实习生。实习生分坐在两边的过道里,把教室挤得满满的。今天的课气氛很活跃,因为孩子们都熟悉太阳,熟悉到像门前的枣树、院内的水缸,菜田里的南瓜……可以说已熟到熟视无睹的程度,但学了课文,特别是听了任老师的讲授,才知道太阳对地球、对人类是如此重要,重要到须臾不可分离。任老师说,没有太阳,世界将一片黑暗,永远没有光明!听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任老师还讲了风和雨形成的过程,学生们听了,一个个惊得张大嘴巴,异口同声说,太阳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啊!一节课不知不觉过去了,学生们撒着欢往外跑,实习生簇拥着任老师走出教室。
课间十分钟倏忽过去。
下一节是作文课。
作文是新课,三年级学生还是孩子,需要引导,提示,甚至还要写出范文,让他们照葫芦画瓢,他们才会挤牙膏似的写出一二百字的小文章。可别小看这些学生,更不能小看他们这一篇篇稚气得如同嫩芽似的小文章,要知道参天大树是由幼苗长成的,大作家也有童年。
上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踩着铃声往回跑,实习生也鱼贯进入教室。任老师最后一个进来,他走上讲台,扫一眼台下,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作文题:《池塘》。上一课学的是《太阳》,结合课文,任老师给孩子们一些提示,说水是生命之源——人离开水将无法生存,农作物离开水也无法生长。孩子们听了,一个个埋头写起来。
人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他就可以避开临近的灾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
世界上没有如果——其实灾祸已悄然逼近任老师,任老师还浑然不觉,他像一棵大树站在讲台前,准备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作文课能有什么问题呢?也就是文章写到某处卡住了,他给点拨一下,那个学生便茅塞顿开,拿起笔继续往下写;或者写着写着,被一个字难住了,举手问一下,说得清的字任老师就说出来,说不清的就写到黑板上。三年级的孩子,写不出的字多着呢。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一个学生举起手说:“任老师,‘哄’字我不会写。”
任老师说:“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共产党的‘共’字,合起来就是‘哄’。会写吗?”
那个问话的学生响亮地回答:“老师,我会写啦!”
也该任老师倒霉,他说这话时,恰逢县革委会主任来学校视察工作,正巧又路过任老师的班级,任老师的话一字不漏全被他听到了。主任生气道:“这还了得,我们共产党是哄人的吗!这是反革命言论啊!这样的坏人怎么教书育人,培养好革命下一代呢?你们说是不是?”
陪同视察的教育局长听完革委会主任一席话,脸都吓白了,点头如鸡啄米,诺诺连声:“是!是!”
革委会主任对教育局长下指示,说:“特事特办,你派人抓紧整理这个人的材料,明天上报革委会!”
局长一边点头,一边擦汗。
任老师仍站在讲台前,两眼看着这一群可爱的孩子,准备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对即将降临的灾祸一无所知——等待他的是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有开除公职、回家劳动改造的处理决定。
处理意见下来那天,任老师像头暴怒的雄狮,大吼一声,抬手狠狠地甩给自己两记响亮的耳光。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任老师的嘴流血了,两条红蚯蚓钻出来,在他的脖颈上一拱一拱地向下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