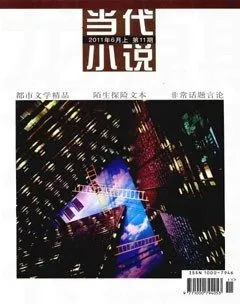从今往后
Fax最喜欢的食物,沾满芥末的生鱼片,鲜嫩多汁的厚牛排。
Fax最喜欢的服装,质料柔软垂坠度佳的黑色阔领恤衫。
Fax最喜欢的酒,Johnny Walker黑牌威士忌。
Fax最喜欢的男人,大方体面有特色,任达华曾经是不错的标准,具体人士依据时间段对爱的感受定义不同,有不同的答案。
Fax最好的朋友,我。
所以,我似乎有必要说些什么,为了Fax,也为了我自己。
以前,时间对我而言,是一段一段的存在,周一上班,周末休息,这时候时间段是五天;情人节到了,不久是我的生日,这时候时间段是一个月;报名修一门课程,时间段是四个月;新工作签约,时间段是两年;参加派对,时间段是四小时;派对后宿醉,时间段是八小时……Fax走后,我突然意识到时间不再是一段一段的存在,而是一整片,一整片,从现在,到死亡。
有时候,我忍不住臆测,为什么当初JZ要把我们两个人拉在一起,我们会将未婚男女拉拢捉对,希望他们有可能发展成圆满姻缘,即使不圆满,但也可能倍数繁衍,由二扩充为四,翻涨一倍,成为一般人心中的完整家庭,这世上完满之现象太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东坡早就说了,此事古难全。完满做不到,至少还可以做到完整,没有永浴爱河不要紧,如果能貌合神离让大家看到白首偕老,也算功成身退,就算半路分道扬镳,也好过从头到尾孑然一身,至少创造出了宇宙继起之生命啊。
后来,当Fax多次当众宣称,我是她最好的朋友时,我突然明白了,因为JZ早已发现我们两个人都需要朋友。也许你会说,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朋友,其实不然,只要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需要的是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象,甚至于敌人,而不是朋友,所以他们彼此猜疑、嫉妒、竞争、较劲,见不得对方好,也见不得对方差,因为对方走下坡了,就不值得来往,无法符合利益,他们真心想要的并不是朋友,那种可以在寂寞时彼此陪伴,消磨时光,诉说心事的朋友。
而我是Fax的朋友。
Fax走后,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下我的父母,再没有一个人,让我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相信,我对他永远都是重要的,再也没有。
在Fax走后,我就像个老人,频频回顾,妄想在某个时间点上改变这一切,这个念头一旦出现,突然觉得自己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扭转,却不自觉,任由机会稍纵即逝,悔恨不迭。好比,25岁那年,我们同时扮演着介入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尽管我们的爱人有许多不同,但我们的心情却有许多相似,尤其是周末家庭日时的寂寞,我们先是一起逛街吃饭打发时间,然后去租录影带,有一回选好了片子,在忠孝东路的顶好超市,我拿下货架上的一瓶苹果气泡酒,酒精度4,回头问Fax:“喝这个?”“好啊,没喝过,喝喝看。”Fax说,微微的气泡,淡淡的果香和酸甜滋味,还有透明的浅绿色,都让我们觉得比汽水好喝,但,时间若能回到那一刻,我是不是不该拿下那瓶酒,是不是我不拿下,8qwP9RqbfhY8QjHhvlJRRahu5a2Js/68Hbj2AhW2I4M=后来Fax就不会因为饮酒引发猝死了呢?
又好比,26岁那年,我匆匆结婚,随即发现是场错误,其实错了,结束就是,当时却不知如何应对,真是涉世未深,只想逃避,索性辞职去了美国。Fax打电话给我,说和老板发生不愉快,三个同事商议后决定另起炉灶,自立门户,我买了一张卡片,祝贺Fax的新开始,突然发现不会背她住处的地址,只带了一张她的名片,算算时间月底前可以寄到,她还没离职,就寄到她的旧公司。如果我故意寄一张明信片,没信封的,让Fax老板看到,破坏她们自立门户的计划,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日后合伙人卷款潜逃的灾难,也许Fax整个人生都会不同。
但也就因为在回忆中有太多可以扭转的时间点,一切反而更形虚假,所有以为可以改变的时机,其实都只是错觉。
从美国回来后,我的生活熙攘而混乱,但至少下了决心结束短暂的错误婚姻,这个决定给了我义无反顾的勇气,我以为自己历经沧桑,其实只是年轻,离婚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那是单身者所不能体会的,一种接近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情吧。突然,我的身边出现许多追求者,有一回,我整夜没回家,和新认识的一名律师在巴塞隆那连看两部艺术电影,缺乏故事性的情节随着暗色调光影推移,离开名为巴塞隆那的MTV时,我脑子的空虚困乏正像搭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因为不想穿着昨天的衣服出现在办公室,惹人非议,于是我在Fax公司楼下服饰店买了一套衣服,然后到她公司换,脸上还是昨夜的妆,意外的是镜中的自己并不疲惫,我用吸油面纸吸去脸上的油,再薄薄铺一层蜜粉,Fax从繁忙的业务空隙中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不错,妆画得不错,看不出来一夜没睡。”
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啊,才敢大胆挥霍,怎么知道,Fax竟就再也收不了手了。
下班后没事的夜晚,我们偶尔会去复兴南路的躲猫猫,喝一杯马丁尼,吃一盘烟熏芝士配葡萄干,加晚班的Fax,和报社发完稿的我碰面时往往已经十点,这时候再喝咖啡,晚上铁定失眠,喝杯酒回去还睡得好些。年轻的我们天真而又充满热忱,这热忱不仅用在感情上,也表现在对事业的追求,虽然我们赚的钱很少,但我们看不起逃税的人,我们坚持一个有能力的人应该愿意为社会付出,纳税是最基本的义务,再有能力就应该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我们不认同炒房炒股营利,长期投资另当别论,短线炒作就算获利也是不务正业,凭空而来的利益对社会没有半点贡献,我们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劳力和智慧,得到应有的报酬,这报酬不仅符合正义,还可以鼓励别人,我们曾经是这样相信的,就连相聚时第一次举杯,我们也总是祝愿国泰民安,我们有热忱,这热忱不仅在自己的事业上,同样愿意用在社会,真的,至少我们曾经努力这样做。那时我已经搬到Fax的楼下,在躲猫猫混了几个月,我抱着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贪玩念头,提议我们开家酒吧,前一晚我们还在家里无聊地吃火锅,第二天剧情急转直下,我们竟真顶下了一家酒吧,酒吧在台北新生南路。
而新生南路也成为我这一生回忆最多的一个地
方。
十一月,杭州的深秋,法国梧桐开始转黄,车经西湖,落叶不停歇的坠落。
立冬前几天,朋友来西湖玩,为了讨女友欢心,特地订了香格里拉酒店,我以前去香格里拉吃饭喝咖啡,都在西楼,竟不知另有东楼,朋友订的豪华阁湖景房就在东楼的顶楼七楼,他放下行李后,我们在六楼的回廊喝咖啡,配着巧克力燕麦饼和奶油薄酥饼,当然最重要的是整片西湖湖景阔朗展开,一览无遗,苏堤深入碧绿的湖水,画舫悠闲穿梭,曲院风荷茂密熙攘,荷叶虽已见枯枝,但是树木依然青翠,绿的黄的浅褐的,层次更显分明。香醇的热咖啡逐渐将我拉回台北,摄氏十六度的阳光,金灿灿的温煦中微微透着寒意,贪恋湖景的我坐在回廊,竟恍惚想起阳明山上的白云山庄,其实风景迴异,若真要追究,顶多是高处俯瞰这点略有相似吧,但视野中的风景却是大异其趣。
两次去白云山庄吃饭,都是和Fax,她对白云山庄有特殊偏好,她没告诉我原因,我猜是以前顾青带她去过,她喜欢坐在窗边看夜景,和我欢快地聊着,因为酒精的催化,微微显出亢奋,后来回想起来,她是在向自己证明,即使没有顾青,生活也不会改变。
后来她开了龙舌兰之后,我们再也没去过白云山庄,龙舌兰时期的Fax活动范围几乎不出延吉街忠孝东路四段,偶尔去了民生东路中山北路一带,都是有重要饭局,是过往记忆禁锢了她?还是谁的咀咒局限了她?
认识顾青的时候,Fax27岁,我不确定顾青的年龄,但应该和Fax有将近二十岁的差距,那时Fax刚刚自立门户,顾青教了她许多,也帮了她许多,Fax对他的情感,除了情人间的缠绵外,多少还带点父女般的依恋。Fax认识他就知道他有太太,顾青也从未说过自己可能离婚,Fax自己要爱上他,要陷溺其中,怨不得谁,但是交往了差不多一年,Fax难以接受的是她逐渐发现自己称不上小二,充其量只是小五,在她之前,顾青至少还有两个外遇对象,Fax说的是还在继续的,已经分手了的不算。
“你怎么发现的?”我有点不解。
“顾青生日,我要花店送了一盆花去他公司。”
Fax的作为我当时并不了解,女人送男人花,在我看来是多此一举,且匪夷所思。多年后我才懂得其中暗藏的语言,那是:我希望你送我花,但你不送我,我只好送你了。
另外一层是:Fax受不了忽视,如果她喜欢一个人,她总会不甘寂寞做些引起对方注意的事。
“送花到办公室,会不会太高调了?”我提醒Fax。
“顾青说他老婆从不去他办公室,我才送的,没想到老婆是不去,但情人会去,花店送花去的时候,他女朋友正好在,花店一放下花,那个女人就抢走了卡片,然后质问顾青,顾青竟然说我是和他开玩笑。”
“息事宁人,顾青只是不想把事闹大,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顾青公司的赵霞姐说的。”
“她和你说这些干嘛?不是惟恐天下不乱吗?”
“这就是让我生气的另一个原因,顾青的另外两个女友原来在公司都是公开的,只有我是地下的,所以赵霞姐真以为我在闹顾青,才说我事闹大了,给顾青找来大麻烦了。”
“顾青不让别人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我想也是保护你,等你要嫁人了,别人还是不知道这一段的好啊。”
“怎么你说的和顾青一样,那为什么另外两个他就不保护了呢?”Fax不满地嚷嚷,其实我想她心里不是完全不明白,只是这件事不但伤了她的感情,也伤了她的自尊。
这一发现让Fax失去平衡,顾青有老婆,她无话可说;可除她之外,还有两个情人,让她很受伤。她一边含泪说要分手,一边又背地里死咬着牙跟踪他,只是跟踪,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何苦呢?”我问。
“我想看看那两个女人什么样子?”
“看到了吗?”
“看到了一个。”
“什么样子?”
“没我漂亮,也没我可爱。”Fax嘟着嘴不满地说。
我瞪她一眼,示意她别废话。
“我完全没想到,那个女人看起来有40岁了,并不好看,真的,身材也普通。”
“可能他们在一起很久了,顾青也40好几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现在很多人40岁看起来只像30岁。”
“也许她是50看起来像40。”我随口说。
这回换Fax瞪我。
“顾青发现你跟踪他了吗?”
“没发现,但我告诉他了。”
“你有病啊,要是我被跟踪,一定和你分手。”
“唉,我忍不住说我看过他的女朋友,他一直追问怎么看到的?好像很紧张,我一气就……”
“他一定怕你继续跟踪他,说不定还去找他老婆。”
“不会的,我不会去找他老婆,也不会和她见面。”
“为什么?”
“这是基本原则,顾青应该懂得。”
Fax所谓的基本原则,是情妇的基本原则,她认为情妇不应该也没立场找元配。但后来她还是见到了正牌的顾太太,在顾青的葬礼上。
就在Fax因为发现自己不是顾青惟一的情人,开始脱序的行为后不久,顾青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Fax哭着在电话里告诉我,偏偏那天我报社忙,六点我打电话找到一个蝴蝶养猫的熟客范迪,要他七点店一开就去陪Fax,并且要准备至少一打的笑话讲给Fax听,直到我十一点出现,范迪努力苦撑,Fax始终冷着一张脸,不理不睬,范迪坚持着,赔着笑脸,直到十一点半,我终于可以离开报社,赶到新生南路,Fax看见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就不能让我静一静。”
心烦气躁的她,一定也明白我们的心意,范迪不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疲惫地离去,我说:“我问了跑医药的记者,大肠癌是治愈率比较高的癌症。”
Fax点点头,泪水迫不及待夺眶而出
顾青的情况却远比想象中严重,手术后,只短暂的恢复工作,很快就发现扩散,住院期间,Fax担心得不得了,却不方便看他,这时候她愈发明白自己没有立场,她有一次问我:“如果是你,你会让你老公的女朋友看他吗?”
“如果他想见,我会的。”
“我也相信他老婆会,”但顾青说,“不想在这最后一段时间增加对他老婆的伤害,她已经要承受老公的病,如果还得同时承受老公的不忠,太残忍了。”
我觉得顾青的顾虑不无道理,Fax说:“那我呢?已经没多少时间了,难道我就不受伤吗?”
等终于找到了空当,Fax去探看顾青时,他已经无法行走,坐在轮椅上了。他的病情恶化的速度超乎大家的想象,一天傍晚,我接到Fax的电话,这一回她倒没哭,她说:“顾青走了,你可以陪我吃晚饭吗?”
“好,没问题。”
我打电话交代酒吧的工作人员几句,告诉他我们今晚不去蝴蝶养猫了,有事打我的呼叫器,90年代,那是个手机还不普遍的年代,我带了一瓶XO,Fax和我约在忠孝东路巷子里的东花坊,是一家日式创意料理,我们各点了一份套餐,我放下XO,说:“今晚我们喝光它。”
我不知道如果Fax哭,该如何安慰她,她却一直没哭,倔强地板着一张脸,批评每一道菜。
几天后,Fax在葬礼上见到了顾太太,Fax形容她气质很好,温柔有礼。
“她会不会怀疑我?”Fax问。
“为什么?你觉得她直觉知道你们有事吗?”
“不是,我哭得太伤心了,抽搐不止,如果有一个女人在我老公的葬礼上这样哭,我肯定会怀疑的。”
“人都不在了,怀疑又能怎样?”
“要是我,我会为他高兴,至少除了我,还有人爱他啊。”Fax说。
我们很少再提起顾青,只是打烊前,Fax偶尔会放蔡琴唱的误点梦,“送走了人间悲欢,转过身水月镜花,只剩下一片云,多情真难舍,痴心又难留,不得不自己走……”那是顾青生前喜欢的一首歌,我们坐在喧嚣闹腾过刚刚安静下来的酒吧里听着:“谁知道梦一半天已亮,梦里的你和醒来的我,相爱这么难。”
梦里的你和醒来的我,如今回头细想,竟是Fax爱情路上的写照。但是,30岁的我们,对未来仍有憧憬,不知道命运有时真的残忍,又或者是自己傻得一错再错。记得Fax很喜欢一部美国好莱坞电影,麦克道格拉斯演的,片名翻译为《白宫夜未眠》,总统追求一名环保推动者,结果连打电话订一束花都碰壁,因为花店一听说账单寄白宫,就认定是恶作剧,立马挂了电话。Fax憧憬的爱情不是平凡伧俗的,其实哪个女人是呢?只不过大家在人生里学会了,从可以选择的机会中找幸福,Fax却不甘心放弃。
那是一段短暂的简单而纯粹的日子,在顾青走后,我们两人都处于情感的空窗期,时间被工作和蝴蝶养猫填满,天天累得只希望能好好睡一觉。
有一回,白天遇到以前的男友携新女友逛街,我急忙闪开,深怕他们看见我,晚上在蝴蝶养猫,我和Fax讨论这件事,我怕他们看见我,究竟是避免尴尬,还是担心正面比较,那阵子,白天跑新闻晚上照顾酒吧,差不多天天穿条牛仔裤衬衫慢跑鞋,连新衣服都没空买,两人不觉自怨自艾起来,于是决定打烊后立刻去买衣服,蝴蝶养猫两点打烊,我们先去了通化街夜市,夜市只剩下小吃了,卖衣服鞋帽饰品的都收摊了,我们想起曾在深夜去林森北路吃宵夜,记忆中热闹非常,两个人于是招了计程车去林森北路,结果服饰店倒是开着,但服装款式完全不合适,多是极短的裙子,包裹得曲线毕露,显然是针对林森北路特有的客层酒店小姐设计,我和Fax只好吃碗米苔目卤大肠,回家睡觉。
日子忙碌,但我们却拥有彼此的陪伴,真实的温暖的陪伴。
1995年吧,我们顶让出了蝴蝶养猫,当时我正计划再度结婚,我原以为Fax可以全心发展事业,她夸下诳语,说她的公司将会上市发行股票。没想到她讲出这句话不到半年,生意就彻底垮台,在她公司倒闭前一个月。她说要买我的房子,但是没有现金,所以要我先把房子所有权变更为她的名字,她开给我两个月后的支票,她估计房屋贷款两个月内可以办下来,谁会料到她的合伙人突然消失,等一批又一批人来要求结清拖欠的款项时,她才发现公司的账户没有任何钱,留下的只有数不清的债,债权人包括她的朋友、客户,也包括我。因为她,我失去了所有积蓄,后来想想,如果不是已经将工作十年存的钱买下的房子,先过户给她让向银行办贷款,此时我会拿房子抵押给银行帮她吗?一个月前,我把房地契交给她时,代书曾经警告我不可以这样做,我没听,Fax是我的朋友,我相信她不会骗我,但谁能想到合伙人卷款潜逃的事。
债务曝光后我们才发现,所有能够用到的关系,Fax都借了钱,她试着向大家说明,公司营运没问题,只要给她时间,她可以将账目填平,一开始,朋友也愿意宽延,但眼看着显露出来的窟窿愈来愈多,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一天,我下了班过去陪她,那一阵子我很担心她想不开,她开给我的支票连续跳票后,银行劝我告她,我说,Fax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告她的,银行的人在话筒那端说:“这种事我们看多了,一点关系没有,怎么会有财务纠纷?有纠纷的往往都是亲近的人,票据法是有有效期的,过了就没法告了,你自己想清楚。”
银行的人果然说得没错,有财务纠纷的往往是亲近的人,就在那天晚上,又有人来讨债,是Fax结识多年的常姐,常姐陆续标下几个会,将钱全借给了Fax,现在她背的会钱,她该怎么还?常姐边哭边骂,Fax一声不吭,常姐急了,上来就给了Fax一耳光,Fax还是不言语,我在旁边劝解,Fax真没钱,再怎么骂她打她也无济于事,再给Fax一点时间,留待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语无伦次地劝着,常姐气急败坏,最后拿走了办公桌上一只专门搁置硬币的玻璃缸,常姐扔下一句:“就是会钱付不出,我被人打死,我的孩子也还要吃饭。”
我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Fax面对了多少这样的讨债人,受了多少屈辱,她这样要面子,当然是不愿意说的,那段时间里,她一再反复告诉自己,一定要东山再起,她要让那些羞辱过她的人知道自己看错了,Fax绝对不会一蹶不振的。
只有这样,她才有勇气面对明天,还有另一个明天……
我反复地问自己,如果不是我惟一的资产已经失去了,这一刻我会倾其所有帮她吗?理智分析,我没有能力帮她,我的财力相较于她的债务,只比杯水车薪略好些,但是情感上很难置身事外,不过这令我无需矛盾烦恼纠结,无需苦苦思索,因为她已经先让我一无所有了,我反而有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轻松。
我只要她答应我,无论遭遇什么,都不准做傻事。
Fax答应了。
但是,我不完全相信,因为Fax的债务压力之大,已经难以想象,有人将她开出的支票转给了地下钱庄,地下钱庄的人打电话威胁她,她不理,豁出去的她,什么都不怕,于是那些流氓转而找Fax的爸妈,奉公守法一辈子的老夫妻,一早开门,墙上全悬红漆写的不堪入目的字,Fax的弟弟妹妹表示爱莫能助,事实上债务之大,也的确不是他们能够负担,地下钱庄的人不肯罢休,继续骚扰Fax的家人,无可奈何,Fax的爸妈听从别人的建议,搬了家,这一回他们没再带着Fax的户籍,力图撇清关系,也彻底伤了Fax的心,从此没再回家过,直到她走完人生,她的牌位才终于接回家。
我真的相信Fax不会寻短,是在邓丽君去世那天傍晚下了班,我买了些简单的吃食去公司看Fax,路上听到了新闻广播,知道邓丽君的死讯,踏进办公室我还来不及说这令人意外的消息,Fax先说了,她也从广播新闻中得知,我们不禁感慨,真是太可惜了。Fax说:“只有活着,人生才有可能,死了,什么都没了。”听了她的话,我突然相信她会坚强地走下去,Fax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
那一天我们难得的没提起公司债务的事,聊的全是小时候听邓丽君唱歌的往事,我有一张黑胶唱片,邓丽君唱的晶晶,那时的邓丽君只有14岁吧,谁会想到这样一个甜美的人,竟不长命。
是啊,谁会想到。
但现实还是让Fax逐渐明白颓势难挽,她突然改弦易辙,做起了酒品买卖,和她因为复杂的债务关系新结识的一群朋友,我以为,毕竟我们曾经经营过Pub,她的公司原本也是做贸易的,也许相较起来,比其他行业容易入手,见她没有一蹶不振,我很高兴,也希望为她尽一点力,做生意我是外行,但是她觉得记者的头衔在应酬场合对她或多或少有助益,于是她时常要我陪她一起应酬,下班后的深夜里,我们出入日本料理店,然后往复兴北路脂粉云集的Club续摊,当酒酣耳热,气氛升温之时,我们相偕告退,留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