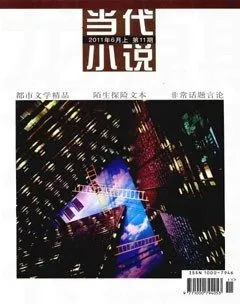地下交通员
俺叔是那天夜里走的。
那是一个雨夜。下着麻秆雨。电闪雷鸣的。
马家村俺三舅爷爷马继玉的院子里积满了水。
躲在俺三舅爷爷家里的俺爷爷,披着蓑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俺奶奶扒着门框说,死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俺三舅爷爷的家人,也劝,也要俺爷爷先躲躲雨,别把这把老骨头淋散了,俺爷爷也不听。俺叔还在粪窖里,俺爷爷得回去救俺叔,雨这么大,能存住气?能要命?
麻秆雨咋就下个不停了呢?不知道家里的雨,是不是也这么大,粪窖里灌进水了没有。要是灌进去了,灌满了,俺叔就惨啦,淹不死,才怪哩。
俺爷爷是一棍子把俺叔打闷,捆了的。
俺爷爷捆俺叔,是怕俺叔跟着一个唱坠子书的女戏子跑掉。
俺爷爷虽然喜欢听戏,却看不起那些戏子,尤其看不起那些女戏子,哪怕是名角,满天红的名角,俺爷爷也看不起。俺爷爷怕俺叔娶个戏子来,把家风给败坏了,豁出命来反对,俺叔就和俺爷爷讲理,死活都要这个戏子当老婆,俺爷爷就把俺叔打了。兜头一棍子把俺叔打晕了,怕俺叔醒来再跑,找了根麻绳就把俺叔给捆了。俺爷爷刚把俺叔捆了,日本鬼子就要进村了。
日本鬼子进村是针对俺家来的,是专门来抄俺家老窝的。是汉奸刘七的汉奸队带的路。离村没几里地了。信,是一个要饭打扮的人送来的。这人摘下草帽,俺爷爷俺奶奶一看,竟然是俺奶奶的堂弟——小三,俺的小三舅爷爷。俺爷爷不信,说,俺家又没共产党,鬼子汉奸咋就专抄俺家?俺爷爷又说,我一个死老头子,都到活埋的年龄了,要剐要杀,随他们。没有一点躲避的意思,俺三舅爷爷就把褂子角猛一撕,撕出一封俺爹的亲笔信,俺爷爷不但不再犹豫了,而且满脸惊骇。俺爷爷做梦也没有想到,多年没见的俺爹,竟然是菏泽、定陶、成武、金乡、巨野五县边区工委书记,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也没想到失踪多年的俺三舅爷爷,竟然一直跟着俺爹,还活动在这一带。
俺三舅爷爷还没进村时,大街上就有人敲着一面破锣,“咣咣”的,大喊大叫着,“乡亲们,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和汉奸队就要进村了!日本鬼子和汉奸队就要进村了!乡亲们快跑啊!乡亲们快跑呀!往西跑,往西跑啊!跑出这个村子就没事啦!”嗓门浑厚有力、高得出奇又有些耳熟,像那个说书的小红她爹的声音。这怎么可能是他呢?这不可能!再说,俺爷爷正在为俺叔要娶他闺女小红这个戏子修理着俺叔呢,没顾上多寻思。俺三舅爷爷来了,这样来了,俺爷爷信了。可是,往哪儿躲?咋着躲?俺叔还让俺爷爷收拾晕了,还没醒过来呢,这么大块头的一个人,扛又扛不动,咋着躲?把俺叔藏了?往那儿藏?
枪声在村口上响起来了,越来越密,俺三舅爷爷都急出泪了,从腰里拔出驳壳枪来,顶上火说,姐夫,再不走,就没有时间了,没时间了!又说,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你和我姐要是有一点闪失,是要受处分的,要受大处分的!俺家的大粪窖里刚起净的,没多少粪便,俺爷爷心生一计,把俺叔先扔进了大粪窖里,心想,躲过这一劫再说吧。
鬼子血洗了俺村,烧了村里的房子,俺爷爷豁出去要和小鬼子拼了,和汉奸刘七拼了,俺三舅爷爷死挡着,不让俺爷爷去。房子烧了没啥,关键是俺叔,这都三天了,俺叔是死是活没一点音信,俺爷爷心里着火呢。俺三舅爷爷天天去打听,打听那些狗日的小日本鬼子和汉奸刘七走了没有。今天一早又去了。这都半下午了,来回也就是十几里路,咋还不回来呢?天又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松一阵,紧一阵。俺爷爷心里的火,越着越旺。
俺三舅爷爷终于回来了,趟着院子里的积水,披着蓑衣,水漉漉地回来了;进院子把大门拴死说,姐夫,日本鬼子走了!汉奸刘七也走了!俺爷爷忘了骑来的俺叔的枣红马了,披着蓑衣,开开大门就冲了出去。俺三舅爷爷一把拉着俺爷爷说,姐夫,俺扒着粪坑看了,里面没有小六了,你别回去了,说不准还有汉奸的暗哨候着你呢!俺爷爷牛眼一瞪,甩开俺三舅爷爷,拍着胸口说,都到这个份上了,你姐夫还怕死?俺三舅爷爷就在后面追着说,姐夫,你不能出一点事。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俺爷爷一边往俺村方向跑着,一边说,屁任务呀!不就是一把老骨头!俺三舅爷爷没辙了,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一捏,伸进嘴里打了个呼哨,立时从雨里走出了几个人影,前后照应着。俺奶奶见俺爷爷、俺三舅爷爷都走了,都去了俺村,顺手抓起一个斗笠,也冲进了雨里。俺三舅爷爷的老爹在后面跺着脚,说,大侄女,那是男人的事,你就别去了,回来吧。俺三舅奶奶就冲进雨里,扯住俺奶奶,怎么扯也扯不住。雨哗哗地下着,像要把这个世界淹了。
鲁西南农村的厕所,大多是窖式的。在院子里避影的一角,挖个大池子,很深的大池子,人跳下去都能蒙了。然后在粪池上加上几根棍子,上面搭上黍黍秸,罩上稷秧子,培上土,仅留一个洞洞。人蹲在洞洞口上方便。粪窖里攒上一季的粪便,粪便也捂好了,发酵了,起出来上地,不伤庄稼。俺家的人口多,大小十几口子人,三世同堂,还有长工短工,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粪窖挖得特别大;大得像一间小房子,能扔进去两辆大车。小日本鬼子来了,走的走,逃的逃,就剩下俺爷爷、俺奶奶、俺叔,三口人,粪窖还是这么大。不是俺爷爷不想改造一下这个大粪窖,是俺爷爷想,人早晚还得回来。几年过去了,只听见枪炮声,却见不得半个人影回来。尤其是俺爹,把俺爷爷、俺奶奶、俺娘扔在家里,一去几年,鬼影不见。不是俺爷爷、俺奶奶身边还有俺叔,俺爷爷怕是活下去的心劲都没了。
俺爷爷几乎是跑到家里的。雨还在沥沥啦啦下着,虽然没那么紧了,也不小。
俺爷爷快60岁的老人了,跑得像射出去的箭似的。
路滑,俺爷爷不时地摔倒,摔倒了爬起来,再跑……
大门让日本鬼子和汉奸刘七砸烂了。房子也没了。五个院落,大小30多间房子啊,除了几间低矮的土棚子,全没了。是烧没的。烧得连根囫囵檩条都没了。不是这场雨,怕是院子里的树也被烧没了。俺爷爷顾不得这些,跑到家里,跑到粪窖边上,把蓑衣一甩,“噗通”一声,就从窖口上跳了下去。接着,“砰”的一声,粪窖的顶棚就飞了起来,飞了老远,飞得俺三舅爷爷俺奶奶满身的泥水。俺爷爷在大粪窖里摸了半天,却连根头发也没摸到,俺三舅爷爷就说,俺说没有就没有,你就不信。俺爷爷脸木着,说,人咋就没了?我捆着哩。俺奶奶就说,你个死老头子,你要不是捆着,俺还不恁担心呢,这人都让你捆没了,你说,你说。俺奶奶说着,嚎啕大哭起来。俺爷爷低低地叫了一声说,你嚎叫个啥呀!这是逃生了,逃生了!俺奶奶还是哭,只是声音没那么大了,说,要是那些王八蛋抓了呢?俺三舅爷爷说,小日本鬼子和汉奸走了,俺就来看了,没小六。又说,日本鬼子没抓走一个人,也没杀一个人,俺都查过多次了。俺奶奶才不怎么哭了。
俺叔是俺爷爷、俺奶奶的老生儿啊,是俺村里的一个大混混。俺叔这个混混,是俺爷爷、俺奶奶仗着有几十亩土地,有一大家子人家,还有一个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官的大儿子,惯起来的。俺叔这个混混和街面上的其他混混一点也不一样。喊俺叔混混的人,也只有我们的家人,再说具体一点,也就是俺爷爷俺奶奶和那些疼惜俺叔的亲戚,比如俺那些舅爷爷,俺那些七姑奶奶八大姨姥姥。要说起俺叔这个混混来,那话就长了。
俺叔排行老六。俺爷爷、俺奶奶都想让俺叔也像他的五个哥哥那样,不去城里读书,起码也要到城里学会一样吃饭的手艺,可俺叔小时候很痞。俺爷爷俺奶奶说出来的话,对俺叔来说还不如一个屁哩。你千说万说,俺叔都给你来个死气不吭,照样玩他的,折腾他的。俺叔六七岁到十二三岁吧,领着一帮小屁孩,不是砸人家寡妇门,就是爬人家新媳妇的墙头,把人家新媳妇浆洗的衣服、被褥什么的,都用锅灰画上画。这些画,当然是黄色的了,虽然没有一样像那么回事的,却就是那样的。俺叔在外面戳一回事,俺爷爷就会揍他一回,可俺爷爷却从来不是真揍,揍俺叔的目的把俺叔吓跑了就行,何况还有俺奶奶护着俺叔,俺爷爷又让着俺奶奶,俺爷爷觉得俺奶奶放个屁都是香的,所以俺叔真正挨揍也没几次。按俺爷爷的脾气,要是揍俺叔那就是往死里揍了,不把你揍得脱层皮不算完。
俺叔这个痞劲的,久了,邻里们就不让孩子跟俺叔玩了。怕跟俺叔学坏了,长大了成不了好孩子。可俺叔从来不怕谁不跟他玩。俺村子大,三四百户人家,小屁孩多了去了,这拨不跟他玩了,他就又有了一拨。一拨接着一拨,身后从来没断过七八个小屁孩。俺叔不光玩,还好喜打抱不平,看哪个小屁孩欺负人了,不把人家打个鼻青脸肿不算完啊。你说,都是些吃屎的,你咋就知道人家是在欺负人呢?这时的俺叔,搅闹得四邻没个安静的时候;不是俺爷爷、俺奶奶为人善良,又有一大家子人罩着,还有个在南京当官的大哥,怕是早让人家填到井里或者摁死在粪窖里了。从小就惦记上俺叔的,不仅仅是后来的汉奸刘七啊。
俺叔是从什么时候不搅扰四邻了,没人说得清楚。
俺叔不搅扰四邻了,村里人突然发现,俺叔竟然是俺家长得最帅气的男子汉:身高一米八五,五大三粗,竟然还满脸的秀气和羞涩,和邻居说话,无论男女,还没张嘴就脸红脖子粗,直挠后脑勺,但俺叔贪玩的脾气,还是没改。俺叔不贪玩也没办法啊,家里有长工也有短工,什么活俺爷爷、俺奶奶都不舍得让他干,像村里私下说的那样——养了个人种。说俺爷爷、俺奶奶养了个人种,那是要把俺叔冤枉死了的。俺叔从来不拈花惹草,从十二三岁就有媒人给俺叔说媒,见的大闺女多得去了,有城里的,也有乡下的,个个似花如玉,俺叔愣是没看中一个。俺爷爷、俺奶奶宠俺叔啊,俺叔看不中,俺爷爷、俺奶奶嘟囔几句,也就随俺叔的便了。再说,俺叔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娶妻生子了。俺爷爷、俺奶奶已有了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了,根扎下去了,俺叔早娶晚娶,俺爷爷、俺奶奶都不怎么在意了,但也不是完全不在意。有时候,俺爷爷、俺奶奶猛然看到俺叔在眼前,像根大烟囱似的戳来戳去,戳得眼疼。都二十三的大男人了,人家的孩子都会打酱油甚至顶个劳力满地里干活了,咱还没个媳妇,也是愁呀;只是这个愁,没那么痛就是了。
俺叔在家没事干,就牵着俺大爷从南京给他弄来的一条猎犬,一条沙巴索·西班牙犬,扛着一条土枪,满世界打猎。这条沙巴索·西班牙犬,是条公犬,叫巴尔塔萨;俺大爷送给俺叔时就叫巴尔塔萨。巴尔塔萨30多斤重,两尺多高,白胸脯,红脊背,雪白的四肢,耷拉着大大的耳朵,眼睛瞥拉着,看人时含情脉脉,像个未出嫁的大闺女,但却非常凶猛,有极强的攻击性。俺村里很多人见过俺叔打猎,枪扛在肩上,也没见他瞄准,土枪“嗵”的一声,巴尔塔萨就飞奔过去把一只野兔子衔来了。俺叔只要出去打猎,都带着巴尔塔萨,然后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嗒嗒’地走了,回来时,枣红马身上绝对要有七八只兔子。一只兔子三四斤重,七八只就是二三十斤。俺家吃不了,就便宜邻居家了。俺奶奶总把多余的野兔子分食给邻居。邻居们只要看到俺叔,“嗒嗒”的骑着枣红马出村了,心里就很甜,口水随之就流下来。
俺叔除了打兔子,就是喜欢听戏了。这一点很像俺爷爷。只是俺叔不像俺爷爷那样喜欢听大戏,而是喜欢听小戏,也就是地方曲艺。比如鱼鼓、坠子书、扬琴等等。
这些地方曲艺啊,俺叔又最喜欢听坠子书,听上瘾来,能骑着枣红马跟着说书人跑二三十里路。俺叔也不是谁的书都喜欢听,俺叔最喜欢听小红和她爹唱的坠子书。掌灯时分,小红和她爹,在场院里或者在街道一棵大树下面,摆上一张桌子,点上汽灯,小红她爹的坠胡胡琴一拉,小红往桌前一站,左手高高一举,枣木简板“叭叭”一打,右手“嘣嘣”轻敲几下桌子上的小鼓,爷俩一晚上的书就说起来了。
小红和她爹第一次来俺村里说书,是1936年的春暖花开季节。是来给俺奶奶祝寿的,说好了唱三天就走。三天下来,俺叔说啥也不让人家走了,让人家继续唱。人家一下子又唱了七天,就这样把俺叔迷上了。那时小红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没有一点粉脂味,扎着个大辫子,梢上扎着根红头绳,像只红翅膀的蝴蝶,飞来飞去。小红个儿不是很高,穿着一件白花蓝底大襟夹袄,一件大裤腿的黑色裤子,脚踏布鞋,却很稳重,很大气。尤其是小红的唱腔,起腔、平腔、送腔、尾腔,步步到位,唱词中使用的三字崩、五字嵌、七字韵、巧十字、拙十字、寒韵等,也很惹人耳目,乖巧得很。小红她爹不到50岁的年纪,精瘦,一脸饱经风霜的样子,轻易不说话,说话时声门高大而又浑厚,要把人的耳朵震聋似的,听一句,一辈子就不想听第二句了,聒噪,但坠胡拉得那是没比的,尖细时就尖细,粗狂时就粗狂,愤怒时就愤怒;如行云流水。俺叔做梦都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的说书人,唱的,拉的,都是一流的。尤其是小红的嗓子,那个质感啊,那个美感啊,听进耳朵里就镶上了,拿钳子使劲夹着,薅都薅不出来;一宿一宿地听,都听不够。小红和她爹说书,说的是《施公案》。从第一回“胡秀才告状鸣冤,施贤臣得梦访案”说起,起伏跌宕,环环相扣,激情澎拜,肆意荡漾,一直说到第六十一回“皇恩诏贤臣,回京都引见”。
小红和其他说书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喜欢拿国家的事打比方。《施公案》里的坏人,那便是当今国民政府什么要员,好人自然是岳飞岳鹏举了。说得大家群情振奋,恨不能立马去抓着那些坏蛋,宰了。后来日本鬼子入侵我中华民族,这大坏蛋,要么就是东条英机,要么就是日本天皇裕仁或者其他什么日本鬼子。三天下来,全村人都知道了东条英机和裕仁这俩大坏蛋了。夜里做梦都扒他俩的祖坟,鞭他俩祖宗的尸哩。
之后,小红爷俩便不请自到;到了后,继续接着上回说《施公案》。每次来,有时候说一晚上,有时候说两晚上或者更多晚上,不定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打游击似的。
小红和她爹是哪里的人氏,都说不清楚。问人家小红爷俩,小红爷俩从不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笑笑而已。
问小红她爹的好朋友张大山,张大山就说,闲事管得不
少!不说。村里的人就开始猜起来了,有人说是巨野的,
有人说是曹县的,也有人说是成武的。可俺叔却坚信小
红爷俩是成武的。说,坠子书是以我们成武为中心,然
后流传到黄河下游地区,都二三百年了,唱这么好,不
是成武的,还能是哪儿的?
俺叔是个戏迷,村里来了说书唱戏的,还撵着人家听,有时候都撵上几十里路去听,是常事。小红唱这么好,把俺叔整个人都唱迷糊了。小红爷俩每次来了,俺叔都是大睁着两眼,坐在前面听,还把给小红爷俩倒水喝的事儿,揽下来了。人家唱完要走了,俺叔满目顾盼舍不得人家走呢,恨不能让人家小红爷俩住在俺家里,永远不走了。舍不得人家走,不是你的人,你不当家,人家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再说,再富裕的人家,天天听戏,也听不起呀。俺叔只能看着人家小红爷俩收拾家什,扛到肩上。俺叔喉管里艰难地咽着唾沫,牵着枣红马,把人家送到村头上,再送,再送,送到去徐州的宽敞官道上,看着人家走得很远很远了,还不舍得离去,不停地照着前面的黑点点,晃手,时常把眼里的泪水都晃出来。
俺叔每次送走小红爷俩,都很失落,发狠地满世界打上几天兔子,把心里的失落撒出来。
一天,也就是1938年农历4月15日这天。这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日本鬼子酒井支队,天还没放亮,百姓还没起床,就从金乡县城窜到成武县大田集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田集距俺村也就四五十里路,那边消息传过来,人就开始往外躲了。午饭时分,村里的人就很稀少了。俺大爷全家都在南京自然不用躲了。俺二大爷、三大爷,还有俺那不见影了的爹,虽然都在外面,在城里,家眷却都在村上,何况还有俺爷爷俺奶奶呢。半上午就来了三辆大马车,在县府上班的俺二大爷,腰里别着一把盒子枪,来拉家里的人进城,躲避日本鬼子。俺爷爷俺奶奶死活不去,说,俺俩都这把年纪了,日本鬼子还能把俺俩活吃了?俺二大爷把俺娘交给俺大爷,说,老四死活不知,不能叫老四家跟着俺俩受罪,照护好老四家,就行。和俺叔刚把三辆大马车送走,小红和她爹却来了,带着一身疲惫来的。俺叔看着小红爷俩,猛一吃惊,继而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说,这趟来,钱我掏了。领着她爷俩就往张大山家走,小红她爹就很悲伤的样子,说,不去他家了。俺叔扭身把她爷俩让进了俺家里。小红爷俩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放上一张老式桌子,摆上摊子。俺叔怕人少,人家难堪,牵出枣红马来,骑上,在村子里转。
这天的书,小红爷俩说得和以前不一样,打头,来了一段谴责小日本侵略我中华民族的段子,大家都群起愤怒了,才继续说《施公案》,说的是第二百零三回“李公然弹打玉面虎,白马李力战活阎王”。说了也就多半场的工夫,大家听得正起劲,来了个戴着草帽、掩着大半张脸的青年汉子。这汉子从后台上去,俺叔看着汉子的身影面熟,可又想不起是谁来,只见这汉子和小红她爹耳语了几句,扭身走了,小红她爹的脸色就变了,家里失了火,烧掉了全部家当似的,猛地站起来,险些蹭掉那个汉子的草帽,向大家深鞠一躬说,老少爷们,对不起了,家里有急事,这戏就说到这儿吧。俺叔不让。俺叔不让不是因为俺叔要出钱,是俺叔没听过瘾,俺叔说,要走,也得把今晚上的戏说完啊。小红的父亲说,少爷,家里有急事了,得罪了!等俺处理完家事,俺爷俩就赶过来,接着说,绝不食言!又深鞠一躬,不再多说什么,装起家什来,扛到肩上,要走。
俺叔恋恋不舍地把小红爷俩送到村口上,看着他们消失在漆黑的夜里多时了,才想起来还没给人家钱呢,回家拿了钱,牵了马,喊上巴尔塔萨,就撵。
俺叔傻子似的,撵了二三十里路,也没撵上半点影子,却撵上了一阵枪炮声,俺叔的头脑才清醒过来,丧气地回转了。
俺叔身后的枪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密,就像打在他的眼前,枣红马惊得都有点战栗,俺叔就担心起了小红爷俩,尤其担心小红姑娘。一个姑娘家,一个只会说书的姑娘家,咋能经得起这样急密的枪炮声呢?俺叔把枣红马拴在路边的一个树上,蹲下来,抽起了烟,心想,小红爷俩也许会被这枪炮声吓回来,可等到天明了,只遇上几个布衣的扛枪人。俺叔想上去打听一下,却又怕招惹是非,骑上马,带着巴尔塔萨回家了。
回家来的俺叔,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睁着眼,闭着眼,都是小红的影子。小红向他微笑的面孔,小红那举着左手打简板的样子,小红那细长的手指,小红那圆滚滚的手脖,以及手脖上那只玉镯,质地非常好的一只玉镯。玉镯不会是哪个男人送的吧?不会。怎么会呢?又怎么不会呢?会呢,会呢,就是会呢。俺叔又想起了那个戴草帽的青年汉子,真眼熟呀,可就想不起是谁来,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更想不起来咋这么眼熟。后来俺叔终于想起来了。这个青年汉子经常戴顶草帽遮着脸,出现在人群里。有一次还出现在张大山家里。是他,就是他。那是一天上午,饭时。俺叔走到哪儿,哪儿都是小红说书的声音,死死地把耳朵堵上,也能听到。听得像丢了魂似的。俺叔想起张大山和小红她爹是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自从张大山把小红她爹介绍到俺家唱戏,给俺奶奶祝寿,都是住在张大山家里,和张大山家里的人相处得跟一家人家似的,说笑,吃喝,全无住朋友的样子,俺叔就下意识地溜达到张大山家里了。这个戴草帽的青年人,就在张大山的家里,回脸朝里,坐在案板边上,听到俺叔的说话声,忙抓起案板上的草帽,“嗖”一下就进里屋了。俺叔很尴尬,张大山忙迎上来,堵在门口,眯着眼睛,笑着说,少爷,是不是来打听小红啥时候来咱村说书?俺叔满脸羞红,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了。张大山就笑。俺叔这才说,嗯,嗯。整天闲得蛋疼,想听书了呢。张大山笑着,又说,少爷,你是真想听,还是假想听?俺叔就有点急了,说,是真想听,真想听。可不知道人家在哪里说啊!张大山就说,这样吧,把你的枣红马借给我骑一下,我去找他们。俺叔满脸疑惑,说,能找来?张大山说,运气好了,有这个可能。那个青年人进里间了,张大山迎在门口是堵着不让进屋呀,原本就尴尬着的俺叔说了声好,扭脸去牵枣红马了。
村里人虽然一两千口子,能在街面站着的,没几个。
小红她爹的朋友张大山是村里的中医,祖辈传下来的中医,专治疑难杂症,又长着一颗善心,从不收穷人家的钱,名震四方,算一个;牲口贩子崔二捣,整天出门在外,能说会道,算一个;铁匠孙大手,打得一口好刀,好镰头,算一个;染坊齐,算一个……从村东头算到村西头,再从村北头算到村南头,来来回回算几遍,能在街面上站的,除了俺家的,也就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呀,虽然都有正当的营生干着,和哪路人来往,他们自己不说,村里人还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只是没人愿意说透。张大山走的是共产党的道,到他家里求医的,不仅仅是病人;崔二捣走的是黑白两道,用着谁了就找谁,挣的是钱;孙大手靠的是一手好手艺,谁也不在乎;刘七这个王八蛋卖的是祖宗,靠的是日本鬼子……
张大山、小红她爹、那个青年人,莫非是……俺叔是个混混,不关心政治,想到这儿,不再往下想了。但有一条俺叔还是很明白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你们走啥路都行啊。
小红爷俩再次来俺村,已是这年的秋天了。日本鬼子已在我们村南五里处的防城寺安上了炮楼。我们这儿紧贴济南直达徐州的要道,除了日本鬼子,这队伍,那队伍,来回过;这儿一阵枪响,那儿一阵炮轰,天下不太平了。小红爷俩在这兵荒马乱的季节里,还想着俺村,也真难为她爷俩了。俺叔问小红爷俩准备在村里说几天的书,要往张大山家里领,突然想到张大山死活不见人影很久了,媳妇在家不知哭昏了多少次,就往俺家领。小红大大方方看着俺叔的脸,说,俺来不是说书哩。俺叔就愣了,俺叔问,不是来说书?小红的脸就红了,一扭,说,你问俺爹吧。俺叔就更愣了,看着小红的爹,说,师,师傅,不,是大叔,您老人家……俺叔竟然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摁都摁不住呢,话也说不成句了,一脸的绯红。小红她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欲言又止,扭脸和闺女小红说,妮,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说吧,爹到前庄上要账去。说完,把俺叔和小红扔在这儿,独自走了。
没见到俺叔是死是活,俺家的房子又全没了,一间好房子也没了,什么都没了,俺三舅爷爷就让俺爷爷俺奶奶先住到俺三舅爷爷家里,改日再把俺爷爷俺奶奶送到城里俺二大爷那儿。俺爷爷叹了口气说,只能这样了。回俺三舅爷爷村上时,俺爷爷俺奶奶大泄劲,尤其是俺奶奶,劲泄得像散了身架骨似的,俺三舅爷爷的人架着她,她才能走,边走边落泪啊。俺爷爷和俺奶奶,是怎么回的俺三舅爷爷家,不知道。不过,俺爷爷俺奶奶一进俺三舅爷爷的村子,俺叔的那匹枣红马“咴咴”的叫声,一下子把俺爷爷俺奶奶的劲头提了起来。
俺爷爷俺奶奶知道,俺叔的那匹枣红马啊,俺叔给它刷洗身上时才这样不停地嘶叫。
接着,俺奶奶就听到巴尔塔萨叫着奔了过来,雨又狂下了起来。
没有电闪,没有雷鸣。
多少年之后,俺叔从将军的位置上退下来,写起了回忆录。出版后,家人每人送了一本。俺家人才解开了俺叔是怎么从粪窖里脱困这个谜,知道了俺叔是让小红她爹救了。
小红她爹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是以说书唱戏打掩护的地下交通员。张大山也是地下交通员。张大山的家是联络点之一。张大山的牺牲,是和小红的爹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被一粒流弹打穿了脑袋。小红她爹知道俺三舅爷爷和俺爹的亲戚关系。小红她爹能得到俺叔被困在粪窖的消息,是私拆了俺三舅爷爷给俺爹的信。小红她爹不但私拆了首长的信件,还冒着生命危险和受处分的风险,半夜里摸过来,抹断了三个汉奸的脖子,把俺叔救了。
令俺叔和俺家里人心碎的是,小红没和俺叔结成婚,就走了。是小红去部队找俺叔结婚的路上,夜里过砀山敌占区时,日本鬼子突然从炮楼里一梭子子弹打过来,要了她的命……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