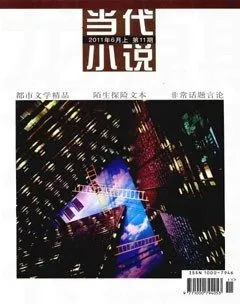樱桃
关于他的命运我了解得比他本人还多。
——茨威格《热带癫狂症患者》
我余下不多的力气,只能爬一点算一点。风在我身前身后吹响,掠过高高低低的树木,静静流淌的小溪,还有地上的小草和野花。那些草和花嗖嗖地在生长……但我不得不听凭自己像一台碾压机,从它们身上沉重地碾压而过。
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前,我还有力气回头看看那些草和花,它们倒伏在地,朝着我爬走的方向,暮色里能看到上面沾着我的血。现在,我已没有力气回头,甚至已经抬不起头了。我感到我的脖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所以现在,我的头跟我的两只脚没什么分别,它们只是被我拖着的零件。幸好我的胳膊还好用。我的脸擦在地面上,那些小草和野花还有荆棘,像密集的子弹纷纷射向我。
我想,我可能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我失血过多。密集的子弹像蜂群一样——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幕不停地在我脑海里重演,它不受我意识的支配。就像那颗陡然射入我体内的子弹,长驱直入,不由分说。
当樱桃出现在我眼前时,我不敢确定自己爬到了哪里。是尚在人间,还是已经到了地狱。一切都来不及分辨,我终于用完了余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可我不想死,我努力抬着不受意识支配的眼皮,但它们还是不由分说地落下来。像卷着的窗帘、或是戏台上的幕布,缓缓地垂下来。
“我是线人。”
这是我醒来之后对樱桃说的第一句话。
说完这句话后我感到了羞愧——因为这似乎暴露了我的求生欲,我怕自己被当成日本鬼子给杀死。
是的,我怕自己被当成日本鬼子,因为我穿着他们的军装。一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中国人,他的身份显而易见,根本无需猜测……的确,我是一名翻译。我们还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汉奸。
我不是汉奸。
樱桃把一块蓝花布在温水里浸湿,擦拭我伤口周围的污渍。我受伤的部位在左胸,据说离心脏很近,他们给我把子弹取出来时,我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说我命真大。大概是在几个小时前吧——我不敢说这个时间是否准确,因为我似乎一直徘徊在意识丧失的边缘——也许是一天之前,两天之前……我没有了时间及其它很多概念,只知道伤口很疼,只知道一把刀子曾经深入进去,在里面搅动,探寻,就像小时候母亲用缝衣针给我的手指头挑刺——那把刀挑出了扎在我左胸里的刺。
在此之前,他们——大概一共有两个人,为要不要给我取出子弹而陷入一场很凝重的犹疑不决之中。他们之所以犹疑,是因为不太相信我线人的身份。他们反复地求证两个问题:樱桃,他真的说自己是线人?他还说什么了?
后来我就昏过去了——我跟被称为樱桃的姑娘表明我的身份后,她找来了这两个犹疑不决的人,他们——重点是一个男的——为要不要给我取子弹而凝重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我本想帮樱桃说服他,无奈实在是又没有了力气。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被樱桃说服的,只知道我在昏迷中忽然感觉到一把刀插进了我的伤口。
当我醒来的时候,被称为樱桃的姑娘把一块蓝花布在温水里浸湿,正擦拭我伤口周围的污渍。我隐约想起他们给我取子弹时的窃窃私语,这让我相信我还活着。而我之所以活着,是因为这个叫樱桃的姑娘对我的信任。她坚持认为我没有撒谎,我是个线人。
那两个曾经为要不要给我取子弹而犹疑不决的人,再次很凝重地聚到屋子里来。他们把门窗关上,男的腰里别着枪,开始了对我的审问。他们包括樱桃一共有三个人,其关系从言语中不难判断——他们是一家人,樱桃,樱桃的哥哥和嫂子。樱桃的哥哥应该是这个村抗日组织里的人——他腰里别着一把土枪,这进一步说明他可能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我连说话都很吃力,因此,他们花很长时间才约略明白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在跟谁保持联络——当然,他们的表情泄露了内心里的将信将疑。他们有理由将信将疑,因为不论是我,还是他们,都永远无法得到我们希望中的确证——与我是线人这件事关涉重大的一个人,在刚刚过去的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无须赘述这个代号青蛙的人在胶东特委组织中的重要身份,那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成了一个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明的人。青蛙同志留给了世界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就在蜂群一样的弹阵里倒下了。而我只是他一个人的线人,我们保持着绝对秘密的单线联系——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死亡就等同于我的死亡。
可我活下来了。
我活下来的世界处在五月阳光之中,处在一棵鲜艳明媚的樱桃树之中,处在我和一个名叫樱桃的十八岁姑娘模糊的互相眷恋之中。那些日子里,很奇异地没有战斗发生,我日日躺在炕上,面对着窗外那棵鲜艳明媚的樱桃树。
在我躺着的那间厢房有一扇朝西的窗户,窗外生长着一棵很大的樱桃树,据樱桃所说,她是在樱桃树下发现我的——我赶在樱桃成熟的季节恰好到来,每天,樱桃都用胳膊挎着一个小竹篓,把那些红透的樱桃摘下来,一颗一颗喂到我的嘴里。她在屋外摘樱桃,或者喂鸡。没有战争发生的日子里,世界是那么安静,能听到鸡们咯咯叫着觅食的声音。鬼子的频繁扫荡断送了村里大部分鸡的生路,但樱桃很聪明,每当鬼子来了,她就把鸡藏到一个水道里。那条水道就在她家西墙外,流经樱桃树下。在离樱桃树两米的地方据说有一块大石板,水道在石板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出一个小暗道,是个没水的暗道,樱桃就把鸡藏在暗道里。
那段日子,伤口的重度感染使我陷入间歇性发烧。由于失血过多,还由于我在荆棘和沙石上爬行太久。另外,我成了一个无法说明自己的人,这让我无比焦虑。在发烧的时候我频频梦见一颗子弹拖着闪亮的尾羽插入我的左胸,状似一支锐利的箭,然后穿胸而过,留下一条明晃晃的弹道……有时我还梦见一枚钉子从我的左胸掉下来,留下一个空洞的钉眼,仿佛一个无可修补的破绽……
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尤其是那伤口陷入无可修补的境地——它源源不断地流出血和脓水。不用看,我也知道那些东西有多么肮脏。我希望由我自己,而非樱桃来处理那些肮脏的细菌滋生物,但我浑身无力,像一个死人。我只能闭上眼睛,怀着一颗羞耻之心,任由樱桃掀开被子,擦拭我伤口周围的污渍。樱桃用一个豁口的搪瓷盆洗那些给我擦拭的布。她的衣服上有很多补丁,却把一块崭新的蓝花布剪开,擦我身上那些肮脏的东西。
我就这样时睡时醒地度着日子,用混混沌沌的目光,看着窗外那棵樱桃树。那樱桃树在我因发烧而迷离的目光中,是一片不甚分明的氤氲之物,我甚至连一片绿色的叶子和一颗红色的樱桃都看不真切。
我看不真切的还有那个日日为我擦拭伤口、往我嘴里喂饭喂樱桃的姑娘,时不时很凝重地进来站立不语的她的哥哥。他在屋子里站立不语,是在担心我死去,或是担心我活下来,我不知道。但我能充分体味他的情感来路——我来的时候,穿着一身让他深恶痛绝的敌方军服。如今我是一个只能自己给自己说明而实际上根本无法说明的人。
在又一次相对清醒的时候,他向我询问关于那场战斗的事情。我很艰难地向他讲述了我所了解的大致经过。
那天下午,小谷永作是忽然决定去扫荡槐花洲的。给小谷永作当翻译的两年里,我给那位牺牲的青蛙同志共送出八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因此我们才有了诸如雷神庙大战等几次著名战斗。不必赘述身在敌营的两年里,我是如何取得了小谷永作的信任,那是一场关乎性命的智力冒险——倘若没有这种信任,我也绝不可能掌握至关重要的情报达到八次之多。
但是在那天下午之前,我没得到任何关于扫荡槐花洲的消息,或许——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临时决定。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你知道,鬼子们扫荡一个村子,有时候仅凭心血来潮就够了……就是这样,小谷永作忽然扫荡了槐花洲,我根本来不及把情报送出去。一切都是巧合——我认为一切都是巧合,甚至连小谷永作事先也并不知道青蛙同志正在槐花洲。
因此,青蛙同志牺牲了。槐花洲两百多口人全被杀死了。我也被杀死了。但是后来我醒过来了。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会醒过来。
……
无疑,这场讲述很混乱,很没有说服力。我能感觉到它们并不能让樱桃的哥哥信服。一个两百多口人全部死亡的村子里,最后神奇地爬出一个幸存者,而且这个幸存者是日军翻译。无论如何,这个翻译的所有陈词都是苍白的、可疑的。
但我只能如此。
而且我承认我撒了谎,我隐瞒了很多至关重要的环节。之所以这样,不仅仅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幸存有多么可疑,还因为,对那场战斗我也感到疑窦重生,很多谜团让我短时间内无法理清。我连自己都说明不了,还怎么说明其它事情……
我不知道人们如何看待坚贞——为他爱着的人,为他做着的事情,为他坚持着的信仰。于我而言,坚贞就意味着沉默,意味着挺住,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面对何种场面、受到何种委屈,都要把感情深深藏起,哪怕为此耗尽一生。这是青蛙同志多次对我的告诫。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的身份只存在于青蛙同志的档案之中。在其他人那里,我是一个没有真正身份的人,或者说,一个有着虚拟身份的人、一个有着伪身份的人。随你们怎么形容。我只是想说,当我站在小谷永作身边翻译他的话时,我承受的并不是我的同胞们给予我的蔑视和仇恨,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孤独。而我懂得,这孤独就是一种荣耀……
事实上,这些关于贞洁的表白,并不是我内心的独白,尽管过去的两年里,我无数次无数次地陷入这种独白之中。这些表白,我是说给樱桃听的。樱桃,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就像窗外那棵我看不真切的充满氤氲之美的樱桃树,给我温柔,给我抚慰,给我想象和活着的力气,同时也给了我——软弱。一种孩子扑到母亲怀抱里时不可避免的软弱。
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在这个五月里骤然而至的软弱,我不会丢失我对于保守秘密的坚贞……我对樱桃讲述了我的坚贞、我只能自己给予自己的苍白的说明、还讲述了那场蹊跷的战斗。
是的,我承认我对樱桃的哥哥隐瞒了真相,那场蹊跷的战斗真实经过是这样的——
在那场战斗来临之前,我送出了第九份秘密情报。情报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小谷永作决定扫荡荷花洲;二是,小谷永作刚刚运来一批崭新的枪支,藏在菊花镇中学里。
事情的蹊跷发生在战斗那天。按照我和青蛙同志的计划,我们第一步先安排荷花洲群众撤离,然后在那里布置火力,静待小谷永作;第二步,派基干团突袭菊花镇中学,夺走那批枪支,运到槐花洲一个秘密山洞里。
这个计划是我和青蛙同志反复推敲过的,我们分析了它的周密性和可行性:一,菊花镇是小谷永作驻军所在地,他带人扫荡荷花洲,菊花镇必定空虚,抢到这批枪支应该没有悬疑;二,菊花镇离槐花洲很近,只需半小时就能赶到,而且沿途布置了接应的兄弟,还有青蛙同志在槐花洲亲自坐镇,顺利将枪支运到也应该没有悬疑;三,荷花洲、槐花洲、菊花镇成犄角之势,三处可以互为接应;四,小谷永作赶到荷花洲后,迎接他的将是一个空村及埋伏在暗处的火力,我们人马和武器处于劣势,但地理优势明显,最不济的结果,无非就是干掉他们几十个人,然后迅速撤退。假如出现意外惊喜,消灭了小谷永作那当然更好……
可以说,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这场战斗是万无一失的。然而事情发生了骤变:就在我们离荷花洲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小谷永作忽然下令拐到一条岔路上去,那条路正通往槐花洲。这时我已来不及把新情报送出去……
过程就是这样。小谷永作用了大约两个时辰,把槐花洲变成了一座空村。全村两百多口人无一幸免,其中包括青蛙同志及二十多名基干团员。我依稀记得,当时,青蛙同志端着一把三八步枪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跳出来,马上他的胸膛就变成了蜂窝……
青蛙同志倒下之前很深地看了我一眼。说实话,我和青蛙同志之间有着你们无法理解的默契,我从他目光中看出,他要我好好活着,继续当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头一次感到了迷惘,因为他目光中另有深意,我并不能理解……
我没能如他期望的那样,把坚贞进行到底,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坚贞之人……他胸膛开花的时候,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于是我朝小谷永作举起枪……我左胸里的子弹是小谷永作射进去的,当我朝他举起枪,他先我两秒钟把子弹送入我的身体。
我倒在青蛙同志身边。我以为我必死无疑。实际上,跟他死在一起,可能正是我的愿望……但是我活下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槐花洲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夕阳的余晖正逐渐暗淡下去……
再没有比现在更让人绝望的了:没人能告诉我,小谷永作为什么忽然拐到了槐花洲,是仅凭心血来潮,还是其中另有蹊跷?只有小谷永作本人知道答案。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
在昏昏沉沉的日子里,我除了梦见那颗射向我的子弹,还频频想起青蛙同志临死前的目光,并越来越体味到,我当时并不能理解的意思,应该是一份让我查出真相的嘱托……
然而真是绝望,我只能在炕上躺着,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分别。我亲爱的樱桃,她读懂了我的绝望,在照料我的间隙,不停到外面打探来一些消息,隔三差五补充到我的思考中来。她告诉我:菊花镇中学那天发生的战斗跟槐花洲差不多,我们的精锐基干团全军覆没,更别提抢到哪怕一把枪支了。
两天后,樱桃又带给我另一个消息:原来,小谷永作提前把枪支偷偷转移到了菊花镇医院里。我们的人赶到以后扑了个空,这时候,埋伏在暗处的日军一阵枪火,半个小时,一切就结束了。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是如何震惊和慌乱……一切显然昭示着:这两场战斗都在小谷永作的计算之内。那么,小谷永作的计算从何而来?
只能有一种可能:小谷永作得到了我方的行动计划。显然,在青蛙同志的身边,也有一个如我一样的人,我们的身份都是线人……而且这个线人比之于我更为隐蔽,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明晃晃的前台上的角
色……
你们能体味到我的恐惧吗?我是潜伏在小谷永作身边的我方的线人,而那个人,是潜伏在青蛙同志身边的小谷永作的线人。但是,我和青蛙同志不知道这个线人的存在,这个线人和小谷永作却知道我的存在……在潜伏了两年之后,我终于暴露了,而我做好了坚贞到底的准备……
瞧,一切都如此明晰,像已切开的伤口或是揭开的阴谋,我却仍时时处在慌乱之中。我的逻辑思维在两个线人中间搅来绕去,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在时睡时醒的昏迷状态,我不断梦见那颗带着尾羽的子弹。在后来的一次,那颗带着尾羽的子弹忽然变得虚化起来——它的虚化是为了凸显本来处在虚化状态的背景——我看到那清晰起来的背景里,是小谷永作,他举着黑洞洞的枪口……
樱桃的哥哥还是时常来看我,他凝重地在屋子里踱步,腰里别着土枪。我藏身的屋子是樱桃家的厢房,自从我来到这里,樱桃白天黑夜都死死地锁住院门,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存在。樱桃的哥哥,这个对我充满疑问的人,每当他凝重地在厢房里站着,都让我感觉我的存在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破绽。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如何处置我这个可疑之人,因为我关涉一位特委同志的牺牲,而且,没人能证明那位特委同志就是我所说的青蛙同志……
在我因高烧而不甚明清的视线里,樱桃的哥哥充满压迫感——他即便不开口说话,也能充分传递对我的压迫。但我不能被他的压迫打垮,我得挺住。因为这个事实的真相一旦摆到现实的桌面上,我,这个从两百多具尸体里爬出来的日军翻译,就只能面对惟一的一种猜测:我提供了一份假情报,引诱青蛙同志去了槐花洲,然后一举消灭了我们的两支队伍……没人能给我证明。
还有,那样的话,我就失去了调查真相的所有时机……虽然我不知道在我活着的日子里,我,这样一个濒死之人,如何调查一件事情的真相,我还能不能活着看到那个真相。
但无论如何,我得挺住。没有任何荣耀可言,挺到最后一秒钟就意味着一切。哪怕没有转机……
我得说,我并不怕死,如今这种躺在炕上昏睡的局面,我认为还不如干脆利索地死去要痛快。但是,倘若是你,在过去的两年受尽自己人的误解,每分每秒都身陷不能分辩的孤独中,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愿意作为一个汉奸而死吗……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你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死法,只要是牺牲,你都甘愿,都没问题;但惟有作为一个汉奸而死,这是你不愿意的。无论如何,在你作为一个生命走到死亡的那一刻,都希望给自己一个说明,因为你的骨灰、甚至你的灵魂,还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上不停地转啊转……
我快死了。我可能终将无法自我说明。也许你们认为我是一个很小我的人,我应该大义凛然,不惜以汉奸的身份而死,那是因为你们没做过线人。那些作为线人的情绪,你们没有体察过……总之,这严峻的现实加重了我的病势,樱桃给我擦拭伤口的次数明显增多了,我已感觉到,伤口溃烂的面积正在逐渐扩展,肮脏的血水和脓物越来越多……
我得向你们说,我眷恋樱桃。这美好的姑娘让我想起一切可堪向往的美好事物——虽然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可堪向往的美好事物是如此少之又少。如今在我可供观望的现实世界里,只有窗外的樱桃树,及这个整日伺候我的樱桃了。
然而,几天以后,樱桃不见了,樱桃的嫂子来了。她接替樱桃,在那个豁了口子的瓷盆里,用温水洗蓝花布,给我擦拭伤口。你们知道吗,我产生一种失恋的感觉。我今年二十二岁,过去没有恋爱史。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也有一些日本姑娘喜欢我,她们中不乏像樱花一样美好的可爱姑娘。但我一直没有恋爱……我想,可能那是因为我在等着认识樱桃。可我认识她的年月是如此荒谬,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樱桃去了哪里,这个问题,樱桃的嫂子始终没给我答案。她说她也不知道樱桃去了哪里,只知道她用篓子带走了几只鸡。是的,现在,我连一只鸡的叫声也听不到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就由樱桃的嫂子照顾。每天她从一墙之隔的另一个院子来到我藏身的屋子,给我喂水和稀粥,给我擦拭伤口。我的病势越来越不乐观,所有对我知情的人——樱桃的哥哥和嫂子——他们一致认为我时日无多。也许正是因为我已时日无多,樱桃的哥哥越发凝重地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这个男人面对我的时候通常保持沉默态度,但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读到了对方一切的心理活动。我读到了他的诘问,而他读到了我的坚忍。我们都行进在对对方的考验里。我想,不久他也许最终会用那把枪指着我……
这样,我不清楚在半睡半醒之间,又过去了多少日子。有一天……我怎么形容那一天呢……樱桃的嫂子告诉我:樱桃死了。
我在神志不清中,听到樱桃的嫂子断断续续提到这样几个字眼:霄龙寺……养鸡……樱桃藏了一把枪,杀死一个人……都说那人是特委组织里的同志……樱桃让乱枪打死了……这个死妮子……
我再次昏睡过去。这次,在梦中我看到那颗带着尾羽的子弹射向了一棵樱桃树。树上挂着鲜艳明媚的樱桃,每颗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在现实里,这些日子以来,我从没这么清晰地看过樱桃,它们在我眼里只是一片氤氲的红。然后,我看到从樱桃树上流下很多红色的汁液,像血一样。
醒来以后我感到左胸的伤口一阵奇疼。多日来,我只能感到从那里流出的肮脏的血和脓水,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因为我的感觉细胞正在慢慢死亡。当我再次感觉到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感觉到的疼痛时,我知道,我即将真正地死去了。
可是我眷恋的樱桃,她竟然死了,现实是多么残酷……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日后你们会听到这样的消息(县志里也有可能如此记载):一个名叫樱桃的姑娘,潜伏到隐蔽在霄龙寺的特委组织里,枪杀了其中的一名同志;然后,霄龙寺里的其他同志,把她乱枪击毙了。
你们将只会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但你们不知道,樱桃为什么要枪杀那个人。或许……多半……基本差不多……她会被认为是潜伏进去的敌方破坏分子。倘若很多很多年后,你们有谁看到了我写的这个故事,才会明白,樱桃是枪杀了一个潜伏在特委里的奸细。也就是小谷永作的线人。
而我已来不及向世界说明。因为我即将死去。
在死去之前,趁这阵子我出奇的清醒,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先要告诉你们,霄龙寺正是秘密的特委所在地。你们如果有谁去过,就会同意我的说法:那是一个不起眼的院落,寺院香火已经败落,僧人多半不知去向,只有一名老僧看家护院……正因为此,为了方便组织隐蔽,特委租用了霄龙寺院,并在西偏殿养了鸡鸭兔子和蜜蜂作为掩护。
那个西偏殿,日后……你们会知道,特委在过去曾因破坏分子而遭到损伤,青蛙同志才不得已想了这样一个主意。在外人看来,那是一家生意不错的禽类养殖公司,而实际上,胶东很多党的机密文件和宣传品,都是夜深人静时分在满是鸡粪味的西偏殿印刷出来的。他们有时还会把从鬼子手里抢来的枪支,隐藏在西偏殿的蜂箱里。
你们猜想到什么了吗?是的——樱桃去了隐蔽的特委所在地,这个隐蔽的所在,是我透露给她的……我想,她应该是用篓子装着几只鸡,装成一个卖鸡的,然后,想办法在那里留了下来,成为一个给他们养鸡的人。为了隐蔽特委的真实身份,他们养了很多鸡鸭,总得有养它们的人……从那天开始,她成为一个潜伏的线人……说线人或许不那么恰当,应该说,一个调查者……但也似乎不太恰当……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她的身份,我对形容一个人的身份缺乏经验,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现在是茫茫的黑夜。我昏过去之前,听到樱桃的嫂子把铁锁挂到锁鼻上的声音,啪嗒,跟以前樱桃每次离开时候锁门的声音一样。然后,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樱桃嫂子走时留下的油灯光。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像垂死人的气息。
我就是那个垂死之人。现在,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当我最后一次醒来,我发现自己异常清醒。从这个条理清晰的结尾里你们能感觉到我的清醒。我知道,这是回光返照。我很高兴我为这个真实的故事留下一个清晰的结尾。实际上,我断断续续写这个故事已有多日,自从樱桃离开了我,我就已经开始写这个故事了。我想,或许那时候,不祥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笼罩了我。
现在我已写完故事的结尾。这几张参差不齐的纸,是我从墙上撕下来的,那是一张已经破损的年画,一幅《钟馗送福》图。原谅我,豹头环眼的赐福镇宅圣君,我只能在你庄严的后背上写这个故事,我找不到另外的纸。而且我只能躺在炕上,无法下地。自从我来到这里,目力所及,只有这间温馨简陋之室,及窗外那棵氤氲的樱桃树……此刻那棵樱桃树是如此清楚,即便是在夜里,我也看到了绿的叶子。而我没看到红的樱桃。它们都落了吧,五月已经过去……
最后,我将把这个故事卷起来,塞进一个玻璃瓶,然后藏到炕边的一个墙洞里。多日来,我就是把它藏在那里的。我会把那块砖小心地拿下来,再小心地塞回去。那里将像一个愈合后没留下任何疤痕的伤口。我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枕边,等着樱桃的哥哥来看呢,他一定会来找我问个明白的,或许会最终把枪指在我的头上……说实话,我不知道。虽然此刻我异常清醒。或许,是我做线人这两年养成的谨慎习惯在作怪——很多时候,其实,我认识到我是一个无比孤僻的人……也或许还是因为,我不认为樱桃的哥哥会相信我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没有人能证明……还有,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沉睡在地下。我们踩着的每一寸土地,下面都有故事。这也将是其中一个。
你们……我忽然觉得世界在慢慢黑下来,油灯呢,灯光呢……我知道,我就要死了。我说过,我要告诉你们很多事情,还有一件: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知道青蛙同志那么多事情。这其实没什么奇怪,因为他是我父亲。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