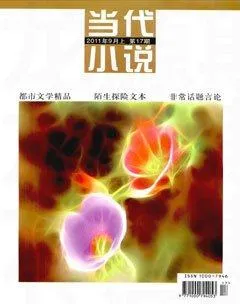阿拉法特头巾
1
却说农历乙酉年两头无春,民间俗称是寡妇年,有好些人家都抢着年前嫁女娶媳。年成犯怪,这年春上不仅一个雨点子也没下,而且天热得简直日了鬼,连蚊子也提前出洞咬人了。村里有个绰号“阴孔明”的半仙吴光三夜观天象,不觉顿脚道:“劫数难逃啊,奈何,奈何。”再问,却是怎么也不肯再透露半个字了。
果然春天还没挨完,村支书汪学家就患了感冒。感冒本属小疾,特别是在春季,不经意便会遭遇;但汪学家这次感冒来得有点蹊跷,感冒上了,便一直咳嗽不停,天天挂水也止不住。赤脚医生汪东林一开始也没当回事,说你这感冒属于热伤风啊,挂个三天两日的水也不见得济多大的事,起码都要挂一两个礼拜才有效果。可整整大半个月下来了,一天两瓶,挂得两只手都快成筛子了,咳嗽却是越挂越凶。东林也慌了神,不敢造次,苦着一张篾片脸瞅着汪学家,那目光却陡然间虚了,缓缓道:“支书啊,要不明天你到毗卢市医院去拍个片子看看噻?”
话一出口,汪学家的心立马咯噔了一下。这几年不断有人被这句诅咒一般的话送走,开发区金龙化工的车间主任金建明、做塑料粒子和打包带加工的汪子松,还有跑农药销售的陈锦波,去年居然轮到汪东林自己的老婆,在绿叶化工厂上班的冬梅,刚过了35岁生日,都是一样的咳嗽,一样的挂水,汪东林当时说的差不多也是这番话,片子一出来都是肺癌……
汪学家没有到毗卢市医院去拍什么片子,村里也有人宽他的心,说汪支书啊,你又没在化工厂上过一天半天的班,你担的什么心噻,不会的,真的不会噻!但会不会的也不知道由天上哪位菩萨说了算,只是每天惊风雨泣鬼神般的咳嗽让他一下子没了底气,他现在每天都捂着一个大大的口罩,并且开始注重早晚锻炼,每天都要绕村子转上这么一转,碰上人就说:练练脚力,有益健康。
一般情况下他都要拢到东林这儿歇歇脚,聊几句家常,心里头却还指望万一哪天汪东林会对他改口说是自己误诊就好了。诊所里老有几个闲人在那玩,有时候人手凑数的话他们就打一局“掼蛋”。“掼蛋”这一阵比较流行,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汪学家掼得不错,手握四张王,就是太上皇,把把都有炸,牌牌争上游,直掼得杀声震天,余音绕梁,任督二脉,一齐打通,竟连咳嗽也给忘了。
汪东林一向以诊所为家,立志把整个身心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事业中。但令他尴尬的是,去年老婆竟然也患肺癌去世了。该同志悲痛之余,一下子对自己的医术和光荣使命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更夸张的是现在再碰到有人来看病,该同志就紧张得虚汗直冒,稍微拿不准他就打招呼让人家赶紧去镇上或者毗卢市检查。但他在诊所为孤家寡人,回去也是寡人孤家一个,在哪反正都无所谓的,汪学家来陪他掼蛋算是瞌睡有人送枕头——巴结不得。
2
毛小羊是外地的媳妇,她是跟汪广长一起在广西传销时被骗过来的。毛小羊自称是少数民族,但她说的那个民族似乎不属于中华五十六个里面任意哪一家,再追问下去叽里咕噜的别人就更听不懂了。她平日里酷爱围一条黑白小方格的大头巾,也没人知道这究竟算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习俗;后来有人说在电视上看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拉法特也老爱裹这样一条头巾,那么照理毛小羊就应该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了,可怎么看似乎她跟人家阿拉法特先生也扯不上一丁点亲戚关系。
汪广长有个很吓唬人的外号叫“汪厂长”,做事说话脚天脚地的,把毛小羊忽悠过来后本想自己留下,但他老娘是个出了名的人精,他这边屁股刚一挪,那边已虎口拔牙,自作主张地把毛小羊转赠给了他打光棍的大哥汪广大,这叫“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汪厂长”不敢得罪巫婆一般的老娘,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从丈夫的位置乖乖沦为配角小叔子。毛小羊没有像报纸或电视上宣传的那样痛不欲生,更没寻死觅活的,安之若素地跟汪广大生活在了一起。
毛小羊很不适应这儿的环境,具体点说就是不适应这儿的空气,她抱怨说空气里的味道简直让人快喘不过气来,她很神秘地告诉人说她只有在接吻时才能暂时脱离这难闻的气味儿。前一句话大家基本可以理解,后一句有点令人匪夷所思。桑木桥村外边就是镇上的化工开发区,整个村子成年累月的都像弥漫在一个充满浓郁药水味的金钟罩里,桑木桥的人大多数都在化工厂打工,一个个皆已修炼得神功护体百毒不侵,说句笑话,要是突然间没味道,他们反而会茫然不知所措。
毛小羊的男人汪广大也在化工厂,身上那股又酸又臭的药水味儿,难闻死了,怎么洗也洗不掉,所以每次他一回来毛小羊都勒令他在外边把衣服全脱光才肯进门。她每天都用那条头巾紧紧地裹着自己的口鼻,饶是如此,还是觉得自己如溺水的人那样窒息。渐渐地,她发现这个村子里除了那个赤脚医生汪东林,其余的男人身上都有臭药水味儿。汪东林去年他老婆死了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很快形消骨立,瘦得仙风道骨起来,像个纸片似的,风一吹似乎都能吹走,身上氤氲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来苏水的味道,初闻上去虽有点闷骚,时间一久便觉着迷恋。
其实还有一个例外的,就是村里的傻子拾宝,拾宝用现在时髦的话讲,他是一个典型的“味道控”,自从村外有了化工厂后,傻子就在村里呆不住了,他整天游荡在那些味道暂时还没侵袭到的荒郊野外,身上不是沾一头花香就是惹满身草的气息,不然就是风的气味,傻子身上清新得能让人忍不住打一个喷嚏。傻子也分文傻和武傻,一般情况下文傻是属于死火山型的,平日里处于休眠状态,只有条件温度都达到饱和状态时,才会猛然喷发出来,而那一瞬间的爆发绝对属于“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拾宝介于文傻和武傻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石破天惊天才性的想法,他不知从哪个垃圾箱里寻摸来一个人家厂里扔掉的防毒面罩,每次回村都会煞有介事地戴在头上,像个外星人似的。
3
那天毛小羊来诊所找汪东林开药,讲自己在这块生活得很不适意,连气也快喘不过来了。汪东林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怪病,拿着笔犹在沉吟要不要打发她去精神病院。毛小羊迫不及待地一把捞住他的手,说医生啊,我知道的,我这病只有在接吻的时候才会稍微好一点,求求你快给我想想法子噻。汪东林有种受了愚弄的恼怒,笔一扔,揶揄道那你回去找你男人就是,到我这儿来捣什么乱呢。
“不行啊,医生,他身上有药味儿呢。”
“哪一个没味道,那你就去找一个好咯!”
毛小羊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找、你、啊……”
汪东林脑袋嗡的一下仿佛被某个暗器击个正着,朦胧中有个硕大无比的红唇裹挟着那条黑白小方格头巾像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一下子压了上来。
自从跟汪东林有过一次接吻之后,这个女人简直疯狂地迷恋上这个小小的天堂一样的诊所,稍一得隙就会偷偷钻进来,逮着没人的机会就跟汪东林腻在一块儿接吻。汪东林开始还有点不敢乱来,毕竟都是同一个庄上的,而且自己还是汪广大的叔辈,万一传出去这个“扒灰公公”的名声可是既不好听又不实惠的。但毛小羊不管这些,她说谁想说说去,我不找你,我命都没了哦。
毛小羊跟汪东林接吻归接吻,但她是个很纯粹的人,旁的什么想法也不会有。汪东林老婆死了已近一年,他是个很正常的男人,跟她亲过几次就不满足这“口舌之争”了,老是想着要把自己的手弄到她的衣裳里去,要跟她再做点什么。她不肯,她很天真地问汪东林:“我们不做那事又不会死,但你不跟我接吻我肯定会死掉的哦!”面对这个玻璃一样看到五脏六腑的人儿,汪东林简直欲哭无泪。
这天晚上汪东林又努力了一下,毛小羊还是紧紧地裹着那条怪里怪气的头巾,一张嘴却凑过来咬得死死的。汪东林来脾气了,说我是医生,我什么没见过,你怕我干什么呢?毛小羊怕医生,又怕他发脾气,便松开了手。汪东林刚扯开她的头巾,突然外边“轰隆”一声巨响,那手顿时呆住了。半天,汪东林才强笑道:“没事没事,狗日的化工厂又在吓唬人呢!”桑木桥村外边就是镇上的化工开发区,那里的化工厂经常发生一些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大炮仗;有时候是“哐”的一声,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被炸到,因为早在爆炸之前,那些仪表和阀门都会有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光。有没有事前毫无征兆的爆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像不多,如果有,那就不叫化工厂,那叫地下爆竹厂。
4
这一次化工厂爆炸的破坏范围不算大,据说只是绿叶农药化工厂内一个新当班的工人违反操作程序,在加原料时省略了一些步骤,结果导致反应釜里热量急遽升高,蒸汽一下子冲开了盖子,发出那一下惊天动地的巨响。虽然在生产上并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那一响直接把毛小羊和汪东林之间的好事打发掉了;然而最大的不幸还不止于此,毛小羊的男人汪广大当时正在宏达化工厂里的废液池边打扫卫生,那一声让他猛地一惊,一失足,滑进了池子里。虽然只是废液,但毒性也是很大的,等找人把废液抽干,打捞上来时人已变成了一个绿毛妖怪,瞠目结舌的,早一命呜呼。
化工开发区到桑木桥村已有好几个年头,但真正发生死人的事故还是破天荒头一次。第二天一早,汪学家便咳嗽着召集几个在家的村委以及部分村民代表到汪东林的诊所里商议善后事宜。桑木桥村以前也有办公室的,会议室、图书室、计生服务室、农机服务中心什么的一大摊子拢共有二十多间房屋呢,后来化工开发区搬来后,地价直线上升,汪学家便索性把村办公室的地皮卖了,直接挪到开发区龙头企业宏达化工有限公司会议室办公去了。双方当时也假马日鬼地签订了一份租赁协议,其实一分钱也没掏。宏达当然也是求之不得,把这座土地庙修到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来,不指望拿妖捉怪,最起码烧香磕头也方便点啊。
但这次出事的正是这个宏达。汪学家本以为凭借自己跟宏老大的交情,这事应该问题不会太大,不就赔几个钱的事吗。但昨晚打电话给他们董事长万仁奎沟通的时候,对方却一口咬定爆炸的明明是绿叶,跟宏达压根连半点关系也没得,让他去找绿叶老总要赔偿。绿叶老总汪学明跟汪学家是本家兄弟,他苦着脸道:“二哥,我们厂里爆炸管他宏达什么鸟事,两家离得那么远呢,就譬如我们村东头老张家放了个炮竹,村西头老李家的羊发了羊癫疯流产,老李家能找老张家去索赔接种的钱吗,哪儿跟哪儿,挨得上吗?!”你看看,本来只是一件异常简单的事故,结果越搞越纠结了。
私下里两家老总偷偷派代表给汪学家递话,原来宏达跟绿叶之所以这样互相推诿,主要还是因为省里马上要下来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这次据说是常务副省长带的队,发了狠的,说一旦查到不合格的立即勒令停业整顿,严重的甚至关门走人。出于人道主义赔点钱大家都不在乎,但事故的责任却是谁也不敢揽的,都怕在这关键时刻弄出点什么纰漏。两家一通诉苦,而后也不忘给汪学家抛一个媚眼,说拜托支书帮忙多做点工作,有情后补。要放在以前,汪学家肯定马上心领神会;无奈汪学家现在变得不能跟化工沾半点关系,虽然口鼻都被大口罩捂着,但还是咳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一口回绝了厂方私了的提议,坚决要求按工伤处理,赔偿丧葬费、抚恤金,还有要开追悼会。“桑木桥人的命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值钱了?”汪学家很重地跺了一下脚,像是为自己的话总结性地打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5
桑木桥的人都清楚汪学家跟化工开发区的老板们合穿的是一条裤子,以为这次他不定又会怎样忽悠大家呢。后来发现他似乎认真上了,毛主席也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个字!这边一较真,果然就挖出不少猛料来。说是化工开发区居然有一大半以上企业都未申领环保许可证,排污超标现象也是司空见惯,像这次惹祸的两家前年甚至还因为排污被重罚过。大伙儿马上群情激奋,说怪不得近几年我们这儿得癌症的人这么多呢,老祖宗几千年下来也没听说过有这些倒头毛病,现在却每年都弄上几个绝症。
几批人马呼呼啦啦集中到东林诊所,纷纷捋袖奋臂,叫嚷着要与这些丧良心的化工企业讨个说法。治保委员丁四儿去年化工厂排污把他鱼塘里的鱼呛死了,虽然在汪学家的调解下当时就赔了部分钱,但余下的一直拖着没给,丁四儿认为自己的损失被严重低估了,那些白花花的鱼啊,谁看着都心疼,不提经济方面,就是精神损失费还不知多少呢;毛矮子,村里的会计,两只手都会打算盘的主,他儿子前几年上了个不入流的大学,毛矮子谋划着想趁此机会把儿子弄进宏达混个会计啊或是文秘的什么位置;而这边“汪厂长”的经天纬地大业也暂时搁置一旁,不晓得从哪个传销窝点窜了回来,找了一个草台乐队班子,雇来一帮闲人披麻戴孝地抬着汪广大的尸体咋咋呼呼要去堵厂门。
汪学家不肯坐视他们盲目蛮干,他年轻时搞过几天基干民兵集训,时刻牢记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纪律条令,他把这些虾兵蟹将分了工,大致分了几个战斗小组:一组以计生委员白麻子带领毛小羊等汪家直系女性亲属为代表的号丧组,她们是丧者最直接的亲人,负责出面接触两个企业的干部,期间可辅以围追堵截哭骂叫掐等任意非常规性武器;一组以“汪厂长”为代表的汪氏族人封堵园区入口,封门堵路,严禁村里人到园区上班,直接从源头处掐掉园区的生产线;另安排村里各个支委分别带队,计有围观望风组、机动组、后勤保障组,以及一个参谋组。参谋组以汪学家自己,加汪东林、毛矮子以及那个半仙吴光三为主。
毛小羊裹着阿拉法特头巾走在队伍最前面,傻子拾宝戴着那个头盔一样的防毒面罩;汪东林身着白大褂,半仙吴光三手摇羽毛扇,“汪厂长”率一帮人抬棺压阵,加上“依依呀呀”呐喊助威的一帮哭丧队,显得既诡异又极具震撼力,一下子就把场面压住了。化工厂那边冲出来几十个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人手一根黑色橡胶棒,煞有介事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但见此阵势,已有怯阵之意,虽也咋咋呼呼,奈何嘴巴喊得凶,鸡毛不打钟。
汪学家很是得意,微微一笑,刚欲开口,猛然间对面厂区里杀出一股黑烟,冲着他们劈头盖脸席卷而来,汪学家避让不及,一阵呛咳,咳嗽蜂涌而上,铺天盖地的,竟咳得弯下腰来。毛小羊眼尖,不觉失声嚷嚷道:“东林,不好咯,支书咳血咧!”汪学家皱皱眉头,不满地瞪了她一眼,直起身,摇摇手,待要发话,蓦然眼前一黑,人已栽倒在地……
6
汪学家一儿一女,皆已出息成人,闻讯忙从外地匆匆飞了回来。汪学家出师未捷,但头脑还算清醒,他说你们都别忙乎了,我的病我心里有数,也不用到医院去受罪了,我想趁还能走得动做几件事:第一是乘一趟飞机,上天看看;第二去杭州玩一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曾经去过就不去了,我想去杭州看看西湖、看看精忠报国岳飞的坟;另外就是一定要打赢眼下这场仗,人争气,佛争香,土地老儿争炮仗,事关桑木桥子孙后代,只许赢不许输。他把汪东林唤去,拱拱手道,东林老弟,眼下这副担子交给谁我暂时都不会放心,整个桑木桥惟你跟拾宝两个是最没心机的,我走了你代替我的位置,代表我去跟化工厂交涉。汪东林一时手足无措,但瞧汪学家那副临床托孤的悲壮,也只好慌乱地点点头。
汪学家这一走,群龙无首,虽留有“你办事,我放心”的嘱托,无奈桑木桥各路好汉已是人心涣散、各怀鬼胎。汪东林的诊所现在俨然成了桑木桥临时村委会,汪东林暂代主政,按照他的想法,光是封门堵路也非解决问题的正道,也不是赔两个钱的问题,还是要再去省城一趟联系他的同学,力争把化工厂违规的一些证据搞到手,而后就可以去环保局或政府部门上访,争取主动权;至于别的人还继续去厂门口耗着,有枣没枣在树下抡根竿子试试。
孰料第二天,“汪厂长”突然没了影踪,据说宏达跟绿叶两家一共给了他二十万,他揣着这笔钱扬长而去,汪广大的尸体半夜不知被谁用车接走,一家伙拉到三里簖火葬场烧了,连骨灰也没让留;丁四儿眼见着化工厂有暗示,说去年的赔偿可以重启谈判之门,便想取出经来唐僧得,惹出祸来行者当,自己本也就一个摇旗呐喊的角色,何必充老大,不如归去;毛矮子的儿子已到宏达化验室上班,顶的就是汪东林老婆的位置,毛矮子马上嚷嚷道他的疝气这两天又犯了,苦着脸,一只手老是不自觉地就往裤裆里揣,仿佛那儿藏着个什么宝贝似的;剩了个可怜的汪东林孤家寡人一个在诊所发呆。当晚有人秘密来访,二话不说,甩下一摞人民币,外加一沓照片,照片上竟然是他跟毛小羊的艳照。来人说,事已摆平,你也消停点,识相的话我负责把你这临时大总统转正……
汪东林走马上任,他不忘旧情,把毛小羊弄到诊所帮忙。俩人再在一起时,毛小羊感觉面前这个男人变得陌生,满身味道又酸又涩,刺鼻难闻,说:“不行,你身上有味。”汪东林没有废话,一把扯去她紧裹在头上的头巾,不由分说就吻了过去。毛小羊一阵晕眩,糊里糊涂搅在一起。说也奇怪,从此毛小羊不再戴着那条阿拉法特头巾,她变得跟所有桑木桥的女人一样素面朝天。
桑木桥恢复了正常,该上班的上班,该打杂的打杂,那股将汪学家熏倒的黑烟继续在排放,其中夹杂着坏鸡蛋一样的恶臭,但没人在乎,也没人抱怨。一天下夜班,一个人的头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他开始没在意,一会儿又被砸了一下,这时他才跟牛顿被苹果砸中后发明牛顿定律一样,发现砸他头的居然是一只树上栖息的麻雀。那些麻雀被化工厂排出的气体熏晕过去,像树上已经成熟的果实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掉落下来。他的心一下子振奋起来,四下里搜寻“果实”。有人加入捡拾的队伍,来的人越来越多,拿着手电、打着火把,大家像过节一样兴奋,一边捡,一边忍不住叫起来:“好家伙,这么多,这么多!”毛小羊也来了,她一眼看到傻子拾宝,忙招呼道:“拾宝、拾宝,快点来哦!”傻子拾宝没理她,撒开腿疯跑,边跑边用变了调的嗓门叫道:“没得命哦,快跑啊,化工厂放毒了!”声音又尖又细,四处回荡着傻子瘆人的叫喊。毛小羊骂道:“傻子,发什呢神经噻!”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