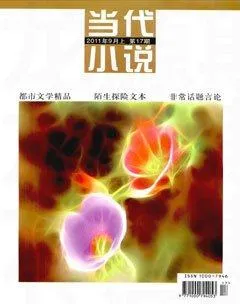清醒祭
1
南方的夏夜总是突如其来,出去的时候还尚存余温的街道这会儿竟被泼了冷冰冰的黑墨,死气沉沉的。星星累赘似的挂在夜空,时不时“嗖”地滑落一颗,划得苏小裸心烦。苏小裸从厕所隔间的浴室走出,扒在宿舍走廊的护栏上,凝视着被他看了四年的街道、路灯、梧桐。在这四年的最后一晚,同样的街道、路灯、梧桐却倏然丧失了前一晚的勃勃活力,瞬间老去了。死的。是的。苏小裸惊讶地发现,他看了四年的这些东西竟然是死的、没有生命的,这使他失望透顶。他几乎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于是他用架在护栏上的双臂夹紧了自己的头,像敲木鱼样的一下下敲打自己。酒精变成了一颗钢针扎进了他的后脑,“啊”——他窝心地一声粗吼,低头,搭在肩膀上的白毛巾顺势滑下,刚好从马葫芦的巨大裂缝处钻了进去。苏小裸也不去理它,他异常清醒的思维开始游离、幻想,他想象着这条毛巾在地下道里面的历程,或许它会永久地留在母校的地下,也算是他和黄岛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的证明。这块毛巾,其实是他室友黄岛的呢!
此刻,趴在床上的黄岛像一只硕大的青蛙,他早已鼾声四起,有一只大臭蚊子正在黄岛的蚊帐外徘徊着找寻突破口。看着看着,苏小裸的心窝泛起了涟漪。可他知道,为时已晚。他想起了刚才毕业酒会散场时于浩对他说的话,于浩说,苏小裸,全班男生就你没喝醉,你这人太有城府了,他们都说你不可交,让人看不透。苏小裸辩解说,谁说我没喝醉?我喝醉了,我从没喝过这么多,我头都疼死了。于浩说,那你怎么没哭?你看你走路都不晃的。四年啦!我们在一起四年了啊,怎么你都没点留恋的吗?我——,苏小裸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看了看周围刚从包车里下来的同学们,确实都在哭。他们有的坐在马路牙子上无声地啜泣,有的相拥着把对方的脊背拍得咚咚响,有的一个人扶着梧桐树干不停地呕吐。他们的脸都变成了一面面反射月光的镜子,苏小裸能清晰地看到镜面上的棱角、污痕。苏小裸变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除了于浩鄙夷地扔下那么一句外,再没人理他。他孤零零地站在一群会哭的男人中间,他们的哭声就像交响乐,而他,确乎是个不懂音乐的人。
苏小裸确实喝多了,可他就是哭不出来也吐不出来,即便用食指去抠咽喉,也只是干呕了几声,眼睛有点泛酸,倒是山崩地裂的头疼折磨得他异常清醒。辅导员拍着苏小裸的肩膀对大家说,互相搀扶着上楼去吧,已经很晚了,明天离校,都注意安全。苏小裸二话没说,拉着晃悠悠的黄岛往楼梯口奔去。被失去重心的黄岛拉扯着,他们俩像身负重伤的战士,不停地撞着走廊的两侧,把一条一百米长的走廊足足走长了两倍。
现在,所有的寝室都静了下来。只有苏小裸扒在走廊的护栏上,他开始像于浩质问他一样的质问自己:为什么自己就是哭不出来呢?他确信自己已经醉了,他的沉重的脑袋正在被凌迟,眼中的景物也开始忽远忽近,然而听觉和思维却异常清醒,似乎比平时还要清醒,清醒得凉丝丝的。他开始厌恶起自己的清醒,清醒使人失去很多东西,譬如勇气。他告诫自己应该糊涂起来,在这四年的最后一晚,他必须糊涂起来,因为他喝醉了,喝醉的人不该这样孤零零地在走廊里度过。于是,他大着胆子爬上了黄岛的床。他想去给他脱衣服,想并排和他躺一会儿。因为过了今晚,他们可能再没机会见面了。黄岛猛地一翻身,把苏小裸的手掌压在了他后背下,压得苏小裸手背生疼,压得他心怦怦直跳。苏小裸停止了动作,就任他穿着衣服去睡吧。他坐在他的床上,定睛看着和他共处一室四年的黄岛。他似乎看到他的额头确乎多了四条抬头纹,四年丝毫没有改变他如婴儿一样的面容,却平添了一股成熟英气和一点狡黠的气质。他们实在太熟了,熟得很多时候苏小裸看黄岛就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熟得他发觉黄岛在他面前就是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狡黠的气质,这在别的同学面前是从未有过的。黄岛的狡黠就像一只狐狸,嗖嗖地跑开来。无比清醒的苏小裸的大脑变成了电影播放器,一幕一幕,像暴雨,瞬间纷至沓来。
2
夜愈发静了。有一只黑猫站在走廊的护栏上向门里张望,它看到苏小裸凝重的神情,竟窜到梧桐树上逃掉了,梧桐发出稀稀落落的声音。这时又剩下苏小裸一个人了。他看着床上的黄岛,又看了看另两张空床上以及地上他和黄岛各自的一堆行李,他们垂头丧气地躺在那。眼前的一切,没法让苏小裸糊糊涂涂地过完今夜。苏小裸开始回忆起许多个第一次。他想自己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如此关注、如此依赖黄岛的呢?难道是第一次见面吗?于是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倏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他鬼使神差地抓起一个背包,退回到走廊上,重温起了第一次走进这间宿舍的那一幕。
苏小裸清楚地记得四年前父母陪伴他走进这间屋子时,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贴在门上的四个名字,他们按顺序是这样排列的:苏律、黄岛、宋科学、王占晖。后来王占晖因为转专业,搬离了这间宿舍;宋科学因为交了女朋友,便借口跟学校打申请,租房去了校外;这间屋子里便只剩下了他和黄岛,那时他还不叫苏小裸,他叫苏律。苏小裸依稀记得他推门走进这间宿舍时首先看到的就是门左侧黄岛的床下一个撅着屁股在拾掇东西的南方妇女,然后就是直挺挺站在妇女身边的黄岛。黄岛俨然一副南方农村高中生的模样,他一米七的个头,面容清秀,明显搭配不当的衣着平添加倍了他淳朴的气息,淳朴得很自然让人想到一个词——可怜。当时,黄岛冲他笑了笑,示意了一下友好,接着便开始跟身旁的妇女喋喋不休。他们用苏小裸完全听不懂的南方方言在争执一些在苏小裸看来完全没有争执必要的问题,苏小裸从他们的动作中判断他们是在为一些物品的摆放位置这类的生活琐碎各执一词。看得出,黄岛是一个无论任何事情都很有主见、不喜欢被人束缚的男孩,甚至,在他身上,苏小裸嗅到一些似乎是初中生才该有的叛逆。
后来,黄岛不无狡辩地对苏小裸说,那不叫叛逆。黄岛说他只是想坚持属于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彼此熟识后,黄岛在向苏小裸喋喋不休地述说自己的母亲是如何捆绑着他、像对待孩子一样管辖着他的时候说道:我只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外这两年,我已经习惯了按自己的喜好生存,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喜欢随性,而不是整天被别人唠叨,唠叨着天冷了就一定得多穿衣服,唠叨着每次吃饭都拼命给自己夹菜。黄岛说,一家人还这样子,我真是不习惯,这也是我为什么放长假都不爱回家的原因。后来,当黄岛把他的“一家人”理论应用到苏小裸身上也如是要求苏小裸的时候,苏小裸竟然倍感光荣。可对于黄岛因此而很少回家的想法,苏小裸是有些难以理解的。作为北方人的苏小裸,每年只能回家一次,所以他断不能理解黄岛的想法。他对黄岛说,你就是被惯坏了,你就是太叛逆了,你二十岁的人了还青春期,我鄙视你!黄岛笑嘻嘻地辩解说,大哥,这不叫叛逆好啵?就算是叛逆,那也是“高级叛逆”。不过我确实知道自己是被惯坏了,惯出个性来了。在家我妈惯着我,出来后碰到你惯着我。对了裸裸,给我交五十元话费去哈!我身上没零钱了。苏小裸说,我要是你老爹,早就KO你了,敢跟长辈使横。说着,苏小裸一个拳头砸在了铁床扶栏上,疼得他哎呦哎呦叫了半天。黄岛早已扬长而去。
自然,苏小裸是喜欢这样的聊天的。他知道黄岛也是喜欢这样的聊天的。只是他不知道黄岛的喜欢究竟搀杂了多少习惯成自然的成分,苏小裸会时不时地拿一个得失的天平来衡量他和黄岛。黄岛会不会在利用他的感情解决一些生活难题?比如手机话费或者洗衣服?他究竟给黄岛交了多少次话费、洗了多少次衣服了呢?恐怕他自己也记不清。
以前黄岛不回家的长假,苏小裸一般是这样度过的:白天陪黄岛去逛街买衣服,偶尔买完衣服两人便去街心公园和清水湖吹吹风。说买衣服倒是真的,说起逛街就有些牵强了,因为那根本不叫逛街。黄岛不喜欢逛街,但他需要有人陪他去买衣服。他一般走进一家店,用双眼快速将所有衣服秒杀一遍,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走进店面,在门口一晃,黄岛就可判断出有没有他想要的衣服。黄岛往往是心里想好了衣服的样子,直接去找;或者之前看好了某家店某个位置的某件衣服,直接去试穿。他偶尔征询一下苏小裸的意见,有时候根本不问,穿着合适就直接买下走人。所以,每次跟黄岛逛街,苏小裸都有些失落:打发时间的目的没起到,从郊区跑到闹市融入闹市的目的没达到,几十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里,逛街就结束了。偶尔在清水湖聊天倒是苏小裸心里盼望已久的,按理说每天黏在一起的两人话是早就说干了的。可是一到清水湖,黄岛就变成了一只兴奋的大雁,他跃上湖边的长椅,迎着晚风张开双臂,兴奋得像一个诗人。这个时候,在苏小裸眼中,黄岛变成了一个骑士。他时而跳上跳下,时而顺着台阶下到湖面上。总之,黄岛是兴奋的。兴奋的黄岛有时会说出一些苏小裸不知道的事情。黄岛给他讲自己的小时候,黄岛似乎能确信他讲的都是对苏小裸来说很感冒的事情。苏小裸听着黄岛以前的事情,就像听说书的在讲故事。那些与苏小裸所经历的北方城市生活大相径庭的南方乡村开始像雨后的春笋在苏小裸的心底冒尖,像沁人的甘露一滴滴淋在苏小裸的每一寸汗毛上。然后苏小裸就有些怅然若失,他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了解黄岛,这在每次黄岛的高中同学来看黄岛,两个人坐在走廊里叼着小烟的方言谈吐中便可见端倪。那时,一向惜字如金也从来不见他抽烟的黄岛变成了另一个黄岛——一个从并不遥远的附近一所乡村高中走来的黄岛。苏小裸断定,他和黄岛之间有着近乎二十年的空白。这空白,时常让苏小裸心生恐慌。
苏小裸恐慌的心却在黄岛的另一重叙述中变得陌生起来。黄岛说,我在写一部玄幻巨著,暂取名《狩妖》。苏小裸没多问,一下子沉默了下来。一个屋子里住着,苏小裸竟然不知道黄岛在写小说。沉默没有把气氛变成冰山,甚至顺理成章、不显任何尴尬。他们吹着晚风,各自若有所思。突然,黄岛问,苏律,你不高兴了?没有,我挺高兴。苏小裸说。骗谁呀!你的情绪总是直观地写在脸上……黄岛也不多问,默默地低下了头。
3
小长假的晚上一般是这么度过的。一份螺蛳、几两豆干、几瓶啤酒,打包买回后摆在宿舍的某张桌子上。这似乎早已约定俗成。有一次,黄岛喝醉了。那次黄岛一边喝酒一边忙着给人发短信,苏小裸不知道他是给谁发。苏小裸的心里跟长了刺一般。他一股脑,灌了一瓶进肚。停下手里的短信,黄岛没说什么。他就拿起酒瓶,“女人都是贱货!不搭理她就反倒这么勾引你!”黄岛抹了一把嘴,“对不起兄弟了!”之后“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整瓶酒瞬间消失。那晚对苏小裸来说也不知是尽兴还是悲伤,总之他越喝越起劲,更像是在赌一口气,赌黄岛一味地发短信不理他的那口气。他觉得黄岛实在太没劲了。黄岛渐渐觉察到了苏小裸的情绪变化,他放下手机,启了瓶白酒。半杯白酒下肚,黄岛的脸红成了灯笼。他的那句来得莫名其妙的“女人就是贱货!”却反复在苏小裸的脑海里盘旋。在黄岛说完那句话之后,他就开始醉了。他突然用双手捂着脸、一咧嘴埋着头哭了起来。苏小裸赶紧去抚摩着他的肩。他第一次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在自己面前哭,并且哭得呜呜响。黄岛的鼻涕蹭了苏小裸一身。他站起来要撒尿,说着就冲苏小裸的脸盆过去了,苏小裸惊得手足无措,不知该不该拉住他。他想伸手,但内心里似乎又默许或期待着他的举动,那更像是崇拜偶像所获得的回赠,只是真要接受这样的回赠多少让苏小裸厌恶起自己。苏小裸的期待似乎夹杂着更多的好奇,好奇将要发生的一切。思忖继续的同时,黄岛早已泄洪完毕。泄完洪的黄岛竟像个地痞无赖半提着裤子转头冲向苏小裸,像个傻子般一边玩弄着自己的阴茎一边淫笑。苏小裸顿时慌张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表情来面对眼前的一切。他心里应该是和悲伤相反的情绪,但是是高兴吗?他高兴看着黄岛在他面前衣不蔽体吗?又好像不是,否则他何以主动制止了黄岛的行为呢?他协助黄岛提上了裤子,拉他坐了下来。苏小裸没理会他,他去倒脸盆,然后拿拖布。等苏小裸收拾完回来时,黄岛早又吐了一地,屋子里充斥着腐臭的味道。在这腐臭的味道冲击下,苏小裸却异常清醒。苏小裸百思不得其解,人真的会醉成这么个样子吗?吐完后的黄岛似乎也清醒了一些,他骂了苏小裸一句,苏律,我操你妈!苏小裸说,黄岛你不能这么骂我!黄岛推了他一把,怎么地?我还想打你呢!说着他“啪”一个巴掌扇在了苏小裸的脸上。苏小裸刚要回敬他,却听他低着头的嘴里反复念叨着:苏律,哥们。不,兄弟,你害苦我了,你害苦我了,你害苦我了……伴随着这一声声的“你害苦我了”的是黄岛接二连三的几个巴掌,只是越来越轻,更像是对先前那一记重击的抚慰。最后,黄岛开始了第二拨的哭泣。苏小裸收回了举起的手,眼角也湿了一行。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究竟是一种释放还是自责,他是看不得黄岛伤心得这个样子吗?应该是,他不确定。
那天夜里的情况是这样的:睡到半夜后,黄岛突然高喊一声把苏小裸惊醒了。惊醒时,苏小裸发现黄岛已经爬上了他的床。那时黄岛早已醒酒了,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要求和苏小裸睡一张床,并且在这个时候苏小裸才有了除了苏律以外的这个新名字。黄岛是这么叫的,“裸裸、裸裸”我要跟你睡!他满脸邪笑,直挺挺地压在了苏小裸的身边。苏律问他为什么叫他“裸裸”。黄岛说因为你睡觉喜欢打赤膊。苏律看了一眼黄岛,整洁的睡衣穿在他身上很有暴发户的味道。黄岛说,你可是咱们学院的大诗人,应该有个笔名。咱就叫“裸裸”了,多个性。后来苏律想了想,还是改成了小裸,苏小裸。
那晚的苏小裸体会到了失眠的痛苦。他从小到大从没跟别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过。而且宿舍的床实在是不够宽绰,很多时候为了不挤到黄岛,他都得侧着身。黄岛的鼻息像小热风机一下下地从背后呼在他的耳根、脖子上,他的身体器官就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变化,那一晚,痛苦与焦灼、等待与期盼袭击了苏小裸的魂,他盯着电风扇,久久难以入睡。梦境就史无前例地奔放着,他梦见黄岛骑摩托车载着自己去郊游,他从背后抱着黄岛的腰,幸福得在梦里笑了起来。
那晚的情景竟然和现在尤为相似,不同的是,现在的苏小裸是和黄岛躺在拼起的两张床上。苏小裸时不时地翻身看看黄岛。黄岛早已鼾声如雷。
4
苏小裸开始仇恨起自己的清醒来。清醒,一切就都得按常理出牌。那么今晚,就将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夜晚了。可是今晚是自己能预见的时光里与黄岛共处一室的最后一晚了,难道不该发生点什么吗?“应该发生点什么”这个想法顿时让苏小裸既焦灼又羞愧。他不知道一直以来黄岛是怎么看待他苏小裸的。当然,在他面前,更多时候黄岛都是乐观并乐于开玩笑的。黄岛会故意把两个人的寝室制造出和其他任何寝室没有差别的氛围,很热闹,让苏小裸不觉得他们的寝室里少了两个人。苏小裸突然觉得黄岛的这种氛围制造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回避,回避触及一些令两个人都尴尬的话题。苏小裸想,黄岛可能在骨子里是厌恶他的,因此在这四年的最后一晚他故意让自己鼾声如雷,过了今晚,他就熬到头了吧?这样想的时候,苏小裸冒出个想法:要以毕业为界限,主动割断和黄岛的一切联系。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机会吗?毕业了,以后换的新的联系方式不告诉他,QQ也删了他,那样自己就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了。苏小裸想,假使黄岛主动联系他呢?那就随他去,如果黄岛主动联系他那就随他去,否则自己绝不会主动再和黄岛有任何瓜葛。那么,黄岛真的会在毕业后主动联系自己吗?比如费尽心机地搞到他最新的联系方式,或者强硬地对他吼:你胆敢不和老子联系,老子灭了你!苏小裸是期待这样的怒吼的。他突然很想爬到黄岛的床上,把那次挨他的几个巴掌一股脑回敬给他。
思维在天马行空一番过后,破晓前的疲惫把苏小裸推进了梦乡。他醒来时,黄岛递给他一瓶绿茶。黄岛说,喝了它,醒酒的。你昨晚也肯定喝多了。苏小裸心中有一丝小小的感动。他定睛看着黄岛许久。黄岛说,唉!打住!得,今天不适合煽情。今天就是普通的一天,过了今天,一切依旧。黄岛转身又笑嘻嘻地说,我昨晚真是喝多了……你扶我上的床?嗯。苏小裸说,废话,不是老子你还想是哪个美女怎么的?美女进不来咱宿舍。苏小裸边说边觉得自己的话实在有点无聊,也有点虚伪了,这跟没话找话差不多。难道他害怕尴尬在今天产生吗?他不知道。黄岛翻了个白眼,狐狸般地谄笑道,那你没把我怎么地吧?苏小裸扬了扬头,看似若无其事地说,嘁!你一个男的,我能把你怎么的?没兴趣,再说你离帅哥实在有点差距。哈哈,那就好那就好。黄岛像放了很大的心似的。
苏小裸的思维总是会慢半拍。在说完这几句的数秒后,他突然为黄岛刚才的话有点来气。再过数秒,他又有点小喜悦。他想,莫不是这小子渴望和我苏小裸发生点什么吗?哈哈!总之,他竟越想越高兴。推开门,他看到太阳仍旧高高地悬在半空中,和每天并没什么不同。
苏小裸若有所失。他想,假使很多年后,他还会记得自己曾经住过的寝室、在墙上刻过的字吗?自己的母校、母校上空的太阳会知道他来过这里吗?或许,很多年后,连他自己都会忘了自己曾经来过,都会忘了这个和自己同一个屋檐下住了四年的兄弟。
苏小裸说,黄岛你几点钟走?黄岛说,反正我东西都搬差不多了,我又是在本市工作,天黑之前背包走人不耽误明天早上上班就行。苏小裸说那咱们一起走吧!黄岛说,好的。
氤氲中黄昏终于来了,黄岛并没有等苏小裸。于浩几个人要送苏小裸。苏小裸对黄岛说,一起聚聚再走吧?黄岛说不了,和于浩没那么熟。我单位临时有点事要早点回去。毕竟我试用期,身不由己啊!
就这样黄岛走了。
苏小裸在宿舍楼底下捧着于浩买的半个西瓜,拉着行李箱打算往火车站赶的时候,接到了黄岛的电话。他没来得及接,黄岛就挂断了。苏小裸迫不及待地跟于浩告别,然后拉着行李箱、捧着西瓜、像个要抓住时间的乘客一路小跑着往公交车站赶去。他一边赶一边拨通了黄岛的手机。他停了停,竟有些紧张。
你刚才打电话有事?
噢,现在没了。嘿嘿。我忘记带硬币了,想让你送来一个。不过,我刚才碰见了同学要了一个。
噢。苏小裸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没挂电话。
黄岛也没挂断电话。
他们隔着电话听着彼此并不匀称的呼吸。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这一次尤为漫长。
许久,黄岛说,裸裸,我会想你的。以后你要常来找我玩,你知道的,我——很多生活上的事——我都弄得——乱七八糟的。
苏小裸意识到自己在流泪了。在他光滑的脸颊上,他的两行泪就像泉水涌了出来,一滴推搡着一滴,迫不及待地争抢着,连成了两条线。他第一次懂得悲伤。悲伤得彻底。此刻他哭着,却并没喝醉。他像重新活了一遭一样,清醒地流着泪,它们像他多年前刚知道悲伤这件事的时候一样地流出,纯净地滑落。
多年前?那是什么时候呢?四年前吗?绝不是。因为四年前的这个时候,他,他和他的兄弟黄岛,正在南北两个方向、在各自糊里糊涂的生活中天真地沉睡。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