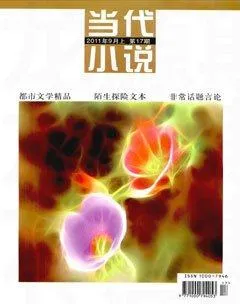颜色
2005年的圣诞节,刚好周末,我一个人无聊,下了班就踏上了去洪城的汽车,打算找母校读研的同学一起过节。谁知班车到洪城的时候,却怎么也等不到去师大的公汽。我招了招手,拦了辆的士,却转念对师傅说,去鄱阳湖宾馆吧!似乎那之前我就预演过一个和路玉一起过节的场景。我想,鄱阳湖宾馆门口一定种着一株圣诞树。
他们说,榕树是洪城的市树,因此在洪城随处可见。这我倒是知道的。我在洪城读书的那几年,无论是公园、学校还是街头巷尾,厚重的榕树棉花似的裹着整个城市。可是,他们后来说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说,古时在洪城这块地儿,有女儿的人家,每家门前都会种着一株榕树,待女儿到了出嫁年龄,有哪家小伙子对女子有意,就会拿把斧头在其家门前的榕树上砍上一斧头,就代表这家女儿已有相亲的对象了。古时女儿藏于闺中,所以男子自然只能凭借榕树的长势来确定是否要砍上这么一斧头。这话音刚落,我便成了他们旅途中打趣的对象。他们说,才子王进,你看我们这些人里,就你的斧头还没落呢!怎么样,什么时候砍树啊?另一个人补充道,砍树就来我们洪城砍,洪城的树最好看。
那是2005年的初春。我们一行二十人正坐在去往庐山的旅行车上,我被他们的话弄得满脸绯红。我们是经邮政报副刊版的编辑点将,从全国各地邮政系统遴选到洪城参加邮政报的通讯员会议的,我因刚毕业进入汀县邮政局不久便在邮政报副刊上发表了像模像样的两篇散文而有幸成为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入选者。副刊版的胡老师给我打电话时说,今年的会议就在你们省的洪城,我倒要见见你这小伙子。那是我第一次跟一些同行业里的文学工作者齐聚一堂,也是我第一次住进鄱阳湖宾馆这样的五星级宾馆,更是我生平第一次为自己感到高兴。我是真的由衷的开心,我想都是因为遇见了路玉。
鄱阳湖宾馆装潢得富丽堂皇又不失江南韵致。转过旋转门,正对着一湾池塘,呈现在池塘中间的是一个立体的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江南小院,流水拍打着假山、荷叶,发出稀稀落落的声响。小院中间偏右的水面上,一片巨大的荷叶拖着一架白色的钢琴慢慢转动着。一位身着绿色纱裙的江南女子正坐在巨大的荷叶上敲击着钢琴键。以此为中心,宾馆大厅左侧是会议室和电梯及洗手间,右侧靠门是一个贵宾餐厅,靠里大约一个百平米的长方形空间则被设计成一处自助餐厅。我就是在那里用晚餐时碰到的路玉。确切地说,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叫路玉。她只是鄱阳湖自助餐的服务员。她缓缓地走过来,问我和同桌的河南郑州邮政局的毕铁要喝点什么饮料。她说是餐厅免费提供的。毕铁说他要啤酒,而我要了杯可乐。我就是在这时注意到她的,注意到她的同时,我的心紧了一下。她长得太美了。
我想,如果你没见过路玉,你绝不会知道什么样的皮肤叫做白;如果你没见过路玉,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样的气质叫做纯。不,我用纯来说她似乎不礼貌,她应该比我长几岁。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眨巴着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她的眼睛流露出一个词:清高。你完全没法想象,一个身为服务员、并明显是个称职而优秀的服务员,她是热情、细致而周到的。可是她的眸子确乎是清高的,就如旁边池塘里开着的那朵荷花。她身材高挑,一米七的个头,圆脸,容貌酷似SHE组合里的S。她言语流露出的是成熟的善言而非稚嫩的活泼,骨子里散发着的是庄重的气场而非轻佻的浊气。最后,我注意到了她那和每个服务员都一样的把头发束缚起来的白手帕:轮到她,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呢!她真好看。
旁边的池塘中央,那个身着绿纱裙的女子弹起了班得瑞的《童年》。我为自己瞬时萌发的爱意羞愧得失了神。这时,毕铁问我,王进,你什么时候到的邮政。我说去年才进来,试用期都还没过。他看我显然对工作的问题不感兴趣,就问我有女朋友没。我说没有。
说到这个话题,又难免牵扯到工作、牵扯到汀县。我不喜欢汀县,我想离开那。可是,这似乎没必要对这个我刚认识一天的毕铁说,虽然我们住在同一间房。
服务员有条不紊地走了过来,她慢慢地把我们的杯子和餐巾纸的位置摆好,然后慢慢离去。她弯腰递给我饮料的时候,我与她有过大约三秒钟的对视。我想我的眸子里一定写满了爱意以及渴念,而她,什么都没有。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的是,我是一位顾客。那时我真后悔我身上没带只笔,或许我可以趁毕铁不注意的空当在餐巾纸上写几个字然后适时递给她。在她转身走后,我又后悔我为什么没进行一项非常俗气的举动,比如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在她递给我饮料的同时故意把那杯饮料碰洒。想必,我感觉自己实在很幼稚。
毕铁很善谈,符合邮政搞营销的人的所有特质。而且,他之于我的亲切点在于,他是北方人。他说着和我姐夫一样纯正的河南普通话。
毕铁说,这种事得看缘分。
我问毕铁,你相信缘分?
毕铁说当然。接着他给我讲起了他与他妻子相识的故事。
他从部队转业到郑州进了邮政后,便自己租了房子单住。有一次,大概是他在陪完客户独自一人回到家后,闲着无聊,就想起了给昔日的战友打个电话。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话把他和他的爱人拴到了一起。他当时把号码拨错了,138的手机按成了139,接电话的是个女人。那次简短的通话过后,他鬼使神差地保存了这个139的号码,接着就是时不时地发条短信、打个电话。说到这里,毕铁显然激动了。他说老弟,你都不知道,我当时上班每天都会路过楼底下的那个幼儿园,也总能碰到幼儿园里的一位女老师。在和那个139的手机号聊过几次后,我就总感觉这个号码应该就是幼儿园里的那个老师。你都想不到,事情还真就这么神奇!
毕铁的故事听得我腾云驾雾了。世间真有这等奇事?感觉像在看电影。而且是一个烂俗片子。
对于我来讲,那个夜晚过得实在有些漫长了。晚饭过后,毕铁就在省公司一位员工的陪同下和一位江苏邮政以及一位广东邮政的员工去逛绳经塔了。我一个人留在了宾馆。这也就给了我很大一个回忆那个女服务员的空间。对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仔仔细细地回味了一遍,然后决定下楼找她。我想我绝对是疯了。这个时候,我更应该到邮政报那几位编辑老师的房间去拜访下、套套近乎,然而那个女服务员的音容笑貌源源不断地流淌在空气里,就像泉眼,不停地被我开发着。我即便小心翼翼地开发,都害怕遗落或弄错了细节。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地下到楼下大厅去转悠。可我并没发现她。自助餐厅黑着灯,想必已经下班了。那个弹钢琴的女孩仍旧在巨大的荷叶上端坐着,远远地,她的手指敲在琴键上,就像下雨。我走进电梯,启动,又有些不甘心,于是又下来。电梯就这样在十七楼和一楼间往返了几次,电梯门合合关关,好在只我一个人。隔着玻璃,洪城的夜灯一会儿在快速上升的电梯下变成密密麻麻的萤火虫,一会儿又在快速下降的电梯里变成一片光影的湖。我下垂、再下垂、成了垂直砸在湖面上的石子,不停地将湖水泛起涟漪。我的心随着快速升降的电梯七上八下。渐渐地我迷恋上了心脏飞翔的感觉,并且在晕乎乎中第一次有贴近感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它真美。直到毕铁他们逛完街回来,我都还像个游客一样地用眼睛打量着这座我呆了四年的城市,同时,用心体会着我自己构筑的和那个服务员之间的隐秘情思。
第二天,我们便踏上了去庐山采风的行程。他们在旅行车里嚷嚷着要给我找棵树砍的时候,我脑子里充盈着那个女服务员的影子,我想她就是我的树。偶尔,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脑子有病了。这怎么可能?人家是五星级宾馆的服务员,见过的大款多了去了,我算什么?甚至我们这一行人又都算什么?她眼里流露出的清高告诉我,这不是一个甘于庸庸碌碌过小日子的俗气女孩。当然我想我自己也不是。可我转念又想,她不过就是个服务员,她文凭肯定不高,说白了就是一个打工的,我又哪里配不上她呢?这么想的时候,我又很有信心。最终,去庐山采风的行程,这个女服务员一直在脑子里陪伴着我,使我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对于他们来说,庐山美景美不胜收,我们去的当日,缭绕的薄雾更是增添了庐山的秀美。可是对于我,我的那棵树早就枝繁叶茂地遮住了庐山所有吸引我的地方。
我们的培训只有两天,也就是说今晚,我将有惟一的一次和女服务员交谈的机会。这样想的时候,脑子里就像有根救命的草。毕铁和他老婆相识的那个故事开始反复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结果,当天返回洪城的那晚,省公司的老总要宴请我们。这实在让人恼火。
这顿宴请把我逼上绝路了。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宴请必定不会在一楼的自助餐厅,也就是说我将错过最后一次和女服务员见面的机会。二来我确实不胜酒力,也很反感这样的应酬。这样的宴请,完全等于是浪费了满桌子菜,然后不停地举杯。我甚至可以想象,作为来自省内的惟一一个参会者,我的角色是多么的尴尬。果不其然,我被安排在了省公司老总的身旁,扮演了三种角色:首先,我要跟其他所有与会者一样对邮政报的领导频频举杯;其次,作为惟一一个本省的参会者,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尤其得对跟省公司老总的初次见面表示荣幸;再次,我也算东道主了,我同时得对前来洪城参会的各地同行表示欢迎。好在我占了年纪小的优势,没有哪个人想不怀好意地灌醉我,所以我喝得并不多。反倒是毕铁,喝醉了。他吐了几次后,被我和另两位同行搀着回了房间。
毕铁在房里折腾了老半天。他先是在他的床和我的床上来来回回换了几次,接着又莫名其妙地去搬窗口的茶几,嘴里还嘟囔着这厕所为什么没水。后来他又跑去洗手间找电视遥控器。总之,他的思路完全错乱且十分亢奋。我拦了几次,发现弄不动他,干脆随他去。我被他搅得心神不宁,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洪城的夜景。
在我离开洪城近半年后,我开始发现洪城的夜是这么的美,空气里都充盈着暧昧。我想我是在汀县呆久了。
想到汀县,难免就会想起茹蓝。茹蓝比我大七岁,我工作后惟一遇到的一位不同于其他同事的人。确切地说是我把她挤走的。
我第一天走进汀县邮政局的时候,茹蓝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收发文件。领导对我的突然到来有些措手不及。原因是并没接到市局分配了新人下来的通知。茹蓝看我的第一眼是惊喜的,我想更多的是惊,可能喜也就停留了几秒,接着她沉默了。茹蓝花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把收发文件、文件归档、人事档案等一切事宜教授完毕后,就被派到孝桥镇邮政局做前台工作了。没办法,她是名劳务工,仅读完了中专。之前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单身的姑娘,因为她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直到她走那天,我才知道她已经嫁人生子了,她男人在深圳打工。那天我很想请茹蓝吃顿饭,我用手机给她发了好几条短信后,她还是拒绝了我的邀请。她说她要回去带小孩,恐怕没时间。我也不知是怎么了,那天我心里的愧疚感史无前例地奔放着。是我的到来把茹蓝给挤走了的想法尤其强烈。我竟然骑着车子在茹蓝出没的那个小区门口转了很久,我很渴望见她一面。鬼知道真见到后我要说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就好比我现在总是想见那个女服务员一样,真见了面,我能说出什么样的话呢?不知道。我想我可能仅仅是想看看她,仅仅如此。那时我就突然有种想去送送茹蓝的想法。我为自己的那个想法感到吃惊。
茹蓝走得静悄悄的。我甚至都没想到三个月以后我会再次见到她。
入冬的一个周末,我们局一行人去孝桥镇买柑橘作为发放给职工的一项福利。我们汀县邮政局每年都有这么一件事情。孝桥的柑橘是全国有名的。孝桥的街道两旁全是橘树,漫山遍野的金灿灿映得人睁不开眼睛。没有哪家是要专门开商店的,买橘子直接开车到孝桥的百姓家。说白了,孝桥家家户户种橘子。令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一行人挑来挑去竟然挑到了茹蓝婆婆家。茹蓝帮我们装车,因她在我们汀县邮政局工作,又是她曾经的直接领导、现在我的领导陈主任亲自带队,所以茹蓝给了我们很多方便。我的心随着装箱的橘子滚来滚去的。我真想抽空对茹蓝说几句话,可是没有任何机会。
满载而归的车子从茹蓝婆婆家驶出来的时候,我看着车子过了小河。我借口招呼师傅下了车,跑向了河边。茹蓝站在河对岸,我鼓足了勇气,我想我或许仅仅是想对她说句对不起。否则还会有什么呢?茹蓝看了看我,转身骑车回去了。我一个人立在岸边很久。
上车后,我给茹蓝发了条短信。那之前我也发过表示愧疚的短信,可我没直接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发完后,我赶紧把手机关掉了。
很多事都很奇怪,比如茹蓝,她是那么希望自己能一直呆在汀县局的办公室工作,因为我知道汀县比孝桥要好不止几倍,而跟洪城比,汀县我是看不上眼、不爱留下的。然而我却留下了,茹蓝走了。
我怎么会在此时想到茹蓝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大概因为我很少碰见这种气场的女人,就跟这个女服务员一样。我文思泉涌,抽了一张房间茶几上的客人留言纸,洋洋洒洒地写了五十几行诗,我要送给女服务员。
毕铁开始鼾声如雷的时候,隔壁来自江苏扬州的刘兄叫我去楼下坐坐,说明天要散了,再和胡老师聊聊。我欣喜若狂。
我又见到了女服务员。她给我们每人点了饮料后转身消失在池塘的另一侧,我的眼珠子也跟着去了池塘的另一侧。
老弟,我就知道你一直对那个弹琴的女孩感兴趣吧!刘兄一把揽过了我的脖子。
实在令我不知所措。
难道找到自己的树了?另一位长辈说,小李,帮忙给王进搞定这件事。
大家跟着附和。
没有,没有,你们别乱说。
语毕,大家开始谈论邮政报副刊版的改革问题和文学方面的问题。我一向不喜欢谈文学,因为那实在没什么好谈的。我满脑子都在想该怎么和服务员套套近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跟她套近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跟她说我喜欢你吗。或许是,对,是的,我想我一定是要对她说我喜欢你这句话。可是,我想喜欢这个词可能会让对方感觉我很稚嫩,她会暗笑我的愚吧?那么,是爱吗?我爱你?仅一面之缘,又不该这般浓烈吧!于是,我招呼她要了第二杯可乐,接着第三杯,我喝了很多杯都没说出口,更没逮住机会给她塞那首我完全不记得什么内容的情诗。
他们问,王进,你怎么这么爱喝可乐?这东西喝多了可不好,你还是少喝点碳酸饮料。
我心不在焉地点着头,这里的好喝。
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啊?我实在喝不下去了。
这时,胡老师说,王进,帮我去叫杯柠檬水吧!
我的劲头一下来了。
似乎服务员有要收班的意思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没看到那个服务员,我说我去洗手间。接着我绕到了那池塘的另一面,找了很久,也没见她。我的心跌落谷底了。
当晚,我整晚都在失眠。
次日,到了我们马上分道扬镳的时刻了。
毕铁说,老弟,相识一场,这支笔给你留作纪念吧!说着,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看似很昂贵的钢笔。我有什么理由收人家的东西呢?寒暄之词说得好听,难道还有机会再见面吗?礼尚往来,我又实在拿不出什么回赠他。而且,自从有电脑后,我确实很少用笔了。就连昨晚给女服务员写诗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笔才能把字写得好看了。所以,我回绝了毕铁。
省公司负责接待的大哥对我说,小王,一会儿我要去火车站送毕铁,还要去机场送胡老师他们,和你的时间刚好冲突,我就不去汽车站送你了,反正是本省的、离得又近。以后常来哈!
我连声说好,没必要送,自己人。接着我提着包自己下了楼。
我真不想那么快走出鄱阳湖宾馆的门啊!
我在厅堂里徘徊了很久,做了些很幼稚很农民的事儿,比如掏出手机到处拍照。
我真想再见见女服务员,可是,我连她叫什么都还不知道。
这时,我看见领班从我身前擦过,叫了声:路玉,你去把贵宾室打扫一下。接着我看到了她,她从假山后面闪出身来,走向了大门左侧的贵宾室。
原来她叫路玉,多好听的名字。
我跟上了她,在贵宾室门口停住了。
她出来后,见我立在门口,问了句:先生,有什么事吗?
我低着头,后来抬起头,看了她半分钟,我确信我的眼睛里晶莹剔透的,否则她也不会继续问:发生了什么事吗?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我——,我笨拙地说了句,我要走了!
她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呵”了一声,略略弯了腰说,欢迎下次光临!
我的身体不知怎么,就这样缓缓地走出鄱阳湖酒店的大门。等我到了汽车站,我才猛地发现:天呐!诗歌还在我兜里放着呢!
后来,我郁闷了很久。我在网上,不止一次地跟当初接待我们的省公司的大哥开玩笑说,我要去你们洪城砍树了。他说,好啊!欢迎。我就乐了。
没想到事情过去大半年,我脑子里仍然时不时地浮现出路玉那张雪白的脸和那双纯净中透着清高的眸子。在鄱阳湖宾馆的那两天,我的生活是有颜色的:白色,绿色?总之是一种很养眼的颜色。
随着的士越来越接近鄱阳湖宾馆,我心跳得就越厉害。快到鄱阳湖宾馆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是路玉不在就好了。这个想法很奇怪,要是路玉不在的话,那么我是来干什么的呢?我不知道。我是喜欢洪城才来的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我就是为了给自己大半年的患得患失地等待画上一个句号吧!我发现我是寂寞的,并且一直很害怕这种寂寞。这个想法令我胆战心惊。
我穿着臃肿的羽绒服,斜挎着运动包,包里空空的,除了那封装着情诗的信封。我捂着信封,就像捂着我的命似的。我想无论迎宾还是服务员,肯定都没见过我这号顾客。我问吧台,我想吃自kswdirmBleFJOX4dFtd50g==助餐。吧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的自助餐都是团体预订的时候才有,平时是没有的。不好意思。我问,那路玉在吗?吧台的接待员愣了一下说,她是自助餐的服务员,没有自助餐的时候她一般是不在的。我问,您能告诉我路玉的电话吗?我想找她有点事。接待员问,先生,请问您是路玉的……?
是啊!我是路玉的什么呢?充其量,我还是她的一个顾客,我仅是她的一个顾客。
我心灰意冷地走出了宾馆的大门。我要在这住一晚吗?
我看着宾馆侧门口写着的节日期间最低优惠至499元的房价打了个寒颤,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洪城下雪了,这让我再次想起路玉雪白的皮肤。想到路玉的时候我很开心,住在鄱阳湖宾馆的那两天我很开心,现在的我同样很开心。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雪边下边化。鄱阳湖酒店门口的圣诞树白绿相间,很是好看,配上地面泥泞的黑色,更加好看了。西方节日的盛行把洪城变成童话里的世界了,真的很美。
我心里凉丝丝的。突然觉得这趟就不该来。
我抖抖身上的雪,想着还是连夜回汀县算了吧!汀县和汀县的工作虽然很普通,但好像也挺好的。
责任编辑: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