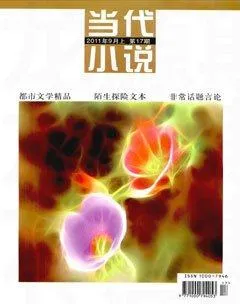冬天不觉得冷
一
零点,我去三八路的永和豆浆吃饭。我是那种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人。一到深夜肚子里必须进点东西。我所在的这座小城,24小时营业的餐馆,除了永和豆浆,就是火车站附近的小店,那边太脏我不爱去。
我哈着手推开永和豆浆的玻璃门,门上覆着层热气,我在上面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将屋里的一些场景透露到大街上。这个点来吃饭的人不多,店里的灯没有全开,光线有些暗。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羽绒服,好像是艾格牌的,她正低着头小口小口地喝豆浆,旁边坐着一个健壮的男人,正在给她说什么,她不时笑笑。男人的嘴角沾着点东西,她拿起餐巾纸轻轻地给他拭去,那男人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点餐的时候,收银员问了我好几声,我也没想起吃什么。后来我点了份煮的牛肉沙河粉。找个角落坐下后,点上一支烟,才想起小票还没交给服务员。我没像以往高声招呼服务员过来,而是走过去把小票递给她,然后指指自己坐的位置。等餐的时间很漫长,我低头翻看桌子上永和豆浆的企业文化报,报纸上有几处油渍,估计是有人边吃边看落到上面的。我只拣上面的标题看,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让我很难看进去。我开始摆弄面前的筷子,先把两根筷子对齐,在桌子上蹾蹾,然后再把它们放倒在桌子上摆齐。如此不知道摆弄了多少回,饭才上来。碗里冒出的热气,把眼镜糊住了。我没摘眼镜,视线模糊着吃。才吃几口,就觉得饱了。
平静中突然发出“咣当”一声,我赶忙把眼镜摘下,用餐巾纸擦拭,戴上后扫扫屋里,她和那个男人刚才坐的位置空了,桌上只剩下两只白色的碗。我愣了一下,然后起身出了永和豆浆。
外面很冷,身上的热气如同一下被偷跑了,身子不由自主地绷紧。一辆车后面的尾灯就像一对红红的眼睛,正慢慢驶去。我钻进车里,把车启动开,没等预热就挂档起步。开到一个十字路口,正亮红灯,那辆车没有停,急驰而过。我把车刹住,突然意识到往这边正是回家的相反方向。我赶忙掉转车头。心里问自己,这是怎么了?
大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昏暗,仿佛就要没电了。我清晰地听到车轮胎和马路摩擦发出呜呜的声音。车灯像推土机一样在路面上推过。我打开车内音响,是一个男人喑哑的声音。这车自买了以后,这张CD塞进去就再也没拿出来。他唱道: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
地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无边的思量
相信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
车开yQwAfyfSoHFzLYvT0G2f2Q==到德兴路,我发现路边有个裹着厚厚冬装脚步匆匆的行人。我想靠边停下问问他要去何处,我可以把他送过去。这个念头刚刚闪过,车已经跑出老远。拐过弯,远远地就看见我家小区门口亮着的那盏灯,这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是行走在今夜?昨夜?还是前夜?
小区里的楼在黑暗里,像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偶尔有扇窗户露出微暗的灯光。我想,那是主人刚刚下班?还是有心事睡不着?
车库的遥控电动门吱呀呀地打开,我在车里却愣住神。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喑哑的嗓子已经哑住,我才清醒。把车停好,机械地拿包,摸索着打开单元的防盗门,一股温暖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在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中,楼道里的灯亮了。开开房门,把客厅里所有的灯打开,屋子里的一切是那么凌乱,突然让我说不出来的厌倦。脱掉夹着寒气的外套,随手挂在椅子上,那上面已经挂了好几件衣服。沏一杯浓茶,然后打开电脑。电脑键盘上都是烟灰,低头吹吹,烟灰飞到桌子上就像沙滩上的几处鸟爪痕。我点上烟,这时候发现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刚想倒到垃圾桶里,却发现那里面更满。用脚往下踩踩,腾出个空儿再倒进去。登陆QQ,上面有几个发亮的动物像,我给他们逐一说了句,你好,吃了么?结果是没有一个回话的。我只好上几个门户网站看看有什么新闻。看了一会儿,找出没有写完的小说,没敲几个字,脑子就空荡荡的,只好关上电脑。
沙发上凌乱不堪,皱皱巴巴的沙发罩上有一床没叠的被子和一个瘪了的枕头。我躺到上面,开始摆弄手机。不自觉拨了一个号,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女人冷冰冰的声音,紧跟着是一串英语。我说,水费卡放在哪儿了?电话回复我的却是嘟嘟的声音。挂了电话,我用遥控器打开电视,一个台一个台地过,不是肥皂剧,就是电视购物的广告。
我突然想起阳台上的花,赶忙接水浇花。那花已经低头耷脑,也不知道能不能缓过来。阳台上还有一堆袜子,放在那儿估计已经很久,我又把袜子泡到盆里,才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抽了会儿烟,喝了会儿茶。看看手机已经凌晨三点,却没有丝毫的睡意。
电视里一对男女正在吹嘘某种品牌的表多么好,多么好。产自瑞士,镶满天然钻石,但是价格有些可疑。屁股底下有些硌得慌,拿出来是本书,翻翻,看了几行,就随手扔向茶几,可是没扔好,书掉到沙发底下。我俯下身,摸了半天,没找到书,却摸出一把沾满灰尘的红色梳子,上面还沾着一根长长的头发。我小心翼翼地把梳子和那根长发放进电视柜下面很少打开过的抽屉里。
这时候洗手间的下水道传来一阵刺耳的哗哗排水声。不早了,我提醒自己该休息了。我站起身推开卧室的门,打开灯,灯很亮,让我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双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我叹口气,把灯关上,然后回到客厅躺在沙发上。
二
醒的时候也不知道几点。根据我的起居习惯判断,应该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外面时不时有行人和车辆经过的声音。还有微小的声音,似乎是旧报纸或者方便袋在风里翻舞。窗帘没有拉严,阳光透过缝隙洒在屋里和我的脸上,让我又有些迷糊。浑身疼,估计是长久一个姿势造成的。我仰面朝天地躺着,揉揉肿胀的眼睛,盯着天花板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只黄豆粒大小的蜘蛛趴在网里一动不动。前年的时候,它和米粒般大小。它和我一样属于夜里欢,白天没精神的主儿。看情况它比我还要懒些。我的视线挪到天花板上挂着的圆形节能灯上,灯的周边黑乎乎的,好像有三年多没清扫过了。过去每逢春节家里都会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我又闭上眼睛,昨天晚上梦里的一些片段跳跃出来,说来奇怪,这三年多我总是做同样的梦。这让我有些恐惧睡眠。我曾试图用酒精改善我的睡眠质量,尽管我酒精过敏。可是除了增加痒得恨不得挠破的红色斑块,以及天旋地转和呕吐,睡着后那个梦还是无法摆脱。后来我只能放弃摆脱它,每天凌晨闭上眼睛以后,我在一边看着它发生一遍,才沉沉睡去。
尽管不想起来,但我还是强迫自己起来,要不很快天就会黑了。我伸胳膊蹬腿闹腾了几下,掀起被子从沙发上爬起来。
刷牙的时候,在镜子里我发现额头上的皱纹比原来清晰。昨天好像是两条深的,一条浅浅的。今天那条浅的,也非常明显。我用手试图抚平,松开手后,皱纹似乎更深了。我抹掉满嘴的牙膏沫,无奈地冲镜子里的那个开始衰老的男人笑笑。镜子下方的置物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我顺手拿起一瓶看了看,是瓶女士润肤霜,保质期已经过了一年,瓶身有些脏。我打开水龙头,反复地清洗,直至光洁。然后我小心放回原处。
几滴晶莹剔透的水珠挂在瓶身上,我望着愣了会儿神。
我打开饮水机的开关,水稍微热点,就沏了杯蜂蜜水。一起来喝杯蜂蜜水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之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是因为有个人曾对我说过,人经过一夜睡眠后,体内大部分水分已被排泄和吸收,这时空腹饮一杯蜂蜜水,既可补充水分,又可增加营养。
喝完蜂蜜水,我抽了根烟,然后开始准备早餐,确切地说是午餐——一桶康师傅方便面。由于水不是很热,面没完全泡开。打开纸盖,飘出一股食品添加剂的味道,我的胃顿时有了反应,一股酸水从下往上直涌嗓子眼。我生生又给咽了下去。边吃边打开手机看未接电话,其中有好几个是公司打来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他们是不会给我打这么多遍的。我一边吐噜吐噜吃着面一边回电话,是小谢接的。她说,合肥的张总今天晚上到。张总是我多年的客户,和他的业务占了公司业务的三分之一,大家一直合作得很愉快。我说,晚上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实在脱不开身,你们把张总陪好。就说我出差了。
方便面的汤味道很鲜。可是面和我的胃口冲突,一大半面没吃下去,却把汤喝完。桌子上已经堆了九个纸桶,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屋子里脏兮兮的,我有些发愁。从茶几的抽屉里找出记事本,翻家政电话的时候,我看见记事本里夹着一张照片。端详端详,照片上的人既熟悉又陌生。我接着往下翻,翻到有几行圆珠笔写的文字的地方,那是个醋熘白菜的菜谱。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把照片夹了回去。
没过多久,家政公司的人就来了,是一男一女,看样子像一对夫妻。我领着他们在屋里转了一圈,交代他们什么地方需要清理,什么地方需要打扫。交代完,我才出门。
大街上和昨天一样,车来人往,我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忙碌?
经过第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段对话:
“明天上街咱们骑自行车。”
“为什么?”
“你看人家那一对,多幸福。”那双眼睛里盛开着羡
慕的花朵。
“怎么了?”
“女的坐在后座,头埋在男人的后背上,多暖和啊!”
我的耳边响起自行车的车链子咯吱咯吱的响声,后背上感觉到那张温润的脸。
三
下午的豪门茶庄安静,茶烟袅袅。
我招呼经理,一个三十上下的女人,“哥们,下棋啊。”
我很早就认识她,因她性格像个男人,所以我称呼她“哥们”。她说友谊长久,对此称呼不反感,因此我就这么喊了下去。
边摆棋子,她边说,“昨天是九比十,今天一定扳回来。”
“凭你那智力,肯定是幻想。”我把烟、打火机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棋下得很认真,两个人基本上没说话,只听见落子啪啪的声音。后来因为她要悔步棋,我不同意,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服务员抿着嘴偷乐。
这子还没完全落下,怎么算悔棋呢?”她眼瞪得溜圆。
“怎么没落下呢,明明是落下了。我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是承认耍赖,就让你悔。”我又点上一根烟。
她“呸”了一声,“你少抽点烟吧,熏得我头发、衣服上都是烟油子味,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抽烟呢。你让我怎么找男朋友。”
“抽完这根就不抽了。”我应付道。
豪门茶庄墙上挂得表好像不准。下了几局棋,时针也没转一圈。我不由得有些焦躁,趁她思考的时候,起身看看摆在货架上的茶叶。货架上有一层灰尘,我抹了一下,看看变黑的手,心想,多久才能落这么厚的灰尘呢?
“你干什么呢?快过来下棋。”看她表情似乎是想到一步妙棋。
我慢吞吞走过去,先从抽纸盒里抽出一张纸,仔细擦手上的灰尘,擦完了,才看看棋盘,摸起棋子就放下去。她又开始思考。
我招呼服务员小静,“妹妹,倒杯茶。”
小静端上一杯日照绿,泡开的茶叶在杯底湛绿湛绿的,冒出的热气带着清香。我吹吹飘在水面上的茶叶,抿了一口。然后问小静,“你在这儿有两年多了吧?”
“马上三年了。”
“找对象了么?”
旁边的小高插嘴说,“人家都结婚了。”
“怎么不通知我去喝喜酒?”我佯装生气。
正盯着棋盘的经理抬起头,说,“通知你了,你说有事去不了,让我代你随礼。”
“是么?”我拍拍脑袋。
“下棋,下棋。”她催我。
我手里捏着棋子,并不放下去。“你们这儿的生意不如过去。要抓紧想想办法。”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快点下棋。”她有些不耐烦。
时间就这么流淌过去,外面不知不觉暗下来。我掏出手机看看点,扔下手里的棋子,说,“到点了,该回家吃饭了。”
“把这盘下完,再走。”经理有些不甘心,今天她输的局数比昨天还要多。
“明天接着下吧。”
“这盘你准输了,不能走,下完再走。”
“那就算我输了。”我笑笑,摸起桌子上的烟和打火机,就往外走。
她在后边追着说,“一看不行就跑,赖皮。”
出了茶庄,我开着车在街上转悠。前面路口左转,新湖路;过两个路口,左转,青龙街;农业局路口,左转,解放路。直行,过两个红绿灯,左转,新一佳超市的停车场。怎么到了这儿?我问自己,天天傍晚来这儿你也不腻?
不行,今天要换个地方,我把车又启动起来。这时候我听见有人敲车窗,咚、咚、咚、咚,四声有节奏的声响。原来是停车场负责收费的大妈,她穿一件蓝色羽绒服,外面套了件黄色马甲,左臂上有个红袖箍,一个浅绿色的书包挂在胸前。我推开车门下车,从裤兜里掏出两块钱给她,她接过来,“今天没票了,明天给你吧。”她忙着整理书包里的零钱,看都没看我一眼。她头上有一缕白发被风吹起来,那样子让我想起房顶上孤零零的枯草。
“行,什么时候给都行。”我应着,快步向马路对面走过去。
走到马路中央,躲闪往来车辆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刚才打算换个吃晚餐的地方。看看近在咫尺的加州牛肉面馆,算了,明天换地方。我想。
店里人不少,热气腾腾的,我看了一眼最里面墙角的那个位置,幸好还空着。刚坐下,那个右眼角有痣的女服务员就冒出来。还没等我说话,她就说,“一共三十二元。”我笑了,她也笑了。我发现她今天打了蓝色的眼
影,没有过去好看。
今天牛肉面里的汤比往日少,红油肚丝里的红油放多了,辣得我直咧嘴。我发现也有如我一样单身的食客,他们心不在焉地吃着,时不时左顾右盼。是不是在等身边的座位不再空着?
吃完饭,我站在这座小城最繁华的街边抽烟。霓虹灯、车灯闪烁,还有明明灭灭的烟头,让眼前的世界迷离、虚幻。我在想像那些坐在车里的人,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心似乎飞到了家里。那里有暖心的问候,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那么一个能和自己说贴心话的人。想想自己,心情变得就像刚才桌子上只剩下点汤汁的空碗一样。脸开始发木,跺脚,活动身子。去哪儿呢?我不停地问自己。
四
后来我萌生了个念头,摸出手机给小吕打了个电话。小吕是我过去的一个同事,辞职后做酒水生意,赔了。现在在开夜班出租车。十多分钟后小吕开着出租车到了。我把自己的车钥匙递给他,说,“你休息休息,我替你开会儿出租。”
转了两个街道,商业银行门口上来一个戴棒球帽的男人。他坐在了后座,其实我是想让他坐到前面。男人要去北园。
我说,“这天气够冷的。”
他说,“嗯。”
我说,“听说北园要拆迁,有这回儿事么?”
他说,“嗯。”
我说,“解放路修路呢,要绕道走湖滨路。”
他说,“嗯。”
之后出租车里开始沉默,这让我有些不舒服。透过后视镜,我看见他正在摆弄手机,手机屏幕发出一闪一闪的蓝色,他的脸被映衬得有些鬼魅。街上很清冷,路灯无精打采的。尽管对面没有车驶过,我还是不时摁下喇叭。时速表上的针始终是在三十到四十之间。我突然觉得喉咙有些痒,老想咳嗽,可就咳不出痰,我只好拼命地咽吐沫。打开车窗,风呼呼地钻进车里,衣领子一下被吹起来,不时拍打着我的脸,一会儿半边脸就木了。
那男人始终没有抬头,他的手机嘟嘟不停地来着短信。这个点,他怎么这么忙?和谁在联系?朋友?这个点和朋友有什么事?老婆?不像。那是情人?直接打个电话多省事?现在我能给谁打个电话,聊聊呢?王胖子?这小子生活有规律,早睡觉了。李哥?不行。这时候给他电话会让他生气的。女的能打给谁呢?王萌?要是她对象接电话,明天准得出大事。
远远地看见了金碧辉煌的霓虹灯,马上就到北园了。这时候我才发现空车灯还没按下来,赶忙按下去。随即车里响起一个有气无力的女声,她好像刚刚睡醒,“欢迎乘坐德州出租车,投诉热线;xxxxxxx。”
下车前我对戴棒球帽的男人说,走好。回应的却是一声重重的关车门的声音。我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心里空荡荡的。嗓子痒得越来越厉害,我用力咳嗽了一声,终于咳出一口痰,我把头探出车窗,使劲吐了出去,那口痰在空中滑行了几秒钟,便被遗弃在空荡荡的马路上。
在钱柜门前我拉了个女孩。大冷的天她穿着裙子。一上车,她边哈气边说,快点走。
我问她去哪儿。女孩不耐烦地说,“往前开就行。”边说还边回头看。因为不知道目的地,车开得很慢。她呵斥道,“你快点!”
我问她,“有急事啊?”
“有人跟踪我。”她这话让我一紧张,挂错了档,车差点熄火。
我透过倒车镜,看见后面有几辆车,赶紧提速。快到路口的时候,我问她,“往哪儿拐?”
“随便,快点就成。”她趴在座背上向后张望。
车开到东方红路,刚才跟着的几辆车都没了踪影,她才坐正位置。我问她,“谁跟踪你啊?”
“我女朋友和她男朋友。”她抿了抿额前的头发。
“你女朋友和她男朋友?”
“是的,他们想害我。”她从坤包里拿出一支烟,熟练地点上。
“你怎么确定他们要害你?”
“他们害了好多人。”她吐出一口烟。烟飘到前面,有点遮住视线,我赶忙用手扇扇。
“那你赶紧报案,这多危险。”
“没用的,没有证据报了也是白报。还会让他们更加痛恨我。”女孩眉头紧皱。
“这一切都是你的怀疑?”我扭头看看女孩,她一本正经的。
“嗯,别看她表面对我好着呢。其实早就琢磨害我。
她还以为我看不出来。”
“她为什么要害你?”
“她就是这种人。有个女的可能已经被她害了。”女孩摇下车窗,把烟头扔了出去。烟头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地后,溅起的点点火星,飘起来,又迅速消失。
“是么?”见我的口气有些怀疑。她说,“那个女的临消失前,我看见他们两口子在背后嘀嘀咕咕。肯定是商量怎么害她。”
女孩说完指着前面路边的一个网吧说,“就在网吧门口停。”
我看着女孩进了网吧的门,又看看旁边的钱柜,里面依然灯火辉煌。
第三个乘客是一个五大三粗的醉汉。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立即把座位塞得满满的。他嘴里吐出一股酸臭的味道,让我有些厌恶,赶忙把车窗的玻璃摇下来。他去国棉厂宿舍,有些远。路上他跟我要烟抽。拿到烟,在打火机打着的一刹那,他转动烟身看了看烟的牌子。点上深深地吸一口,然后缓缓地把烟吐出去。享受了半根烟后,他说,“小伙子,你怎么抽这么好的烟,挣的钱够抽烟么?”我赶忙解释,“这烟是一个乘客落下的。”“那好。”他说着把烟揣到兜里。
我瞥了他一眼,心中有些不快,心想,怎么还有这种人?
“中华烟就是好抽。”我没确定他这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说,所以没有搭腔。
“小伙子要会过日子,现在挣钱多不容易。”
我哼着哈着。
“我给你个信息,保证你晚上能多挣点。”他摇开车窗,吐出一口痰,我感觉有唾沫星子被风吹到右脸颊上,恶心得要命,赶紧用手擦擦。心里想,把他送到,得找个地方仔细洗下脸。
“我刚才从碧波浪沙出来,那可是个高档的洗浴中心,那里的小姐啊,嫩得都能掐出水来。”他嗓子深处滚出低沉的笑声。
“那地方我们出租车司机可去不起。”
“你肯定消费不起,我三天两头地去。”烟都抽到过滤嘴了,他还使劲在裹。
我没吱声,时速表上的指针迅速上升到六十。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去玩,而是让你拉客去。碧波浪沙的老板讲究,介绍一个客人去,给提成二十。”他盯着烟屁股看了得有十秒钟,才把烟头扔了,我看见他右膝盖翘起来扭动了几下。
到黑马市场路口正赶上红灯,我没减速,冲了过去。
“小伙子,好好感谢我吧!”他拍了拍我肩膀。
“谢谢,谢谢。”我应付着。
说话间就到了国棉厂。我停住车,他问,“到了?”
我说,“到了。”
他开开车门刚迈下一条腿。我赶紧说,“大哥,还没给钱呢。”
“钱?我没钱。”他扭过身笑吟吟地说。
“大哥,一看你就是个有素质的人。我们开夜班出租的不容易。这趟你要不给,今天晚上就白干了。”我觉得自己的口气可怜巴巴的。
“算你小子会说话,不用找了。”他扔下十块钱滚蛋了。
计时器上显示的是二十五块四。
快零点的时候我把车交给小吕,还有皱巴巴的二十五块钱。正打算走,小吕喊住我,“哥,请你到永和宵夜。”我回头看看他,眼睛有些发涩,“咱们还是去火车站那边吃烧烤吧。”
还是我开着出租车。车开到广场天桥底下的时候,小吕说:“哥,上火车站你咋开到这里了?这不是去永和的路吗?”我恍然大悟赶忙急刹车,顿时路面上响起刺耳的摩擦声,我的身子也跟着晃了晃。小吕抓住车顶的扶手,关切地问我,“哥,你怎么了?”我趴在方向盘上片刻,抬起头紧咬着嘴唇说,“没什么。”
五
大前年的冬天,中心广场的天桥下,我清楚地记得她穿着艾格牌的白色羽绒服,是我们在保龙仓买的。她紧紧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哈气钻进了我的衣领,痒痒的,又暖暖的。她伏在我耳边说,“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责任编辑:刘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