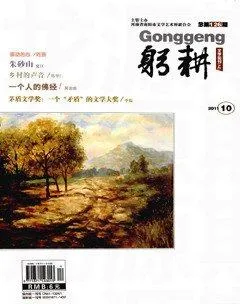乡村世界的鸟音
角角
乡村鸟多,到处都是鸟,很多种的鸟,都集聚在春天。树上落的是鸟,地上蹦的是鸟,天空里飞的也是鸟。人走在山野里,就走进了鸟的家。有的鸟看你走过来,嗖地一声飞了,好像是怕人。有的鸟看见人,“啾啾一滴溜溜”地鸣叫,像是在警告人,这是我的家。还有的鸟在天空上盘旋,在人的头顶上飞,啪地一声,一泡鸟粪落在人头上。
人看见鸟,就会站着不走,看鸟蹦看鸟跳,听鸟叫听鸟唱。
乡村人最喜欢的鸟是角角,叫声清脆悦耳,声音多种多样。“叽-叽溜-叽溜溜-叽溜溜溜”,这是角角的叫声。“滴-滴呖-滴呖呖-滴呖呖”,这也是角角叫的声音。乡村人听角角叫,很惬意,听完就说:“吹笛呢!”
谁也不会想到,名字土里吧唧的鸟,就是百灵鸟。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百灵鸟是一种很美丽的鸟,它们是鸟中的贵族,难得一见。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家乡山坡上的角角,就是百灵鸟。
家乡的百灵鸟,通身褐色,背部灰褐色,腹部淡黄色,背上有褐色斑纹,头上有一小撮毛,应该是凤头百灵吧!家乡人把它们叫做角角,可能源白干它们头上那撮毛吧!
我突然想起,我原来怎么就没有想到,角角就是百灵鸟呢?也只有百灵鸟,才会发出如此不同音调的鸣叫。那天籁般美妙的歌声,麻雀是发不出来的,鹦鹉也发不出来,斑鸠、鹌鹑更发不出来。
“叽溜-叽溜溜-叽溜溜溜……”多么熟悉的声音,它们伴着我长大,陪着我度过了寂寞的乡村生活,它们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乡村歌手。
我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生活在乡村。家乡空旷的山野里,蓝天白云下,总能看到角角的身影,在自由的天地里,它们是快乐的。林木泛绿,麦草青青的春天,那优美的歌声,在山野里此起彼伏。听到这样的歌声,我总是仰起头,在蓝天上寻觅。也许是它们飞得太高,往往是,只闻其声,难觅其踪。
曾经记得,农历三月,山坡上,角角成双成对,蹦蹦跳跳,鸣叫着,寻找适合筑巢的地方。它们常常把巢筑在灌木下,草丛里,也有的筑在栗毛墩里。筑完巢,雌雄角角双双飞舞,从它们筑巢的地方,凌空直上,直插云霄,在天空上鸣叫悬飞,似乎是在祝贺新家的落成。鸣叫一阵后,歌声戛然而止,垂直下落,快要接近地面时,它们又向上飞起来,歌声骤然响起,一阵盖过一阵,响彻云霄。
我小时候喜欢养鸟,常到山坡上抓雏鸟。角角的鸟巢很隐秘,满山架岭地寻找,半天也未必找到一个鸟巢。后来学精能了,看到成双生对的角角在天空上盘旋,起起落落,就划定范围寻找,这种办法很灵验。找到鸟巢后,如果是鸟蛋,就不动鸟巢,做好标记,等鸟蛋孵出小鸟后,把小鸟弄回家养。如果是刚孵出来的幼鸟,也不动,等幼鸟的绒毛褪尽再养。也有刚找到鸟巢,小鸟的绒毛就已褪尽,当场就可以捉回家养了。
养角角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掌握不住食量,不是喂多,就是喂少。三五天一过,鸟就生病,开始是拉白色的稀粪便d6uBdxn+cAPM9xFer4jMcX7IcqS2IoqrXDal/bGgf5s=,然后鸟的翅膀耷拉下来,再后来,小鸟的头也抬不起来,一旦出现这种状况,小鸟很快就会死掉。每年的春天,我们都会反复地抓鸟养鸟。能养活两只角角,别提多高兴了,时常拎着鸟笼,四处炫耀。
在乡村,角角很招人喜爱,人们把角角当做“乡村歌手,”那“叽溜溜-叽溜溜”的歌唱,从未听烦。角角不仅会唱,还会跳舞,它们鸣叫时,大都会伴着优美的舞姿,有时翅膀是静止的,有时翅膀上下忽闪,也有的时候,它们会翻个身扭个腰。对于美,没有人会拒绝的。乡村人,他们也热爱生活,懂得欣赏。因为欣赏,他们喜爱角角。
我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见到儿时的伙伴老歪。老歪曾是我们村子里的养鸟高手,他养鸟,不管啥鸟,养了就活。那时,我们养鸟,他是师傅,常指导我们养鸟。我告诉他,我们以前养的角角,就是百灵鸟!
老歪听了说:“我现在已不养鸟,那是害性命啊!”老歪又说:“什么百灵鸟?我还是觉得角角叫着顺口。”
谁说不是呢?角角是民间的,百灵似乎有点贵族气息。
麻衣鹊
乡村总是躁动的,就是春天寂静的季节,生命的旋律从不停歇。鸟在春天,是乡村的歌手。最初的鸟声,是麻雀,站在初绿的枝头,“啾啾”地叫着。在麻雀的鸣叫声中,树的枝头,长出了嫩绿的叶片。“麻衣鹊”似乎是受到了感染,飞上枝头,大声地呜叫,它们的声音,盖过麻雀,滑过树的叶片,响彻大地。
“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叫得脆响,树枝晃晃悠悠,把声音传递到人的耳膜。当人们听见麻衣鹊的鸣叫,脸上花一样绽出笑容。没有人拒绝麻衣鹊的歌唱,在乡村人看来,这是喜庆的歌声,吉祥的歌声。
“麻衣鹊”其实就是喜鹊,这在乡村,几乎人人都知道。但乡村人习惯了“麻衣鹊”,从不把喜鹊叫做喜鹊。甚至把民谚“喜鹊叫,喜事到”也改成“麻衣鹊叫,喜事到。”喜鹊,在民俗里,一步步成长为“麻衣鹊。”
乡村人长期与鸟相处,接触较多,对鸟的形体、色泽、脾性十分了解,对鸟类产生了不同的情感。比如《禽经》中说的喜鹊“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
宋代欧阳修赋诗赞道:“鲜鲜毛羽耀明辉,红粉墙头绿树林;日暖风轻言语软,应将喜报主人知。”说的都是喜鹊报喜。
在乡间,“麻衣鹊”或者喜鹊的传说,人人皆知。牛郎与织女的故事,影响了多少代人,谁也无法说清。七月七天河相会,喜鹊搭的鹊桥,曾经让我们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仰望星空,寻寻觅觅。葡萄架下,少男少女,侧耳倾听,牛郎与织女的呢喃,总在梦里萦绕。很多年过去,天上的鹊桥,至今没有看到,只留下一个梦。
鹊桥是没有看到,但“麻衣鹊”却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它们三五成群,出没在山坡上,林子里,村庄及庄稼地。我们小时候看它,总是带着朝圣者的目光,甚至觉得,那黑色的头与尾巴,白色的颈与腹,色彩的搭配,是那么的完美。“麻衣鹊,”在我们的少年,带来的总是神秘。
少年时期,对于神秘的东西,总想一探究竟。“麻衣鹊”我们只能远远地观望,但它们的巢,还是触手可及的。往往是在“麻衣鹊”不在巢里时,我们爬上大树,观赏它们的巢,看那淡蓝绿色,布有浅褐或紫褐色斑点的鸟蛋,甚至摸摸毛绒绒的雏鸟,满足我们的好奇。
“麻衣鹊”的窝巢非常考究,用枯树枝粘土粘合搭建而成,呈球形状。有顶盖,外层为枯树枝,杂草和泥土;内层为细的枝条和泥土,垫有麻、纤维、草根、羽毛等柔软物质。老鹊喜欢自己的旧巢,小鹊则营造新巢,繁衍后代。
对于“麻衣鹊,”乡村人有着特殊的情感。在乡村,不但没人养“麻衣鹊,”更没有人猎杀“麻衣鹊。”乡村的孩子,总是顽皮,喜欢抓雀掏鸟蛋,但对“麻衣鹊”却始终不敢下手。那种对“麻衣鹊”的敬畏,来自于父辈教诲和乡间民俗。
乡村的女孩,对“麻衣鹊”更是情有独钟。怀春的姑娘,总是望着“麻衣鹊”若有所思。乡村女孩对“麻衣鹊”的钟爱,来自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很早以前,一个待嫁的姑娘,正在绣楼上“哭嫁”,突然听到一只鹊儿的阵阵叫声从窗口飞了进来。姑娘走到窗口向花园望去。看到梅枝上有只从未见过的鸟儿,羽毛美丽,叫声悦耳,舞步轻盈。姑娘很高兴,取来剪刀和红纸,照着鹊儿和梅花的样子,很快便剪成了一幅窗花。家人来催姑娘上轿。姑娘却拿着刚剪好的窗花,自言自语道:“这是什么鸟……”快嘴的丫环忙说:“今日姑娘大喜,就叫它喜鹊吧!”姑娘到了婆婆家,婆婆见新媳妇的这幅“喜鹊登梅”的窗花,很喜欢,就照着画了,又加了只喜鹊,寓意成双成对,双喜临门。此后,每逢姑娘出嫁,总要剪些“喜鹊登梅”的图案,贴在嫁妆上,沿袭至今。
乡村的女人对“麻衣鹊”的那种感情,是与生俱来的。从她们闺女时代的窗花,到婚嫁时的陪嫁物品,都与“麻衣鹊”有关。在乡村,看到有人做伤害“麻衣鹊”,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女人。她们大声地呵斥,絮絮叨叨诉说着“麻衣鹊”好和祸害“麻衣鹊”的带来的厄运。可以说,女人,是“麻农鹊”的守护者。
我总是在想,在乡村,人们为什么对“麻衣鹊”由衷地热爱?也许是来自于淳朴的民风,也许是沿袭已久的民俗,或许是长久以来的和睦相处。似乎都是,似乎又不是,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无法说清。
其实“麻衣鹊”,它们是乡村的灵魂。没有“麻衣鹊”,乡村变得魂不守舍,大地充满着孤独、死寂。不仅是“麻衣鹊”,就是麻雀也一样。如果有一天,人们听不到麻雀的声音,也一定会感到孤独,思绪就会漂移不定,灵魂将无所依附。
很多事物,是相互依附的,缺一不可。就像人与“麻衣鹊”,就像人与树。没有了树,大地就没生机,生命就会枯萎;没有“麻衣鹊”,听不到优美的歌唱,人就孤寂。
我们不想孤寂,那从树梢上滑落的声音,是那么的美妙。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这样的歌唱:“喳喳-喳喳-喳喳喳喳……”
火斑鸠
火斑鸠,它们属于故乡,痴痴地留恋着它们生活的地方。它们从不记恨曾经受到的遭遇,尽管那是无法忘却的悲伤。
只要有记忆,就不会忘记,一种美丽的鸟所遭受的杀戮。我没有忘记,那些贫困的年代,火斑鸠所承受的灭顶之灾。我那时就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痛下杀手,猎杀这么美的鸟。
火斑鸠,真的很美,见到这种鸟的人,都会忍不住站下来观望。它们的头灰色,颈部青灰泛绿,翅膀、胸腹和肩背红褐色,尾巴上黑下白,色彩搭配时尚,激灵灵飞起来,是亮丽在高空炫目的风景。
每年的春天,火斑鸠开始恋爱,准备建立家庭。确立恋爱关系后,它们成双成对,迎着晨雾,披着暮霭,叼来树枝,为自己营造新家,在自己的新家里,忙忙碌碌,生儿育女。
我在家乡时,看到过两只斑鸠安静地卧在自己的巢里,比肩歇息,卧听风雨。它们的温暖,就是这么就简单,简单到没有人打扰,简单到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这样的温暖,是一种幸福,一种平淡的幸福。
这种幸福,总是瞬间即逝。我看到过它们凄厉的鸣叫,它们的巢里,那不多的三两只鸟蛋,被人捡走了,那是它们尚未出生的儿女,就这样被扼杀了。那种叫声,似乎是无奈的呜咽,是失去儿欠的伤痛。
更多的时候,它们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鸣叫,就一头从树上栽了下来。那一刻,它们听列一声轰响,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而那个放枪的人的家里,锅里冒出扑鼻的斑鸠汤,或者是一只只香味四溢的五香斑鸠。
我有些时候就没弄明白,那么小小的一只斑鸠,能有多少肉可供食用,人们为什么那么的喜欢吃火斑鸠呢?有人说,火斑鸠补肾壮阳,乡村的人,个个都很喜欢。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确实如此。火斑鸠用于男人,可治疗肾气虚亏,阳痿不孕、腰酸遗精、头晕耳鸣。它们的悲哀,来自千男人对于性的贪婪。
火斑鸠警惕性很高,并不容易捕杀。也有人说,火斑鸠是一种灵性的鸟,对来自于外界的危险十分灵敏,偶遇风吹草动,立马振翅而去,很难猎取。但贪婪的人们,并不因为难以捕捉,就会放下手中的猎枪。现在乡村是没有猎枪的,那些火药枪,在90年代中期被收缴。但是,另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新式武器随着猎枪的收缴,应运而生,这就是网,专门用于粘鸟的网。
我回老家,多次看到山坡上,三三两两的人,拿着粘鸟的网,在山坡上、果园里乱窜。这种网,主要是粘斑鸠的,三五个人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粘到各种斑鸠数十只。在市场上,一只斑鸠可以卖到10元。巨大的利益诱惑,让很多人丧失了良知。
在家乡,这样富有灵性的鸟,人们却没有把它们当做朋友,总觉得是一种遗憾。不过,遗憾的不仅仅是一种叫做火斑鸠的鸟。还有很多的鸟,就在我们的遗憾中,告别了蓝天白云。
让鸟们自由的飞翔,给它们一片蓝天,似乎还是一个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贪欲,悲剧就会继续上演。
水母鸡
乡村总是宁静,没有城市里的喧嚣。山野里,只有鸟的声音,杂乱地歌唱;风凑着热闹,呼地刮过,带着一丝哨音,掠过山坡,从低洼冲出去。风过低洼处,总会有一个堰潭,碧绿的水面,挂着一丛丛水草,有几只水鸟,在水面上嬉闹。在北方山区,只要种植水稻的地方,这样的堰潭,处处可见。这是北方山区,独特的风景。
人不觉得这是风景,司空见惯,到处都是。水鸟不同,水鸟的想法奇特:山野里多么的宁静,那一潭清水,就是一片大海,多美的风景啊!它们在堰潭里尽情地挥洒着快乐。水鸟在微波上一晃一晃地游着,高兴时,头一缩,钻进了水下,不见了踪影。
农人看到水鸟,站着不动,看了一阵,看烦了,对着水面,丢一颗石子,水鸟扑棱棱飞向远方。
没有人近距离看到这种水鸟,倒是有人用枪打死过水鸟。死后的水鸟,看上去像鸭子,也不像鸭子。有人说是水鸭子,可比水鸭子小一点。我后来查阅资料,这种水鸟,其实就是一种鸭科动物,叫绿翅鸭。家乡不知道是什么鸭子,把这种水鸟叫“水母鸡。”
我喜欢这种像野鸭也像秧鸡的水鸟,我更喜欢水母鸡这样通俗的叫法。在乡村,看见这种水鸟,我们总会说:“看,水母鸡,水母鸡。”为什么叫水母鸡?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少年时代,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寂寞时,我会走上山坡,在长满栗毛的山坡上,晃来晃去,看见一只鸟,我看半天;看见一群鸟,我也看半天。我在山坡上,我在鸟声里,消磨着时光。更多的时间,我会在家乡的堰潭之间来回穿梭,看水母鸡,看它们在水面上悠闲地游玩。我看见过一只水母鸡从堰潭这边钻入水中,又从那边钻出水面,然后甩甩头,继续在水面晃荡。它们的悠闲,让我羡慕。
乡村的人,不会像我那样,只是看看,看它们的快乐,看它们的自由。他们不这么想,在他们的眼里,“水母鸡,”这些肥嘟嘟的水鸟,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他们看水母鸡,是一盘盘下酒的菜,是营养普遍缺乏的年代最好的滋补品。水母鸡成了他们猎杀的目标,他们三五成群,掂着火药枪,出没在堰潭、水库、河流边,躲藏在树丛里,贪婪的眼睛,盯着水面。
我在老家时,有一次去南洼,经过南洼堰潭,突然看见几个人,手里掂着火药枪,几个人呈扇形分开,用火药枪对准堰潭。离堰潭很远,我看见一群水母鸡在游玩,大概有几十只,在水里钻来钻去。还没等我走过去,就听见几声枪响,那些刚刚飞起来的水母鸡,纷纷坠入水中。几个人脱下衣服,在水里捞那些中枪的水母鸡。大概有十几只,一溜地摆在面前,那些人看着死去的水母鸡,抽着纸烟,笑得脸上开了花。
躺在地上的水母鸡,刚刚还活蹦乱跳,在水面上游玩,瞬间就折翅而亡,抛尸荒野。还有那么一两只,在抽搐着,痛苦地挣扎,等待着死亡的来临。那一刻,我感到生命的卑微。在人的眼里,生命,一如草芥。
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想到的是美味带给他们的快感。在人们的意识里,生存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一只水母鸡,就是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当人们拿起枪瞄准水母鸡时,当人们大口啃咬着水母鸡鲜嫩的肉时,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记得那时候,水母鸡很多,堰潭、水库、河流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只要有水母鸡的地方,就有猎杀水母鸡的人的身影。可能是被打怕了,水母鸡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腾空而起,瞬间消失在远方。人们说:这小东西学精了,打不住了。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但我一直没有记住它们的容貌。它们鲜活的样子,是不是可爱,我一无所知。我看到的是它们血淋淋的尸体,还有临死前那痛苦的挣扎。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事实,可这确实是事实,我真的没有近距离地看过它们。我看见的是游在水中的水母鸡那朦朦胧胧的身影。
我老家现在还有水母鸡,因为没有了火药枪,因为生活好了,也就没有人再打这种鸟。可是,老家的堰潭,却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只有在远离我老家几十里的鸭河、冢岗庙水库看到。远远地,它们悠闲的样子一如当年。只是,它们已不再是当年的水母鸡,警觉地游在水库中央,远离了人群。
磕头虫
每次看见它们,多是在稀疏的林子里。农家的房前屋后,也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喜欢到农田、溪流边觅食。看见人,胆子有点小,马上转身,用背对着人。人若再靠近,便发出“咕咕一咕咕”的鸣叫声,然后忽闪一下翅膀,飞到树上,对着人,反复地呜叫。
它们原本是不叫磕头虫的,斑鸠的一种,学名“珠颈斑鸠”,这是我从关于鸟的资料里看到的。这种斑鸠有个特点,鸣叫时喜欢不停地点头,我们家乡人就叫它磕头虫。为什么把鸟叫作虫呢?家乡人有个习惯,把鸟都叫作“虫意儿。”比如麻雀,个头小,乡村人就把麻雀叫做“小虫。”珠颈斑鸠喜欢点头,就叫它“磕头虫。”生动形象,叫着顺口。
磕头虫的长相比较可爱,头为鸽灰色,上体大都褐色,下体粉红色,颈部为淡粉红色,间杂有黑白分明的斑点,看上去比较醒目。它们的尾巴细长,黑色,但尾梢白色。有美感,可供欣赏,但不知是否为观赏鸟。就我个人而言,这应该是一种美丽的观赏鸟。
我们老家,这种鸟不多,很少见到。早些年我在老家时,看到过这种叫磕头虫的鸟。它们三三两两,有的落在电线上,有的落在树枝上,很少看到成群的磕头虫出现在树林里或田间地头。
它们有着美丽的身材,常吸引孩子们的目光。乡村小孩顽皮,看到它们长时间落在树枝上不动,就甩块石子。磕头虫往往会吓得翅膀一抖,惊恐地飞走。它们飞翔时,速度极快,但不能持久,飞了一阵,马上就会落到附近的树枝上,也有的落在农田里。受惊的磕头虫,叫声响亮。看到磕头虫被惊飞,孩子们高兴地哈哈大笑。
我看到过它们的巢,很简单,是用小树枝搭建的,里面铺些柴草。它们的巢,大都筑在高高的树权上,一般的小孩,是够不到的。就是善于爬树的孩子,也不敢爬上去掏鸟蛋,一是怕树高,会摔下来。二是不知道鸟孵化时凶不凶,怕鸟啄人。因此,村子里的人,很多没看到过鸟蛋啥样子?也没看到过幼鸟的模样。
这种鸟也在房屋上筑巢,我在家乡时,没看到过。有人说它们偶尔会在地上筑巢,但大都在山坡上。家乡的斑鸠有多个品种,它们的卵,也基本相似,就是看到了,也分不清是那种斑鸠产的卵。
磕头虫是爱干净的鸟,它们的身上,经常光溜溜的,羽毛紧抿在身体上,看上去干净利落。它们喜欢到小溪边,捉捉虫子,喝点溪水。但主要是为清洗身子。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断定。但我看到过它们洗澡,有时候用翅膀拍打溪水,用溅起的浪花,清洗身上的污物。也有的在水里翻个身,然后扇动翅膀,水珠四溅,以此清洗身子。
据说,磕头虫肉质鲜美,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现在,已有人工饲养。但不知是作为美味饲养,还是作为观赏鸟来饲养的?反正,我老家没有饲养珠颈斑鸠的。
现在的老家,有没有磕头虫?我不知道。我回家乡,没看到这种鸟,因为没看到,不敢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有,恐怕也不多了。为啥出现这种状况,说不清楚。要说是人为捕杀,也不是。我在老家时,很少有人捕杀磕头虫。只能说,是环境的因素吧!
野布鸽
人都是爱美的,我也是,我喜欢美丽的东西。比如衣服,比如女人。爱好衣服和女人,是我长大以后。在我成年以前,在我乡村老家,我喜欢鸟,特别喜欢美丽的鸟。鹦鹉我喜欢,黄鹂鸟我喜欢,百灵鸟我也喜欢。还有一种鸟,体型大一点,我没养过,但我也喜欢。这是我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体型较大的鸟,家乡人叫它“野布鸽。”
野布鸽是鸟的小名,也是俗名。我说的野布鸽,其实就是岩鸽,一种生存在野外的野鸽子。在家乡,人们把不是家养的与鸽子差不多的鸟,都叫野布鸽。这种习俗,由来已久。
野布鸽体型与家鸽相似,羽毛灰色,脖子、上胸部绿色与紫色,在阳光下闪着美丽的光芒。腰部到尾部有一白色横斑,腹部多为白色,黑嘴红脚,模样还算俊俏。
对于野布鸽,我比较陌生,很少看到它们。我十来岁时,它们就不多见了。而它们的巢大都筑在陡峭的悬崖边,或者石缝里,很难看到。据说它们的巢筑的很简单,是用枯树枝,杂草、和羽毛筑成的,看起来很凌乱,没有一点美感,与它们美丽的相貌有着很大的差别。
野布鸽的叫声不怎么好听,像家养的鸽子,“咯咯一咯咯”,反复地鸣叫。只有受到惊吓或者是从天空落下时,才会发出音调很高的“咕咕一咕咕”声。这种声音听起来有点发颤,似有惊吓所致。
我们家乡,属于浅山丘陵,适应野布鸽生存,六七十年代,这种鸟比较多。它们栖息在山石峭壁间,觅食时,结成小群,在山间觅食杂草的种子。落到草地上,就是一片,在草地上悠闲地溜达,不时地在草地上寻找食物。遇到人,“咕咕”地叫着,呼扇着翅膀,扑棱棱飞走。
秋天,农作物成熟季节,喜欢到农田里寻找食物。看到高梁地,一只鸟落到一棵高粱上,只要没有惊扰,直到吃饱,才会飞走。农人收获高粱时,砍下的高粱穗,大都是空壳,里面的高梁米,被野布鸽啄食一空。因为与农人口中抢食,农民对它们十分反感,常用土枪猎杀。
在乡村,野布鸽也是农人捕杀的对象。当然,这种捕杀,并不全是它们危害农作物的原因。野布鸽的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农村人捕杀野布鸽主要是用来滋补的,尤其是病人,家里穷,买不起营养品,就捕几只野布鸽熬汤,为病人增加营养。
野布鸽是一种义鸟。它们在遭到危险时,所表现出的舍生忘死的精神,令人震撼。我在老家时,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猎人上山打猎,转了一天,没有打到一只猎物,回家时,看到一群野布鸽,大概有十几只,猎人对准那群野布鸽放了一枪,打中了一只,在地上扑棱。猎人很高兴,跑上前去捡那只野布鸽。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几只飞上天空的野布鸽,突然箭一般地飞下来,架起那只受伤的野布鸽腾空而去。猎人惊得嘴巴大张,当他回过神来,那些野布鸽早已无影无踪。
这是村子里人说的,事情发生在很早以前,那个打猎的人,是村子里的张老五。我没看到这样的场景,但我相信,这是真的。这样舍生取义的鸟的故事,没有经历过的人,是编不出来的。就是小说家,也未必能编出这样震撼人心的故事。
故事是美的,但不是所有美丽的故事,都有个美丽的结局。家乡人并没有为它们美丽的故事,心生慈悲,放下猎杀的土枪。因为一点粮食,因为它们的鲜美,它们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秃尾巴
一种没有美感的鸟。全身栗黄色,黑褐色与白色,翅膀总是耷拉着,没有尾巴。不论是色彩,还是形体,都没有亮点。它们不怎么飞,看见人,翅膀扑棱着,半飞半跑。是鸟不喜欢飞,在乡村,人们总觉得它们不是真正的鸟,言语里就有点歧视。因为没有尾巴,乡村人连它们的名字也不喊,就叫它“秃尾巴。”
在我们家乡,谁都知道,这种鸟叫鹌鹑,但谁也不喊它们鹌鹑,似乎把它们的名字淡忘了。人们看到这种鸟,就说:“看,有一只秃尾巴在跑呢?”
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鸟。在有人烟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与人类的关系源远流长。其貌不扬的鹌鹑,是从《诗经》里走来的,是从古埃及的金字塔里走来的。在战国时期,鹌鹑被列为六禽之一,成为筵席珍肴。在民间,喜欢吃鹌鹑的人,也大有所在。我们家乡,也有很多人喜欢吃鹌鹑。有句俗语:“天上飞禽,鸽子鹌鹑,地上走兽,兔子狗肉。”所以,鹌鹑是乡村人喜欢的美味。
秃尾巴模样有点邋遢,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它们的喜爱。鹌鹑不但是不可多得的美味,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说:“肉能补五脏,益中续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适用于治疗消化不良,身虚体弱、咳嗽哮喘、神经衰弱等症。《食疗本草》中有“食用该种食物,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其药用价值被视为“动物人参。”
在乡下,人们对不花钱,既是美味又能治病的动植物,有着本能的喜爱。乡村人,大都经济拮据,能省钱尽量省。捉鹌鹑,成为人们治病的借口。走到路上,看到有人手里掂着火药枪上山,人们见了就打招呼:“干啥呀?”抓鹌鹑的人就说:“抓两只秃尾巴,补补身子。”秃尾巴一般是单个或成双出现,很少有成群结队的“秃尾巴,”用火药枪打它们,效果不明显,往往是放了几枪,也就捕杀到三五只。
也有的人是用网。那时的网,不像现在的网,有胶水粘性大,秃尾巴撞上就跑不掉。过去的网,没有胶水,下一次网,一个晚上也就五七八只,运气好的,十几只就很不错了。还有的人是夜晚用手电筒照。秃尾巴这种鸟,有点傻呼呼的,夜晚用强光的手电一照,眼睛就花了,头一缩,趴在地上不动。照秃尾巴的人,用手就可以抓到它们。
抓回去的秃尾巴,有的用作病人补身子,但大部分被人当做了下酒菜。前些年,市场上收购秃尾巴,一元钱一只。现在收一只秃尾巴,估计需要两三元吧!饭店里卖的,一只六元,需求量很大。我的工作单位不远,有一家饭店,生意很火,店里就供应秃尾巴鹌鹑,一只六元。服务小姐说,卖得很火,一个晚上能卖出去数百只。不过,那些鹌鹑,都是养的,野生的很少,山上的秃尾巴被抓干净了,上哪弄野生的呢?
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这是人的贪婪。比如美女,男人看到,总想多看两眼。还有的人,手里有点钱权,看到美女,就不仅是多看两眼,总是想方设法搞到手里,占为己有。鸟也是,美丽的鸟,人们总想把它们装进鸟笼,供自己欣赏把玩。而像秃尾巴这类的鸟,虽没有美丽的容貌,但肉质鲜美,自然也逃脱不了厄运,成了人们口中的美味。
如果有来生,秃尾巴最好不要做鸟。做鸟不是被养在笼子里,是被人吞到肚子里。也不要做植物,做一棵植物,不是被割掉;就是被砍掉。更不要做人,做人长得丑了,被人歧视;长的美了,被人玩弄。要做就做一滴水,流进大海,波涛汹涌,随波进退,蒸发了成为空气,来去自由。
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的话,她说:“我要做一只小鸟,飞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告诉她,千万不要做一只小鸟,要做就做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