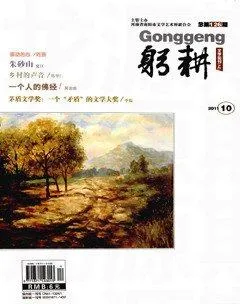1975年的狗事
村里屠狗的那天早晨大雾弥漫,天地仿佛浑沌了一般,平日里很清晰的房子和树全不见了,连河坝也不见了踪影。屁孩推开门吓了一跳,他想要是这样在街上走来走去,很可能会把自己走丢。
屁孩是村里有名的睡不着,早晨天不亮,他就踩着爹娘的鼾声出了门,一直走到黄河坝上。站在坝上眼界立时开阔起来,眼见得那些房子小得如同鸡笼一般,依附在坝下。再远了看便像羊屙屎似的细长的一溜。房顶上狗尾草茂盛地长着,衬着土不拉几的矮墙,让人想起多少年未理过发也未洗过澡的乞丐。只有村北大队部的房顶是瓦片覆盖的,暗红暗红的像凝固了的猪血。紧挨着大队部的是三喘家的房子。三喘是个痨病鬼,他喘起来全村都听得上。屁孩睡不着的毛病就是三喘给吓的。
那年,三喘喊屁孩他爹小神仙起来上坡。喊完了,三喘便在窗棂子下自顾自喘起来,一口粘痰在肺管子里上上下下,像只软木塞子被推来搡去,将正在熟睡的屁孩吓醒了。此后,鸡叫过了头遍,屁孩便再也睡不着了。别的孩子一岁多就会说话,屁孩到了三岁还吐不出半个字。这可把小神仙急坏了。小神仙是村里的厨师,娶媳妇嫁闺女的人家都来请小神仙去做酒席,公社来了领导要炖鸡炖羊也把小神仙喊了去,做酒席除了白吃三天饭,末了,事主还会送两瓶好酒,一挂猪大肠。为了给屁孩治病,小神仙把这些到手的好处全辞掉了,一心一意带了屁孩去看病。公社县里地区的医院转了个遍,中药西药吃了几十付仍不见好。夜里,小神仙偷着请来村里的神婆五奶奶。五奶奶很有把握地说,没啥,这是让三喘把魂吓掉了,收起来就好。说完,便用一方脏兮兮的手帕撮了绿豆、红豆、小米,又让小神仙剥了一棵葱准备了一双筷子,嘴里便念念有词地替屁孩收魂。收了之后,屁孩仍然睡不着,仍然早早就出了门。再问五奶奶,五奶奶摇摇头道:这可奇了,怕是屁孩的魂附在三喘身上了吧。小神仙听了五奶奶的话,有点半信半疑。他怕大队书记马小辫说他搞封建迷信,赶紧拿出家里的二斤烟叶打发五奶奶走了。
屁孩在街筒子里瞎逛,就把大人们的一些鸡零狗碎全看在眼里了。别看屁孩才六岁,也已经懂些事了。有好几次,他看见赤脚医生刘大收从小灯笼家出来,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他还看见公社驻村的程胖子翻过半截土墙去会小白鞋。屁孩见程胖子两只肥臀从矮墙上滚过去,就知道三喘一定又是出公差了,一定又是多少天不能回来。
现在那些鸡零狗碎的事看不到了,连晚玉米青枝绿叶的模样也隐去了。屁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耳朵里灌进了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虫的吟唱,好像有唱不尽的忧伤。凭经验,那些吟唱是从晚玉米棵子里传来的,他知道已经到了村北的井台,再仔细找了找果然就看到了井台。井台上没有一个人来打水,井口倒是热气腾腾显得很神秘。屁孩正看得出神,蓦地,黄大从雾里钻了出来。
黄大抖了抖身上的露水,冲屁孩摇了摇尾巴便向一块牛屎奔了过去。它很认真地嗅了嗅,围着牛屎转了两圈,抬起腿撒了泡尿又嗒嗒地跑开了。屁孩知道黄大是和三喘一起看坡去了。坡里那些晚玉米嫩嫩的,掐一下就流出奶一样的汁液,这就需要人去看,省得让人偷了让狗啃了。三喘去看坡,把小白鞋一个人扔在家里,让他很不放心。不过,大队里安排的活,三喘不能不去,尽管他对小白鞋一百个不放心,他还是得去。三喘不但是村里杀猪的屠夫,他还是村里枪头子最准的猎手。三喘去看坡的时候,黄火也一起跟了去,反正黄大在家也挡不住程胖子。程胖子的肉骨头把黄大喂得都里通外国了。想到这些,三喘就气炸了肺,指着黄大的头说,你真是个白眼狼,白费了那么多玉米面窝头。骂归骂,看坡的时候,三喘还是要带上黄大。他胆小,一个人在坡里睡不着,有了黄大他就能安稳地睡觉了。可是,黄大放不下母狗青花,每天早早地就从坡里跑回来了。
黄大从坡里跑回来,不知道正有一个劫数在等着它,等着村里所有的狗。这个劫数本来可以晚一点来到,是大队书记马小辫一句话,让这个劫数提前了。马小辫说秋后社员们没啥事干了,别闲出事来,让他们把狗打了吧。程胖子听了笑道:行啊。也该吃狗肉了,村里那么多狗要费很多粮食呢。见程胖子同意了,马小辫就在鞋上磕了磕烟袋锅子说,我这就让狗子去安排。狗子是马小辫的侄子,村民兵连长,同时还兼着打狗队的队长。黄大跑回村的时候,狗子已经下了通知,要队员们到大队部开会。开会点名的时候没有点到三喘。狗子知道三喘去看坡了,就说不等狗日的了,让他一回来就到小神仙家去。开完会,狗子便和队员们在大队部吃烙饼卷大葱。小白鞋说,我们家三喘的那份呢?说着,就卷了五张大饼扭着浑圆的屁股走了。小白鞋出了大队部,狗子对其他队员说,瞧瞧小白鞋,屁股蛋子都快撑破裤子了。队员们听了都哈哈地笑起来。
黄大还在想着它和黑狗米汉的爱恨情仇,对于日益迫近的危险毫无察觉。它现在对米汉耿耿于怀。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米汉,它和母狗青花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黄大是村里的狗王,完全应该得到母狗青花的青睐。这段时间,黄大发觉青花对自己没有以前那么热情了,反而对米汉大献殷勤。米汉是小灯笼家的狗,与青花是邻居,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地利上,黄大是吃了亏的。现在黄大又随了三喘去看坡,行动上更不自由。自从程胖子勾搭上小白鞋,三喘出公差的机会就多了。到了秋上,就干脆让三喘去看坡了。黄大没少吃程胖子带来的馒头和肉骨头。虽说吃人嘴短,可黄大对程胖子和小白鞋的作派还是很看不惯的。每次程胖子来了,它都会呜呜地低吠两声。不过,再优秀的狗也抵挡不住肉骨头的诱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黄大只是一条狗呢。
有一点,黄大是很自豪的,它从来没有到茅坑里吃过屎。说狗改不了吃屎,那是对村里其它的狗说的。它就亲眼见米汉进过茅坑。从那以后,它就对自己的情敌充满了鄙视。它不明白,青花怎么会看上米汉这样的草莽英雄,它难道就不嫌米汉的口臭。吃屎的狗嘴里都会有一股难闻的怪味。
黄大来到屁孩家的时候,看到青花正跟米汉耳鬓厮磨。它示威似地吼了两声,米汉也龇出了锋利的牙齿。青花见了便走过去亲一亲黄大的脖子,以平息黄大的怒气。黄大梗着脖子一动未动。青花见状便悻悻地跑开了。它小跑着去了场院的秫秸垛,那里有它的三只幼崽。青花跑的时候两排奶便一直晃荡着,像面旗帜似地把黄大和米汉一起引了过去。见青花钻进了秫秸垛,黄大和米汉便一左一右立在那里,成了青花的忠诚卫士。后来,当青花遭遇劫难,黄大和米汉表现得英勇无畏,不说气吞山河但也算得上壮烈,确实可围可点。
三喘醒来时,黄大已经不见了。三喘便扯起了嗓子喊黄大。可是,雾中什么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软软的像撞在了棉花上。三喘以为黄大出去撒尿了,就爬起身提了鸟枪骂骂咧咧地去找黄大。三喘骂了黄大,心里痛快了些,就好像他已经骂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他不敢惹。不然,深秋季节自己也不会出来看坡。夜里那个人还睡了自己的老婆,也许现在正睡得有滋有味。这些事村里都传遍了。三喘觉得自己不该是这么个熊样,他是村里的屠夫,杀猪是很在行的。那些别人杀不了的猪,他一刀就结果了,但他就是怕那个程胖子。他之所以胆怯,是因为他下面不好使了。前年村里杀年猪时,那头六百斤的大公猪不断地挣扎,居然把绳子弄松了,三喘一刀下去捅偏了。那头猪缓过劲来用力一蹬,正好蹬在他的命根子上。以后,三喘晚上就失了往日雄风,这就让程胖子钻了空子。再说,小白鞋也是这样的烂货,离了男人就睡不着觉,两个人一拍即合。三喘家与大队部只隔了堵半人高的土墙,是个男人挺挺身子就过去了。原本三喘是要修一修的,却一直想等大队里修,这样也好省几块钱的料钱。谁成想,无形中倒是便利了程胖子。三喘要告姓程的,大水把她爹拦下了:告啥告,这是光彩的事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大水说这事你甭管,我去找程胖子。找了程胖子不久,大水就到公社去上班了。大水模样俊,嗓子好,唱样板戏里的小铁梅那叫个绝,轰动了全县。大水也会和那些个领导们交往,让那些领导觉得大水真是水做的骨肉,不像那些革命女人一天到晚冷冰冰的,一点也猜不透领导们的心思。不知道领导们除了抓革命促生产,时间长了也需要滋润一下。不到一年,大水就成了公社的妇联主任,能够列席公社党委会议了。
小白鞋与程胖子出了那档子事,三喘最恨的是黄大。程胖子翻墙进院的时候,你咋一声不吭。那肉骨头就那么好吃,你他娘的跟汉奸有啥两样?三喘越想越气,他吭吭地咳着,那些雾被震得一漾一漾的。猛然间,他看到玉米地里有什么在动。三喘心里骂道:娘的,这个黄大在偷玉米。想到这里,三喘就动了恶念:把这个吃里扒外的黄大打死,出了口恶气不说,还落了一张好狗皮。再说,自己不打,黄大也活不长了。狗们经常到坡里偷吃玉米,每年秋后,大队里都要组织打狗队,保卫劳动果实。想到这里,三喘就开了一枪。那个影子摇晃着倒了下去。毕竟是自己家的狗,枪响之后,三喘心里有了一丝隐隐的恐惧。本想去看看,又怕黄大没死反被那畜牲咬一口。踌躇了许久,听到狗子在喇叭里吆喝打狗队集合,心里才略略宽慰了些,毕竟这畜牲气数尽了,不被自己打死也会被狗子等人要了命。说不定自己这一枪把黄大吓跑,反而让黄大躲过了一劫。眼见太阳从雾里钻出来,知道到了饭时,三喘便提了鸟枪往村里赶。要打狗了,再怎的,也不能耽误了烙饼卷大葱。
三喘进了村,正看到狗子押着赤脚医生刘大收和小灯笼过来。狗子让三喘先到小神仙家集合。几个看热闹的说,刘大收和小灯笼火白天也不闲着,趁着大雾便明目张胆起来,还不停地呻唤,让狗子逮了个正着。狗子觉得这事挺严重。小灯笼的男人在煤矿当工人,刘大收这是在破坏工农团结。三喘见狗子押着刘大收和小灯笼过去,心里好像出了口恶气:这些狗男女是要斗争了。要是再把小白鞋和程胖子纠出来斗一斗那才好呢。三喘这么一想,仿佛吃了顺气丸浑身通泰,接连放了两个响屁,食欲也被勾了起来。他没有去小神仙家,而是径直去大队部扯了两张面饼,也顾不得喘声如牛,鼓起腮帮子嚼着烙饼卷大葱,一路上噎得嗝声不断。
三喘进了小神仙家,屋里已经挤满了打狗队员,一个个叼着公家的烟卷儿弄得乌烟瘴气,把三喘呛得一个劲咴咴地喘。他折身来到院子里,见小神仙已经支起了炖狗肉的九丈大锅,灶上备足了大葱、蒜瓣、花椒,桂皮,单等着狗肉下锅。炖狗肉是个美差,谁家炖狗肉都会落一大锅狗肉汤,吃罢了狗肉,厚厚的一层狗油又可以炖几大锅白菜,让全家人可劲地吃上三五天。所以,很多人对小神仙炖狗肉都很眼馋,也到大队部反映过。马小辫说,你们谁有小神仙的手艺你就炖去。说得那些人立时噤了声。
狗子回来见屋子里烟气腾腾,便说都窝在这里做啥,出去,出去。人们听了就轰地一声出了院子,按照开会时布置的依次堵住了各家的门。很快,街上就传来了狗吠声、喊打声。到处狗毛乱飞,血腥气直呛人的鼻子。几个信佛的老太太明里不敢对抗革命行动,暗地里便点了香敲着木鱼为狗们超度。正午未到,村里的狗基本上被打净了,只有三喘家的黄大、小灯笼家的米汉和小神仙家的青花没有找到。一个队员说,早晨起来挑水见那三只狗跑进了村南的场院。狗子说,宜将剩勇追穷寇,等打完了这三只再喝庆功酒。打狗队来到了场院很快便把三只狗围住了。青花个头不大,居然性子格外烈,一个立功心切的队员手上先挨了一口,疼得嗷嗷叫起来。别的队员有些着慌,说用枪打吧。狗子说,你们狗日的就知道动枪,一枪下去打成筛子,那狗皮谁还要。人们不想坏了一张上好的狗皮,又怕再被咬一口,就从灶上扯来了小神仙。小神仙来到场院,叫着青花的名字,青花听了极不情愿地走了过来,一下子被绳子套住了脖子顺势吊在枣树上。黄大平11米汉见状奋勇扑了上来。它们拚命的架式让狗子一下子怯了。未等想明白,手里的枪便响了。其他的队员也各自开了枪。黄大和米汉被打成了筛子,被人倒拖了后腿走了。人们怂恿着小神仙往青花肚子里灌水,狗子说勒死的狗一股臊味,已经坏了两张好狗皮不能再坏了一身肉。小神仙怕别人说自己不革命,就硬着头皮去灌水。灌着灌着,青花饱胀的奶子突然喷出了晶莹的奶水,像下了一阵飞雨,溅了小神仙一脸。青花的尾巴一个劲摇着,低低地哀鸣,小神仙一见再也灌不下去了。
“灌呀,心疼这个斋牲了?它咬人的时候你咋不心疼了?”说着,狗子踹了小神仙一脚,自己夺过水瓢狂灌起来。青花的尾巴眼见着摇得越来越慢,嘴里的哀鸣渐渐弱了下去。
“我日恁娘。”一个尖细的声音从背后传了过来。人们注意力都在青花身上,听到骂便齐刷刷回了头。一看是屁孩,手里还拿了块砖头。人们就笑了,不再搭理他。人人都知道屁孩是个睡不着、半哑巴。
“屁孩,你刚才骂啥?”小神仙激动地眼里放了光。
屁孩说,我日恁娘。小神仙一下子抱住屁孩,激动地大声喊起来:屁孩会说话了,他不是半哑巴了。
小神仙不能不激动。自从让三喘吓掉了魂,本以为屁孩再也不会说话了。现在屁孩会说话了,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正常的孩子长大之后自然是个正常的男人。一个正常的男人就能讨上老婆,就能把刘家的香火续上了。
小神仙不顾屁孩的踢打,
一路抱着屁孩跑回了家。院子里,三喘的手被狗血糊满了,给他打下手的两个也是鲜血淋漓。看到黄大时,三喘的手哆嗦了一下。他一下子想起了早晨打过的那只狗。早晨自己那一枪没有把黄大打死,它居然自己跑回来了。三喘问黄大是谁打的。送狗的队员说是狗子亲自打的,你们家黄大倒挺凶,直往人身上扑呢。
三喘知道自己早晨打错了,不知把谁家的狗打了,也许是临村的吧。想到这里,三喘心里哆嗦了一下,手上的动作慢了起来。
下午一点多,雾终于散尽了,村里肮脏的街道显露了出来。因为受到狗子的批评,小神仙开始很认真地炖着狗肉,他把自己这些年做大锅菜的经验全用上了,锅里渐渐的香气四溢。女人们已经抱了孩子挤满了院子。一些孩子等不及在娘的臂弯里睡着了,没有睡的嘴角都流出了涎水。小神仙见女人们都拿着不知从哪里淘来的大碗,像一个个面盆儿。见此,小神仙就又往热气腾腾的锅里加了两大瓢水。
揭开锅,小神仙开始打发女人和孩子们。女人们的盆汤汤水水满满的,知足地走了。男人们就围住锅开始喝酒。狗皮一张张钉在了墙上,淅淅沥沥地淌着血水。男人们边喝酒边说要做狗皮袄,还要做狗皮褥子。人们故意瞅着三喘,不怀好意地道:三喘最需要一床狗皮褥子了。坡里雾气重,当心把胯里那坨玩意儿冻坏了。三喘听了脸刷地红了。他兀自一个人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好像又找回了当年的豪气。很快三喘就醉了。他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该到坡里去了。他指着那些精壮汉子说,都回去搂着老婆睡觉吧,狗肉是大补呢,别把那些热乎劲浪费了。狗子说,这狗日的喝醉了。让他去看坡,不把庄稼看没了才怪。
三喘出门时看见了屁孩,用手去摸屁孩的头。被屁孩一扑愣脑袋躲开了。三喘走后,小神仙端了一大碗狗肉轻声喊道:屁孩,屁孩。屁孩转过身,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肉香,碗里漂着一层厚厚的油花。小神仙催促道:快吃,别让人看见。屁孩端着那碗肉,本来想倒掉,但肉太香了,谁吃过这么一大碗的肉呢。屁孩吃得满嘴流油,把青花黄大米汉全忘记了。
屁孩来到场院边上,那里已经堆了一大堆狗骨头。太阳就要落山了,那堆狗骨头被镀了一层金光变得闪闪发亮。在金光里,屁孩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晃动,一看竟然是青花生的小三。全村的狗只有小三没有死。它大概是躲在窝里睡着了,醒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它肯定是饿了,于是就从窝里走出来。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找到了这堆骨头。它太小了,牙齿嫩嫩的,还没有坚硬到能啃骨头的地步。它用粉红的舌头在骨头上舔着,尾巴不停地摇着。屁孩走过去,把小三吓了一跳。它蜷起身子,尾巴夹进大腿,缩成球状,浑身哆嗦个不停。当看到是屁孩时,小三的身子腾地弹开了。它向屁孩走过来,用力摇着它的小尾巴,用舔过骨头的舌头舔着屁孩的手,舔着舔着就把屁孩的泪舔了出来。
狗子一直对三喘不放心,半夜里带着民兵小分队去坡里查岗。见窝棚里没有一点动静,也没听到三喘咴喽咴喽地拉风箱,狗子就钻进窝棚,见三喘一动不动。狗子说,你个狗日的睡觉咋没声呢。狗子上前踢了一脚,三喘仍没有动静,拿手电筒照了照,狗子“妈呀”叫起来:快来人,狗日的死了。
三喘死了。狗子把刘大收押到了现场。刘大收看了说,他不该吃那么多狗肉喝那么多酒。狗肉是属热的,他一个痨病鬼吃那么多还不要了命。
三喘死的第二天,人们在河边发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女人一只脚光着,身上被鸟枪打成了筛子。她的手里死死攥着一篮子玉米。中午,女人被对岸临河村的人抬走了。他们只是把女人抬走了,一点也没有大闹一场的意思。藏在玉米地里的狗子见状就领着民兵悄悄地撤了。明摆着,她是来偷玉米的,想闹也师出无名。何况三喘已经死了,真闹起来也只能是自讨没趣。
三喘死了自然是埋了。小白鞋哭得鼻涕四流,让人看了真是很伤心的样子。三喘一死,倒是让赤脚医生和小灯笼躲过了开批斗会的命运,保全了面子。他们以后都变得很收敛7NJY8z6mUx8BcPT1jrBSSw==了,成了挺不错的公社社员。程胖子调走后,小白鞋也断了那方面的念想,就像是秋天的雾,被太阳一照全散了,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再以后就是霜降了,雾没有了,每天早晨树上房顶上都结了一层霜,早晨起来觉出了格外的寒意。刘瞎子、丁瘸子这些人也懒得那么早起来。三喘死后,屁孩早晨睡得香梦不断,常常不经意间就笑出声来。小神仙不放心又找了个道行高的人看了看。人家说,屁孩小时候被三喘这一吓,魂没有吓飞而是附在了三喘身上。不然,魂早就收回来了。如今三喘死了,他的魂自然就复位了。高人一番话把小神仙说得口服心服。高人又说,吓掉魂的孩子长大了都会有大出息,这样的孩子格外聪明,不然小小的年纪咋知道害怕呢!小神仙听完点头哈腰千恩万谢,把炖狗肉时藏下的一大块狗肉干送给了高人。
屁孩如今已是不惑之年。他们那个村河水漫了滩,已经统一搬到了坝外。屁孩上学时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一直也没有像那位高人说的有大出息,初中毕业就在镇上开了家肉食店,当了个小老板,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他卖驴肉牛肉羊肉鸡鸭鱼肉,就是不卖狗肉,人们也从来没见他吃过狗肉。不过,屁孩倒是养狗。他养的那条狗又老又丑,皮瘌毛秃,走几步都要喘一喘。太阳出来,那条狗就独自踱到太阳地里晒太阳。有时,它还趴在马路中央,也不怕汽车把它轧死。有好几次,人们都以为它被轧死了,但每次它都回到了肉铺。有时回得太晚,屁孩就会满街筒子喊道:小三,还不回家作啥?那条狗听了就懒洋洋地不知从哪里走了回来。它在街上不紧不慢地晃着,一下子就晃出了米汉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