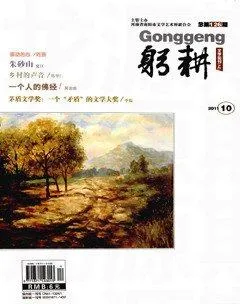驿动的心
1
据说凡是去过涧河的人,都知道一家名叫“驿动的心”的酒吧。这家酒吧,座落在涧河这座县级市的腹地,与北岸商場斜对过,营业时间是每天的上午十点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半。
有那么一段日子,具体说来是2010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这家酒吧刚刚开张那会儿,只要工作不忙的时候,周德东就时常去那坐会儿,要一杯生啤或者咖啡,找个偏一点的座位坐下,耷拉着脑袋,一个人慢慢地喝,挺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其实,如果是守着我们这些朋友的面,周德东是不敢摆出这副带死不活的悲情样子的。我会相对婉转地说,嘿,你们发现没有,咱们这里多了一个流浪歌手,欸?不对,是先锋诗人。老白则会擂周德东一拳,大骂,你装个鸡巴毛深沉?我操!
酒吧老板据说以前是卖鱼的,复姓欧阳,周德东跟他似乎挺熟的。后来,周德东在给我发来的E—mail里告诉我,这家酒吧开业之初的那两个月,除了他和几只异常活泛的苍蝇,通常就一个顾客也没有了。会有哪个生意人开店就是为了赔个底朝天吗?对于这个问题,周德东就是用脚趾头或者头皮屑来想,也会得出否定性的答案,否则他也不会撇下我和老白,大老远跑去涧河开了家影楼。
那段日子,老板欧阳都要瘦成一根稻草了,周德东也跟着着急。可是,周德东很快发现,老板欧阳似乎平静下来了。这个三十三岁的前鱼贩子,备好了一根绳子,正好有两米半那么长。然后,老板欧阳就哼着水唧唧的小曲,开始寻找一棵看起来顺眼一点的歪脖子树。
周德东的E—mail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当时也是闲得难受,就给他回信,问他,后来呢?之后,我又问了周德东一个我有些好奇的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根绳子正好两米半长?
过了大约三四天吧,周德东给我回信了。他说,是一个女子,拯救了欧阳和欧阳的酒吧。就这么一句。应该说,拯救这个词,被周德东使用得很有嚼头,要是用个眼下流行的热词,就是给力。但在当时,周德东却把我惹毛了。这倒不是说我急于知道酒吧的具体经营状况,我是生周德东的气,有什么话痛快说出来就得了呗,有什么值得遮遮掩掩的?
我马上就给周德东打了电话,他却迟迟不接听。我就耐着性子听他的手机彩铃,是一个男歌手在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于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我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唱它的歌手是谁。但我觉得,这首歌起码不难听。这让我先前的火气小了不少。这首彩铃歌曲唱完两遍的时候,周德东接了电话。
我说,德东,我求你件事行不?
周德东说,你客气什么?有什么事,说。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有屁就一下放出来,别零打碎敲行不?
周德东说,我也求你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有屁就一条直线放出来,别拐弯抹角行不?
我就笑了,说,那个女子是怎么拯救了酒吧和酒吧老板?
周德东也笑了,说,这事说来话长。
我说,没事,我刚交完电话费,有多长你说多长。对了对了,我还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那根绳子正好两米半长?就不能是两米四或者两米六?
周德东说,那我先问你,知道我手机彩铃是什么歌不?
我说,不知道。
周德东说,你问老白去吧。
之后,周德东就挂断了电话。我急忙再拨,这个败类死活就是不接,气得我当时都有把他拆巴零碎了拿去喂狗的心思。
2
我就真的去找老白了。老白是我们市名头很响的先锋诗人,还是作家协会的一个什么理事。据说他的代表作是一首长诗,不在二百五十行之上,也不在二百五十行之下,刚好二百五十行,题为《肚脐以下》。其中最短的一行也要二十五个字,江阳韵一韵到底。我没有看过,我也不想看。
除了诗人之外,说来也是有点巧合的,老白也经营着一家酒吧,位于桥旗路中段。老白的酒吧,名字叫第八感觉。我想,只要脑袋没被驴踢过的人,通常是想不出这样的店名的。但别管怎么说吧,老白的酒吧生意很火。这除了因为酒吧出售的洋酒掺水较少,价格也还没有黑得闪闪发亮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老白把这里办得更像艺术沙龙。一群自称是下半身诗派的先锋诗人,每一个半月左右就来这里举行诗歌朗诵会,也有业余模特来这里展示时装秀,还有过气的歌星在这里举行新唱片首发式。诗人、模特和歌星都不来时,就会有夏天穿羊皮袄、冬天光着身子的人,来这里表演行为艺术。
我是写小说的,觉得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应该要比别的地方故事多,所以每隔一段日子,我就来老白的酒吧坐上几个小时,渐渐地就跟老白成了朋友。而周德东呢,是搞摄影的,可能也是觉得这地方能给他带来创作灵感吧,就也常来。我们三个,就这样凑合到了一块,用老白的话来说,三个诸葛亮,怎么也赶上一个臭皮匠了。
这会儿,我来到了老白的第八感觉酒吧,正赶上一位女诗人在这里举行诗歌朗诵会。这个剃了光头的女诗人,竟然把眉毛也剃光了。女诗人朗诵的同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右手举过头顶,然后猛地下挥。台下的二三十位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哨。老白事先准备的几大束玫瑰花,都被这些观众买去送给了女诗人。
而我却听得两颊潮红,一脑门子汗水。我是真的不明白啊,女诗人的诗歌中,蕾丝内裤、席梦思和精液这几个词,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出现。
我就把老白叫到一边,问他,周德东的手机彩铃是什么歌?你最近跟他联系没有?
老白说,有联系。他的彩铃是《驿动的心》,驿站的驿,动荡的动。
我说,第一句是不是:曾经以为我的家是票根?
老白说,对,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整首歌词,也就开头这句有那么点意思,其余的都鸡巴毛不是。
我想笑,但没笑出来。写诗的人瞧不起歌词,这应该不算意外吧。就像我,写中短篇小说,就时常不把小小说放在眼里。这其中没什么深刻又站得住脚的原因可讲,就那么回事吧!我说,周德东可能是抽风,给我发邮件,说涧河有个酒吧,生意不好,后来好像又好了,因为出现了一个女人。
老白说,对,这事他在电话里也跟我讲了。那个酒吧就叫驿动的心,用歌名做店名,一看老板就白痴。
我说,哦。
老白说,说那老板是白痴,我这都是高估了他的智商。你就说吧,他店名叫驿动的心,他却不知道这是首歌名。最要命的是,他以为是移动公司做的什么广告。我操!
毫无疑问,老白的话,又听得我一头雾水。我说,这些都是周德东告诉你的?
老白说,是啊。你以为我像你一样,总把母鸡虚构成凤凰?
3
为了少出现几个老白的口头语,也为了尽可能客观一些吧,接下来,我用我自己的语言,复述一下周德东给老白讲的那些事情。
拯救了欧阳和酒吧的这个女子,是欧阳雇用的一个服务员。女子二十一二岁的样子,长了一双超大的眼睛,有些像日本明星滨崎步。周德东见过她几次,只是知道她姓赵,但没记住她叫赵小单还是叫赵小双。私下里,周德东就管她叫赵滨崎步。
据周德东讲,赵滨崎步也是无意中拯救欧阳的,就是说,瞎猫还真有碰见死耗子的时候。那天,赵滨崎步本来是要向欧阳讨要薪水的,但她想先过渡一下,她就叹了口气说,要是姜育恒能来咱这儿就好了。
欧阳抡起苍蝇拍,啪地一下拍在墙上。那声啪简直光芒四射,但那只苍蝇却四两拨千斤地躲闪开来,它小巧玲珑的身体,在空气中划出了一组轻盈的嗡嗡叫的曲线。之后,欧阳说,姜什么什么恒,是谁?
赵滨崎步就将黑眼仁上翻,做出一副就要晕倒的样子。她说,姜育恒!姜育恒是谁你都不知道!台湾歌星,嗷嗷有名,不过这几年看不到他了。
欧阳的目光从赵滨崎步的脸上移开,重新寻找那只苍蝇的下落。
赵滨崎步接着说,咱们酒吧叫驿动的心,姜育恒的成名歌曲也叫《驿动的心》。之后,她就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
紧攥着苍蝇拍,欧阳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傻了。这首歌,欧阳以前的确听过,但直到现在他才知道歌名叫《驿动的心》,与他的酒吧店名一字不差。在这之前,欧阳一直以为歌名叫《移动的心》,是给移动通讯做的广告。
欧阳就死盯着赵滨崎步。足有两分钟后,他猛地拍了下大腿,指代不明地骂了句,他奶奶的。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欧阳锁上了酒吧的大门,只让两个服务员站在酒吧的大门外。凡是想进酒吧消费的顾客,都被她们挡在了门外。对不起先生(女士),我们这儿今天顾客爆满。一个服务员说。另一个服务员说,欢迎您明天早点惠顾我店。
这三天中,有一次周德东来找欧阳,同样被那两个服务员挡在了门外。周德东隐约听见里面传来了歌声、掌声、喝彩声和口哨声,他就来到窗前。可玻璃是透明性差的茶色玻璃,里面又严严实实地挡了一层厚厚的窗帘。周德东不知道欧阳的酒吧里面发生了什么,就回家看电视去了。周德东看的是一家外省卫视的一档现場直播综艺节目,姜育恒演唱了《再回首》和《女人的选择》这两首歌。
三天后,涧河市起码有百分之八十的市民都知道著名歌星姜育恒来过了,在一家名叫驿动的心这么个酒吧,演唱了他的同名成名曲和最新专辑中的主打歌。凡是在那三天中去了该酒吧的顾客,都得到了姜育恒的签名照片。而另外一些市民还获得了幕后新闻,比如涧河是姜育恒的原籍,北涧头村老彭家或老李家的房子,要是上溯到嘉庆年问,那可是姜育恒家的牛圈;比如驿动的心这个酒吧,其真正老板就是姜育恒本人;而在《驿动的心》这首歌中,姜育恒实际表达的是他对原籍的真切怀恋,等等。
周德东听到这些时,就忍不住笑了。他急忙打电话给老白,说,老白啊,人家欧阳的酒吧,比你的酒吧火多了,火得欧阳和赵滨崎步在休息间里都穿不住衣服了。老白说,我操,这招真他妈的高……
给我讲完这些后,老白问我,最近这几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诗人没有?
我说,我不清楚,好像是穆勒吧。
老白说,等哪天我这里生意不好,我就把这个老穆请来,保准比请歌星有效果。
我笑了笑,刚要说话,那个女诗人走下台来,坐在了老白的大腿上。她在老白的脸颊上很响地亲了一下,然后对我说,Oh,my god!老白则对我耸了下肩膀,同时摊了一下双手。
我知道我该离开了,就抓紧时间问老白,周德东跟你说没说,那个欧阳准备过一根绳子,不长不短,正好两米半那么长?
老白拍了拍女诗人的屁股,说,我操,老周那是说了句形象化的语言,意思就是那个白痴老板赔得想自杀。
我恍然大悟,之后就笑着离开了老白的酒吧。这个时候,老白一定没有想到,被他一再称之为白痴的欧阳,不久之后就要跟他有一些瓜葛了。当然,这个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4
老实说,离开老白酒吧之后的很多天里,有几个问题还是在我心里纠结着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在前面说过我是写中短篇小说的。可实际情况是,写小说不能让我吃饱饭,所以我还有个职业,在一家小报做记者。做新闻首要的一点就是得较真,所谓用事实说话。
我就觉得,有几个问题其实是应该再推敲一番的。比如,欧阳曾经听过《驿动的心》这首歌却不知道歌名这件事,周德东是怎么知道的?再比如,欧阳和赵滨崎步在休息间里穿不住衣服,是周德东亲眼所见吗?
在之后的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络中,我没问周德东这些问题。但是,我问了欧阳酒吧店名的由来。周德东说,店名是欧阳当初花钱请一个算卦瞎子取的。欧阳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瞎子就说“驿动的心”这四个字中,饱含着无数重美好的寓意。瞎子引经据典、口吐白沫地解释了十好几分钟,欧阳只听懂了其中的一点:叫了这个店名,他就一定发财。
周德东还告诉我,我上次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听,是因为他正和欧阳、赵滨崎步在一起,说话不太方便。他说他当时正跟欧阳商量呢,要以赵滨崎步为模特,拍一组照片,准备参加一个什么摄影展。我问周德东,照片拍得怎么样?周德东说,别提了,没拍成。之后,周德东就挂断了电话。
时间转眼就到了201 0年的7月,我又给周德东打了电话。一来是我想问问他,到底因为什么没能给赵滨崎步拍照;二来呢,我刚刚采访完我们市的高考状元,我想问问周德东,稿子怎么写才能更有一点新意,毕竟他当初是我们市的高考文科状元,大学里学的还是新闻。
可我没想到,周德东的手机停机了。我发了电子邮件,又在QQ上留言,他都没有回复。
我就急忙去找老白。老白说,我也挺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那小子十有八九是跟一个叫什么赵小双的女孩子私奔了。
我说,你别开玩笑。
老白说,我没开玩笑。
老白接下来告诉了我周德东可能私奔的理由,我当然不相信。可是,到了2010年8月初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叫肖黑的男人。我就真的相信,老白没有骗我,周德东真的是跟一个叫赵小双的女孩子私奔了,起码是他们二人同时没了下落。至于这个肖黑到底是谁,我过一会儿一定会讲到的。我还是先讲一下周德东私奔或者失踪的过程吧。
当然,我必须说明的是,周德东私奔或者失踪的过程,我是从老白和肖黑的讲述整理出来的,其间掺杂了少量我的想象。
5
我想,应该是2010年6月最后那个周六的早上,吃过早饭,周德东想给欧阳打电话。
因为近来影楼生意很忙,周德东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去欧阳的酒吧了,他想问候欧阳一声。但欧阳的手机已停机。周德东就想往酒吧打电话,但考虑到欧阳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此时应该是正在睡觉,他就没打电话,想吃过午饭后直接去酒吧看欧阳。周德东就把手机放回包里,随手打开了电视机。
赵小双就是在这个时候,敲响了周德东的房门。三下很轻的叩击传来时,周德东以为是有人在敲他家对门的房门呢,但他还是用遥控器减了电视机的音量。
周德东先生在家吗?赵小双在门外大声说了句。
周德东就来到门前,隔门问,谁呀?
赵小双说,我,赵小双。
周德东想不起赵小双是谁,赵小双的声音他也是陌生的。他就又问了句,谁?
赵小双说,我是赵小单的妹妹。
我的朋友周德东也没想起赵小单是谁,他就没有开门。
赵小双接着说,欧阳,驿动的心老板欧阳,是……
赵小双说到这儿就停了下来。周德东就一下子想起了赵滨崎步。他想,这个赵小双应该就是赵滨崎步的妹妹了,而赵滨崎步的原名原来是赵小单。可是周德东实在想不出赵小双为什么要来找他,他和她以往可是没有任何往来的,他和她姐姐赵小单也只是在酒吧见面时打个招呼而已。
周德东就有些犹豫地打开了房门,嘿!赵小双果然跟赵小单长得很像。
我姐在哪儿?在沙发上坐下之后,赵小双一脸焦急地问周德东。
周德东就点愣住了,张了张嘴巴,没说出什么话语来,就顺手用遥控器将电视机关掉。
赵小双接着问,我姐和欧阳现在在哪儿?
周德东挠了挠后脑勺,他说,在酒吧呀。
没有什么过渡,赵小双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说,我去过了,酒吧十天前就兑给别人了。这半个月,我天天在找我姐,让她回家。我妈病了,想看看她。一开始,我打电话,她还接,她总说明天就回家,明天就回家。后来我再打,她就不接了,总关机。我就去酒吧了,才知道酒吧兑出去了,我姐和那个欧阳也不见了。
周德东就去洗手间给赵小双拿了条毛巾,递给她让她擦擦眼泪。
欧阳和赵小单眉来眼去的,人前人后都板不住搞点小动作,这些周德东都知道。周德东本来以为欧阳和赵小单在一起只是玩玩,一場游戏而已,当不得真的。而听了赵小双的话后,周德东知道欧阳这是动真格的了,闹着玩下了死手。
周德东说,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姐和欧阳那个,那个不见了,你找我又有什么用呢?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
赵小双止住抽泣,她说,我姐上次回家时跟我提到过你,她说你说她长得像滨崎步。
周德东说,你家不在涧河吗?
赵小双点头,说,嗯,我家在河滨镇。我姐说你和欧阳是最好的朋友,你一定知道他们俩现在在哪儿。
周德东就点了根烟,说,其实我和欧阳也有一个多月没联系了。你敲门的前几分钟我正给他打电话,他手机停机。
赵小双说,也给我一支烟行吗?
我的朋友周德东递给她一支烟,帮她点着,又把烟灰缸往她那边推了推。
抽了一口烟,赵小双就笑了,说,你好厉害呀!我随便在大街上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认识你,说你照片拍得可好了。
6
故事讲到这儿,我想插进一小段基本没用的文字。
我记得我在前面说过,周德东是个摄影师,去涧河开了一家影楼。应该说,周德东的拍照水准还是说得过去的。有一次,《涧河晨报》一个记者的相机坏了,这个记者就带着周德东一道去采访。周德东到那儿,随随便便地拍了三张照片。结果这三张照片,竟然在年度全省新闻评选中得了最佳新闻图片奖,为《涧河晨报》实现了零的突破。有关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明星照》,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翻翻,没兴趣就算了。
被赵小双夸奖照片拍得好,周德东觉得挺受用。他笑了笑说,那些人可能都是我顾客。
赵小双说,我就这么找到你家了。以后你也给我拍几张照片呗,我觉得我比我姐漂亮。
周德东含糊地说,行。
赵小双用两个手掌支着下颏,眼睛看着墙壁上周德东妻子的照片,说,你妻子好漂亮。
周德东说,行。然后他看了看表,九点五十分了。
赵小双突然就用手拍了下周德东的头,说,你总行,行,行什么呀?你妻子怎么没在家?
周德东的脸就红了,说,她去省城参加面授。你先别急,我给欧阳家打个电话。
赵小双的脸色,看上去就又焦急和沉痛了,她说,好吧。
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周德东说,可能他家没人。
赵小双说,那我怎么办?
周德东被问住了。这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而他又不想给自己找什么麻烦。他说,我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我还能帮你的,就是把欧阳家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你,你自己去找。
赵小双说,好吧。她的眼里又有了泪水,接过写有欧阳住址和电话的纸条往外走。
周德东说,我送送你。
赵小双孩子似地噘着嘴巴说,不用。
但周德东还是替她打开门,跟在她后面出了房门。
赵小双头也不回地往楼下走。
周德东说,再见。
话音刚落,赵小双突然脚下一滑,跌倒,滚下楼梯。
周德东急忙跑过去扶起她。怎么样?摔坏没?他问。
赵小双就紧紧抓住周德东的手,她哭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能是太饿了。从昨天到现在,我一口饭也没吃。我的手是不是很热?我病了。
周德东试着抽回自己的手,但没抽回。他说,为什么不吃饭?
赵小双说,找我姐找的,钱都花没了。
这时候,住在周德东家对门的肖黑,正要去菜市場买菜。肖黑刚一出门,看到周德东和一个女人拥抱着,他就又轻轻退回屋里,轻轻带上门。在门关上的同时,肖黑听到周德东无限怜爱地说了句,你呀!然后,肖黑从“猫眼”中看到,周德东扶着那个女孩子下了楼。
肖黑是没有跟踪周德东和赵小双的兴致的,但因为菜市場和驿动的心酒吧在同一条街上,肖黑就只能跟在周德东和赵小双的身后。周德东和赵小双进了酒吧,肖黑才发现,这酒吧怎么改了名字?原来不是叫“驿动的心”吗?如今怎么改成了“移动的心”?紧接着,肖黑看到周德东和赵小双又走出了酒吧,周德东的手里,多了一条白色的尼龙绳子,长度应该是在两米半左右。肖黑没心思管这些闲事,就进了菜市場。
这之后,周德东和赵小双就没了消息。
而我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德东曾经在电话里跟老白这样抱怨,欧阳长得跟块猪头肉似的,赵小单怎么就能相中他呢?老白当时说,相中你还差不多是不?周德东说,那是。
7
很遗憾,故事到此没有结束。
2010年的第一場雪飘落下来的时候,从前住在周德东家对门的肖黑,搬到我所生活的城市来了,而且跟老白家做了对门。我就是这样通过老白认识了肖黑。老白又说了那句话,咱们三个诸葛亮,怎么也赶上一个臭皮匠了。
2010年的第一場雪下得有些不靠谱,竟然整整下了三天三夜。雪停下来的时候,一个自称叫赵小三的大眼睛女子,来到老白的第八感觉酒吧。当时,我和肖黑也都在場。对了,在場的还有那个剃光了头发和眉毛的女诗人。按计划,老白和女诗人的婚礼,将在半个月后举行。
赵小三一进来,肖黑就悄悄告诉我,这个女子,跟去找周德东的那个女子,长得一模一样。我一愣,还没缓过神来,就听赵小三在问老白,你是白先生吧?你认识周德东吧?
老白说,我姓白,我认识周德东。他去涧河了,我们和他已经有半年没联系了。
赵小三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差点瘫倒在地上。
赵小三说,是这样的,我大姐的男朋友——我叫他欧阳大哥,欧阳大哥和周德东关系也不错。我欧阳大哥让我二姐去找周德东,来酒吧小聚一下,可周德东把我二姐拐跑了。
老白一拍大腿说,我操!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我,你找我有什么用?我有什么办法?
赵小三说,我知道你和周德东关系特别铁,你保准知道我二姐和周德东现在在哪儿。
紧接着,赵小三的眼泪唰唰唰地流了下来。她说,我妈病了,特别想见我二姐。
我、肖黑和老白都沉默了。只有女诗人把右手举过头顶,猛地下挥,同时大声说,Oh,mygod!Oh,my god!作为老白和周德东的朋友,我是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离开的,但我又不得不离开。因为我采写的一个稿子,出现了很严重的失实,总编咆哮着命令我马上赶回报社。
稿件事件平息下来,已是三天之后了。我匆忙赶到老白的酒吧,却发现酒吧改了名字,不再叫“第八感觉”,而是更名为“黑白两道”。
我一进酒吧,就看到女诗人在哭,肖黑正在安慰她。
我问,店名怎么改了?
肖黑说,啊,老白把酒吧兑给我了。
我说,老白呢?
肖黑用右手轻轻拍着女诗人的后背,说,他跟赵小三一起不见了。
肖黑说这句话时,女诗人的哭声,火苗子一样蹿高了一大截。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
肖黑说,哦对了,我才想起来,老白让我把一个东西送给你。他边说边走向吧台,从那里取出一条白色的尼龙绳子,不由分说地塞进我的手里。
我跟肖黑要了一把尺子,认真地量了三次,每次都是两米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