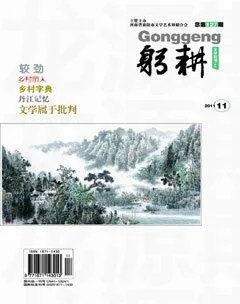伤痛歌乐山
伴着深秋的冷寂,我随旅游团来到“雾都”重庆,走进了歌乐山红色景区,瞻仰了红岩魂广场、白公馆和渣滓洞革命烈士纪念馆。这素有“渝西第一峰”美称的歌乐山,它秀美的山水,没有让我愉悦;它旖旎的风光,没有让我“歌乐”。伤心,伤心,难以言表的伤心;流泪,流泪,抑制不住的流泪——歌乐山,这就是我首次游历你之后的全部感受。
红岩烈士陵园区,一派肃穆。二胡伴奏的女生独唱《红梅赞》单曲播放,回肠荡气——“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尊尊花岗岩烈士雕塑,铁骨铮铮,栩栩如生;一座座复斗型的坟墓,安葬着烈士忠骨;一块块长方形墓碑,铭刻着烈士英名。那目不暇视的碑林诗文,集合着烈士们的遗志遗愿。云雾在苍松翠柏间缭绕,这是烈士不散的冤魂;溪流在山间呜咽着流淌,那是为英灵吟唱的挽歌。白公馆监狱、渣滓洞监狱、蒋家院囚室、黄家院囚室、杨家山囚室、松林坡刑场、步云桥刑场、电台岚垭刑场,阴森恐怖。
长箫伴唱的女声《绣红旗》,反复吟唱,如泣如诉——“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多少年呀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你,盼到你……”在凄美的歌声中,我参观了监舍地牢,找到了小说《红岩》与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故事发生地;目睹了烈士遗照遗物,见到了小说和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原型”。在凝重的氛围中,在沉重的步履中,我走遍了纪念馆的角角落落,走进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
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禁锢世界。在抗日救国如火如荼的年代,在民主自由风起云涌的岁月,“军统”特务在歌乐山麓,用高墙、电网、岗楼、刀枪圈起一个从杨公桥到磁器口,方圆十余里的神秘“特区”。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禁区”,专门关押、迫害、屠杀“抗日分子”、“民主斗士”,从事祸国殃民的卑鄙活动。1941年春,四川绵阳国立六中三分校学生冯鸿珊、陈河镇、李仲达、石作圣,身带进步书籍,从重庆出发去鄂豫边界的解放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途经磁器口时,被特务检查出“禁书”而被捕,先关押于贵州息烽监狱,后转至白公馆监狱,关押八年,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这是丧尽天良的罪恶行径,这是令人发指的现代版“焚书坑儒”!
这里有臭名昭著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这里蚊如雷,蝇成群。灯光暗,暑气蒸。“囚徒”们吃的是三多饭(沙子多稗子多老鼠屎多),睡的是一脚半(极拥挤),穿的是叉叉服(囚服)。这里的黑牢,关押过著名烈士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陈然、许晓轩、王朴、江竹筠、蔡梦慰……关押过天真可爱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流浪儿“蒲小路”、“监狱之花”卓娅。白公馆,你“黑牢”的本质,完全消弥了你原名“香山别墅”的盎然诗意!你地狱般的生活,彻底辜负了你“山泉流淌,翠霭浓浓”的优美环境。渣滓洞,你的命运似乎蒙着与生俱来的悲剧色彩——首任矿主为实业救国而开矿采煤,终因渣多煤少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继任矿主励精图治使矿业中兴,却因军统特务霸矿占房而上吊自尽。从此,你与白公馆双双沦为“活棺材”,联手装殓一个悲剧世界。“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禁锢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空气呵、日光呵、水呵……成为有限度的给予。人,被当作畜牲,长年地关在阴湿的小屋里……”——这就是“黑牢”地狱般的生活。这里的“囚室”,囚禁过:北伐名将叶挺,“西安事变”历史功臣杨虎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但局促的“囚室”,囚得了志士的“身”,囚不住志士飞向自由天地的“心”,囚不住先驱追求正义的冲天豪情!
这里是一个烈火中永生的熔炉。这里有恐怖阴森的刑讯室和刑讯洞,这里有毛骨悚然的刑架与刑具,这里有残暴变态的四十八种刑罚。然而,为了“把颠倒的乾坤扭转,把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为了“千万对情侣不被拆散,万千个孩子不再失掉爹妈,穷人翻身不再做牛马”——寒门子弟车耀先走来了,富家公子刘国鋕走来了;工人之子余祖胜走来了,富商之子何柏梁走来了;放牛娃陈作仪走来了,童工江竹筠走来了;“书香门第”的王白与走来了,官僚家庭的罗广斌走来了;市长侄女杨汉秀走来了,社会贤达王朴走来了;“人民的歌手”古承铄走来了,诗人蔡梦慰走来了;著名教授罗世文走来了,“五四”精英黎又霖走来了;《西安日报》编辑宋绮云走来了,《和平日报》记者钟奇走来了;东北军将军黄显生走来了,“中央监察委员”薛传道走来了……
他们“走”的泰然自若,“来”的义无反顾。在这里,志士们“宁关不屈”,拒不“认错悔过”,更不“声明脱党”,把诱惑的“金子”扔进粪堆里,把可耻的“红顶花翎”用脚踢开,一任皮鞭打得肉烂,烙铁烧得皮焦,竹签扎穿十指,“老虎凳”折断筋骨,电流通过全身……惨绝人寰的毒刑,花样百般的摧残,撬不开一张嘴巴,得不到一句口实。志士们用自己的至疼,护住组织的“安全线”,守住战友的“生命线”,“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炼成钢的熔炉,琢成玉的磨床。”“集中营”灰色的院墙上“迷津无边,回头是岸”的劝告,形同虚写;血腥弥漫的刑讯室里,“天下为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联语,讽刺绝妙。在这里,烈士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愿把“牢底坐穿”;从容地走向刑场,像去赴一个神圣的约会。在敌人的刑场上,烈士们昂首挺胸,直面枪口,高呼口号,视死如归。这样的“死刑犯”,多么慷慨!这样的刑场,何等悲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慷慨”,这样的“悲壮”?我徜徉于烈士诗文碑林,浅读低吟,猜想着谜底,寻找着答案。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由,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是陈然烈士向敌人递交的“自白书”,何等坚强!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深知道:
人的身躯哪能由狗洞爬出!
……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是叶挺将军创作的《囚歌》,何等豪迈!
“同志们,听吧!
像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
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
我们死而无憾!”
——这是刘国鋕先驱抒写的《就义诗》,何等激昂!
这些碑刻的诗篇,不是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温馨书斋里的闲情逸致,装腔作势的无病呻吟,而是淬火加钢的铿锵誓言,气冲霄汉的战斗檄文,可歌可泣的壮士长吟!
这是一块令人肃然起敬的革命圣地。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在这里残酷较量;残暴和善良,坚强和懦弱,光荣和耻辱,在这里殊死博弈。
渣滓洞里的难友们组织了“铁窗诗社”,坐对铁窗吐笔花,倾诉蔑视敌人、渴望胜利、热爱自由的炽热情怀——“独夫梦想成秦霸,壮士从容作楚囚”、“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绞刑架上心不跳,断头台上色不变”、“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越狱脱险成功日,神州开遍自由花”、“我爱花,我爱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花,带着霜露迎接朝霞”……这是何等壮丽的诗篇,何等横溢的才华!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捷报,传入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欣喜若狂,利用1949年大年初一“大放风”之机,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春节大联欢”。难友们用稀粥在零星草纸上写成“春联”,贴在牢房门口,一语双关地表达了乐观和喜悦之情——“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放风坝上,男“囚徒”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翻起了“空心筋斗”,叠起了“罗汉”;女“囚犯”们载歌载舞,边唱“二月里来是新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边扭着秧歌舞。——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何等博大的情怀?
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7日,喜讯传入白公馆监狱。难友们兴奋得像孩子见到了久别的爹娘,彻夜难眠。新中国诞生了,牢底就要坐穿了!在罗广斌提议下,陈然、刘国鋕、丁地平、王朴等同志,用铁片作剪刀,以红被面和白衬衣为布料,用剩饭做浆糊,制成一面“五星红旗”,决定“先把它藏起来,在解放大军来了那天,洒着自由的眼泪,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这是怎样的赤诚,何等的期待!后来除罗广斌等极少数难友侥幸脱险外,绝大部分难友“光荣”了,未能等到他们望眼欲穿的“那天”!未能打着狱中自制的五星红旗冲出牢门。解放,与先驱们擦肩而过;胜利,和烈士们失之交臂!这是何等的遗憾,怎样的悲哀!
在重庆解放的炮声日益迫近的时候,敌人困兽犹斗,紧张策划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难友们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起对地下党斗争时期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回顾总结,形成了纯洁党组织、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八条意见”。大家相互嘱托:谁能有机会活着出去,一定要把它报告给党组织。“11·27”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罗广斌同志,在重庆解放后不久即以书面形式将“八条意见”交给了党组织。这是浸淫着血与泪的烈士遗嘱,多么沉重!这是凝结着信念和忠诚的先驱们的“最后寄语”,何等珍贵!
这是一处中华民族永远的“疼”。这里有我和我的民族永志不忘的“时间”——1949年9月6日,10月28日,11月14日,11月27日,在这些时间,多少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永别了祖国。这里有我和我的祖国永久颤栗的地点——松林坡,大坪,步云桥,电台岚垭,白公馆,渣滓洞。在这些地点,多少朝霞般靓丽的九州才俊,诀别了战友。这些永不磨灭的时间与地点,让我和我的人民伤心不已,隐疼不休。
歌乐山,有257位革命志士牺牲在你凄凉的土地上。你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悲壮;你的一草一木,都见证着血火。这里的“黑牢”与“囚室”,是特殊的“第二战线”,与外面刀兵相见的“火线”遥相呼应,彼此召唤。难友们“像笼中的鹰,梳理着它的羽翼,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当来自火线上的人传来捷音时,放风场上的每一双眼睛都“放着亮”,每一个脸颊都“发着光”。“二百多个人只希望着有那么一天——等待着自己的弟兄,用枪托来把牢门砸开!”尽管这里的“囚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牺牲殆尽,但那“永不泯灭的忠魂,在青翠的歌乐山巅,仰望黎明”!这是怎样的人世悲剧!又是怎样的世间壮举!
我不敢正视“小萝卜头”宋振中系着红领巾的雕塑,因为它会让我流泪不止。
宋振中啊,你一生中只留下一张婴儿照片。从这张照片上看,你胖乎乎的,两眼炯炯有神,多么可爱!可你生不逢时,长不逢地,拥有最苦难的童年,遭遇了最悲惨的人生结局。年仅8个月,你就与父母一起过着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你脱了相,变成了头大身小的“萝卜头”模样。这扭曲了的体形,丝毫无损于你的可爱……你多么盼望出狱,过上平民百姓的生活啊!多么渴望在狱外快乐地读书、自由地玩耍啊!这本是一个儿童最基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可是,“小萝卜头”啊,你竟没有这样的“福气”——在你9岁的时候,在松林坡刑场,在你“我没有罪,放我出去”的挣扎声中,十恶不赦的刽子手残忍地杀害了你和你的父母!临死时,你的小手里还紧攥着那只红蓝铅笔头!“小萝卜头”,你究竟犯了什么罪,遭此灾难与毒手?这是怎样的人生苦难!怎样的人世罪恶!
我不敢阅读江竹筠烈士的遗书,因为它会让我痛心不已。江竹筠,你就是那位人人敬佩的“江姐”,就是丹娘的化身,苏菲亚的精灵,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你的丈夫彭咏梧烈士牺牲之后,在一岁半的孩子彭云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你毅然决然重返川东,去到了丈夫牺牲的地方,全力为党工作。被捕后,你在夹竹筷、老虎凳等酷刑折磨下,昏死三次,坚不吐实,不喊疼,不流泪,表现得那样坚强;而在狱中看到日夜思念的云儿的照片时,竟声泪俱下,不断地热吻儿子照片,又显得那样“脆弱”。在赴向台岚垭的途中,你把云儿的照片紧贴胸口,从容就义!江姐走了,留下了这样的遗书:“竹安弟,假如我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是怎样的爱子之情!怎样的报国之志!
怕心酸,我不敢朗诵“铁窗诗人”蔡梦慰写给母亲的遗诗——
妈呀,你在哪里?
我听得见你在悲叹,
你在呼唤我的乳名,
千遍,万遍……
像幼鸟翱翔天际,
飞向太阳……
像雨点滴入江河,
奔向大海……
你的孩子呀,
属于他的伙伴,
属于一个众人的理想。
一个时代的毁灭,
一个时代的诞生,
要付出多少母亲的眼泪,
要经过多少母亲的煎熬……
妈呀,我们两个生命
原本是紧紧地
相依,相偎……
连系在两颗心间的纽带呀,
牢牢地谁能割断?
这是怎样眷恋的母子之情!这是何等浓厚的爱国之情!
怕失声,我不敢回忆烈士王振华、黎洁霜一家四人临刑的场景。这是一对革命的伴侣,英雄的夫妻。为了抗日救国,王振华串联同学去“南京请愿”,被北大开除学籍;黎洁霜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广西第一届学生军,加入抗日队伍。在共同的人生道路上,两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人相识相爱。后来,二人双双被捕,关押于白公馆。狱中,二人坚贞不屈,相互鼓励,相互关爱,纯洁的爱情经受了铁窗考验,于1946年在狱中结为革命伉俪,先后生下“小华”、“幼华”两个孩子。在“天快亮的行凶”中,夫妻二人各抱一个幼子,在凛冽寒风中走向松林坡刑场。临难之际,两位从未向敌人求过情的志士,屈尊向刽子手求情:“把娃娃留下,多打我们几枪。”这是天然的亲情,不可非议;这是人性的光芒,无法遮蔽。“一个不留,斩草除根”——刽子手冷酷地拒绝了他们天经地义的请求。在凄厉的枪声中,志士全家四口人无一幸免,鲜血染红松林坡。这是怎样的蛇蝎心肠!这是何等的穷凶极恶!
怕惊心,我不敢翻阅黄显生将军留在白公馆小桌上的那本台历。时光如水般流逝,而这本台历却永远翻停在1949年11月27日。这位在“九·一八”事变中拍案而起,驰骋抗日疆场,立志马革裹尸、报效祖国的名将,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中,却遭到了“军统”特务的暗算;这位落难白公馆,但“虎入笼中威不倒”的英雄,却在“11·27”大屠杀中,第一个血洒步云桥。这多么令人痛心与怨恨!
怕动魄,我不敢触摸白公馆放风坝上那棵石榴树。六十年前,许晓轩烈士亲手栽种了它;现在,它依旧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而许晓轩烈士,这位曾在息烽监狱核桃树上刻下“先忧后乐”四字的热血青年,这位曾从白公馆“黑牢”中捎给家人“宁关不屈”字条的铮铮硬汉,却在33岁的韶华年纪上永别了亲人和战友,永别了他寄予深情的石榴树。这多么叫人难心和愤怒!
歌乐山,理想信念撑起你一峰独秀的雄姿,烈士鲜血浇聚起你令人景仰的高度,悲壮惨烈叠加成你铭心刻骨的记忆,“黑牢诗篇”昭示你光照千秋的“红岩”魂魄!歌乐山,你红色的景区,是驰名中外的旅游品牌;你红色的经典,是中华儿女采之不尽的精神富矿;你红色的遗产,是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殷实家底;你红色的记忆,是华夏民族披荆斩棘的不竭动力;你红色的故事,会被传说千秋万代;你红色的文化,将被传承地久天长!
在胜利了的今天,“军统”特务们罄竹难书的血债,是否都已清偿?被隆冬红梅所唤醒的百花,是否都放着清香?烈士鲜血染红的国旗,是否依然鲜艳如初、纤尘不染?明窗净几的书房里,我们是否依旧阅读小说《红岩》?那烈士们临终前的“八条意见”,是否被组织采纳落实?清明节里,我们是否去烈士墓前烧纸敬香?在和平着的现在,我们安居乐业,是否“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沙漠耕种成美丽的园林?”是否有党员未经“酷刑”,就叛党变节、放弃信仰?在尽享子女绕膝之乐之际,我们是否去安抚了烈士的后人?
歌乐山,你以红色的处方,医治着醉生梦死群体中流行的“精神贫血”病;你以心灵的鸡汤,缓解着大变革年代伴生的“信仰危机”症。歌乐山啊,歌乐山!我走进了你的腹腔,感受了你彻骨的伤痛;你走进了我的心里,让我体验了无尽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