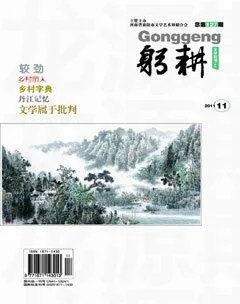丹江记忆
十年前,应文友海明之邀,去丹江岸边游玩。想象中的丹江,应该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那水天相连的地方,白帆点点,轻轻飘荡,不远的江面之上,鸥鹭轻飞,低吟浅唱,站于江边,惊涛拍岸,雪浪滚滚。但真的到了丹江,它却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时值深秋,天气本该是凉爽的,可那年恰逢百年不遇的干旱,长时间未曾落雨,“秋老虎”十分凶猛,热气一浪高过一浪,让我们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张大了嘴巴,大声喊热。路上,所有班车的空调好像都坏了,不制冷,我们不停地冒汗,手抱矿泉水不停地狂饮。
车快到海明的家香花镇附近时,窗外的景色让人为之一振,颇感迷惑。田野里、丘陵上,到处是红彤彤的,分外夺目,望不到边际,并且车前车后,车左车右,如影随形,长时间不能摆脱,汽车仿佛潜游在红色的海洋里。我误认为是它们月季花,便暗暗感叹:哎呦,有这么多的月季花呀!待走近它们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月季花呀!它们是辣椒!成熟的辣椒!火红的辣椒!那些稠密的辣椒角,三个一束,五个一簇,举向空中,成为一束束烛烧的火把,红透了丹江岸边,和丹江的沉稳凝重形成强烈的反差,撼人心魄。
海明住在一个叫刘楼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十分另类,我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村庄。它和丹江仅一岭之隔,站在刘楼的房顶上,丹江便一览无余。海明介绍,丹江暴涨的时候,江水距坡岭最多也就五六丈,于坡岭上就可钓到丹江鱼。我诧异:离丹江这么近不危险?海明说,自打他记事起,丹江水从没翻过岭,住惯了,也不觉得危险。
丹江岸边的这个村子,什么样子呢?没去过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整个村子的房子大致可分为两类:砖房和泥房。先说砖房。那些建房用的砖头大多是灰蓝色的烂砖、破砖,小的有拳头那么大,大的半尺有余。这些砖头比现在的砖头要簿一些,但比较宽大,砖上装饰有花纹,以横竖纹较多,看起来十分古朴。我略通些文物知识,我敢保证这绝不是现代生产的砖头,细看像汉砖。用这样的砖头建房的人家很多,大致有一少半人家吧!若真要是汉砖的话,这些人家都是住在了文物里,那真是一大奇观。
再说泥屋。要说他们的村庄建在黄土岗上,盖房应该就地取材用黄泥,可偏偏不是这样,他们盖房用的是青泥或者叫乌泥,建筑方法与常见的建筑方法大有不同。农村土房的建造通常是用打墙板打墙,打出来的墙看上去一层一层的,但他们建起来的土墙却浑然一体,分不出层次。更奇特的是,那墙上遍布着草根,墙体被风雨冲刷后,那些草根就裸露出来,形成了一张厚厚实实的大网,看起来俨然成了一堵草墙。那些房屋已经有些年月了,墙体龟裂开来,裂纹纵横交错,有些裂纹甚至上下贯通,摇摇欲坠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整个村庄并没有发现有一座倒塌的。这样奇特的村庄,算我孤陋寡闻,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干旱,丹江水一退二三里,让我们和丹江相会的庄严时刻,整整推迟了近一个钟头。想象中,我们见到丹江应该是激情澎湃振臂欢呼的,可丹江真的出现在面前,心中不仅没有澎湃起来,反而生出些许隐隐的遗憾。那魂牵梦绕的丹江,那博大雄浑的丹江,那闻名天下的丹江,只能从它辽远空旷的江面,想象它昨日的风采。眼前的丹江已经不能称之为江了,成了一条漫不经心的河流。宽阔的河面上,形状各异的沙洲,把江水切割得支离破碎、丝丝缕缕,河水在宽阔的河面上走笔一样恣意挥洒,龙飞凤舞。沙洲上水鸟轻盈地漫步舞蹈,水流闪动着碎银般的光芒,尽显其婉约阴柔之美。俗话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这样的丹江也算别有况味吧。我的丹江之行,竟有如此多的意料之外。
我们走在丹江的河床上,满眼都是龟裂开来的淤泥,像一个蹩脚的渔人撒开了一张大网。鱼网尽数落在河岸上,网中没有鱼虾,有的是青翠的蒿草,肥嫩的草叶和纠缠在一起的藤蔓植物。随着我们的不断深入,河滩上茂盛的植物也逐渐的稀疏起来,稀疏成星星点点。河床变得富有弹性,走在上面,像走在棉花堆上面,用不上力气。河床的颜色也有浅变深,一直变成乌黑的胶泥。这里的植物已经很少了,但有一种植物却大放异彩。它们是一种匐匍于地的蔓生植物,藤蔓从圆心开始,呈放射状向四周生长,蔓间有节,每节寸长,且节间生有根须,叶儿是更为细碎的条形。看得出来,它们在此落户时间不长,当初极可能只是飘于河面上的一段草根,一旦上岸,它们紧紧把握住难得的生长机会,迅速扎下根来,开始了它们蓬蓬勃勃的生命航程。那绿色就像造物主饱蘸生命的颜料,不经意滴落于清水之中,迅速扩散开来,形成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绿太阳,散射着无比蓬勃的绿色光芒,灼烧着过往的目光。放眼望去,乌黑的泥地上,盛开着一朵又一朵这样的生命之花。我知道这种植物叫葛巴皮,葛巴皮在丹江边是一种强势植物,在临水的一些地方,它们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一眼看去,都是它们的兄弟姐妹,别的植物很难插足,简直就是葛巴皮的王国。
丹江看水,如同反复铺垫的一场大戏,终于来到它的高潮部分。我们在一道河湾里登上了一条小船,海明摇起船桨,悠悠地向河湾里驶去。河湾里水域宽阔,已让我们体味到了大江大河的感觉。我们这些生在山里的旱鸭子,坐在船上,像到了太空中一样,脚下没跟,身体似乎要飘将起来,便紧紧地抓着船梆。海明熟练地摇着桨,让我们品味着异乎寻常的感觉。恍惚间,船儿已经来到河湾中间,海明要下河洗澡,把船桨推给了我,撒手向船头奔去。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让我不知所措,本能地拼命摇浆,愈摇小船晃动的愈厉害,让我一屁股坐在船梆上,险些翻入河中。此时,海明一个猛子扎入河中,不见了人影。
船儿渐趋平静,海明没有浮上水面,我想:海明这么长时间都没浮上来, 这儿的水还真的不浅呢!又过了一会儿,仍没有海明的影子,我有些害怕起来,别是海明出了事儿吧?于是,我们都惶惶然盯着水面,只见河面上冒出一连串浑浊的气泡,随之,海明像一颗炮弹从水下弹出。弹出的海明把我们吓了一跳,这那里是海明,分明是个怪物。海明的头竟变了颜色,像一个青黑的大泥球。我连忙问道:海明,你这是咋了?海明用力抹了一把脸说:嗨,水太浅,扎到泥里去了。海明站起身来,河水也仅仅淹到他的腰际,这让我们忍俊不禁。我们这些旱鸭子一下子都胆大起来,你争我抢地学起划桨,狠命地晃动船儿,看它到底能不能翻入河中,也学着海明的样子,一头扎进河中去学游泳。我们一下子完成了从陆地动物向水生动物的转换,尽情地在丹江里嬉戏起来。
丹江的水虽浅,但这样的丹江兴许更适宜我们,且大有收获。首先,在丹江平生第一次洗了青泥浴。现在回忆起来,那种感觉真是爽极了。我们在江中乐够了,玩累了,就到岸上休息。那时天空的太阳大大的,在岸上待久了,经不住太阳的炙烤,纷纷回到水中去降温,不知谁忽然有了灵感,用泥巴涂满全身,以防太阳暴晒,美其名曰青泥浴。大家一看此法甚妙,纷纷效仿,有人甚至把脸部和头发全涂了,只露出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睛,很是滑稽、搞笑。一时间,岸上躺的,水边站的,全是青泥雕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认不得谁,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了。
丹江的泥巴确实不错,细腻、纯净,没有杂质,没有异味,非常的有粘度,抹在身上,滑溜舒服,这真是个绝妙的创意!我们浑身涂满泥巴,躺在江边的黄土地上,像晒泥胎一样任凭太阳暴晒,感觉身上的水分慢慢被太阳收去,皮肤由松变紧,紧得通身像被什么东西箍着似的,然后感觉有很多小东西在扯动我们的汗毛,越扯越紧,紧得有些痒痒的痛痛的,身上的甲壳也越箍越紧,紧得让人有些难受。然后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忽然就爆裂了,那细微的爆裂声从身体的某个部位传输到中枢神经,被无限放大,传递出一种强烈的轻松感、解脱感,然后,身体多个地方爆点频频,再之后整个躯体就进入了大爆炸时代。这种爆炸此起彼伏、难以数计、无以辨别,全身上下有无以名状的痛快。等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结束,再到丹江里扎个猛子,浑身洁净如初,不着丁点泥土,浑身上下有脱胎换骨般的感觉。
另一个收获是,通过洗青泥浴,解开了我心中存留的一个疑团。刚才说过,丹江的淤泥纯净细腻,没有杂质,极富粘性,但这淤泥中蕴含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经意间,我们从中有了新的发现。在洗青泥浴的过程中,脚下踩到一种硬硬的、滑滑的东西,又扁又平,本以为它是河蚌,心想在丹江中没有捉到鱼,捉一只河蚌也好,便把它从淤泥中摸了上来,却发现它是一块又黑又丑的砖头,便沮丧的把它重新扔回河中。但我的同伴们好像一群啥都感兴趣的泼皮狗,他们便你争我抢地把扔到河中的砖头捞出,再把它扔到更远处,然后再争抢着去打捞,竟成了一种趣味盎然的游戏。我被他们的激动情绪所感染,也加入到抢夺的行列中,待那半块砖头好不容易回到我手中时,它已被抢夺得黝黑铮亮,纤尘不染,在我把它重新投入江中的一刹那,发现它表面竟雕刻有古朴的花纹,就将未及出手的砖头急忙收了回来,仔细查看,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有些似曾相识。伙伴们上来抢夺,我赶忙示意住手,像得了宝贝似地把它捧回岸上,一边擦拭一边细细再看。伙伴们见我发现了宝贝,也纷纷围来。
我问海明:这东西是啥?海明不屑地说:半截砖头!我问:它咋就跑到丹江里来了?海明说:这儿就是它的原产地。我疑惑地瞪大眼睛。海明指着岸边说:你看,这岸边那坑坑洼洼的地方,都是古墓,它就出产在那儿。我这才发现,我们晒太阳的黄土岸边,坚硬的黄土地上有许多凹陷的地方,那里还能看到破碎古砖的痕迹。我手脚并用在坑边开挖,终于找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古砖,宝贝似地捧在手中。海明一看乐了,笑我没见过真正的好东西,错把破砖当宝贝。海明说,你真要觉得这是宝贝,回家开个拖拉机来,想拉多少拉多少。我说:这东西真的是宝贝,我要把它带回家。海明说:俺们丹江的宝贝多了,这算啥。前些年天旱的时候,人们到丹江边放牧、捕鱼,脚一踢就可能踢出来一尊战国铜鼎。
我问:这地方为啥有这么多古物哩?海明说:顺河往下五六里,就是楚国的龙城,知道吧,那可是楚国的第一个国都,那里出土的铜鼎、编钟,个个都是国宝级文物,价值连城,现在都是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才叫宝贝哩。我被海明的话给震撼了,丹江,真是一块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竟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内涵。眼前这浅浅的丹江,让我从心底里感叹它无法丈量的深度了。
回到刘楼,我问海明:这毛茸茸的草屋,是用岸边的葛巴皮泥垛起来的吧?
海明说:丹江的乌泥是个好东西,劲道结实,葛巴皮草又成了天然的捻子,用它盖房,任凭风吹雨淋,就跟铁桶一般。那这些砖屋也是用墓砖垒的吧?是的,都是从丹江里捞出来的。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不假。丹江人吃的住的,无不从丹江而来。丹江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它两岸的人们,不仅是鱼虾和它浇灌的粮食、树木,甚至它的一把泥土,一簇青草,它的一切的一切,包括它的过去和现在甚至是将来,只要是人们有用得住的,就毫不保留地奉献出来。这就是丹江,我真切感受到了它的博大与无私!
丹江水哺育的丹江人,骨子里秉承了这种品质和性格。而这种品质和性格,十年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体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后,他们为了支持工程建设,让京津人吃上丹江水,16万人舍家为国,毫无怨言义无反顾地迁徙他乡,用行动书写了一曲当代农民的无私奉献之歌,有谁不为之深深地感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