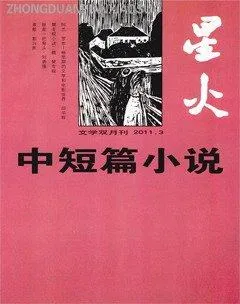夜鼓
那个念头是存起打工回来的第三天突然产生的。
那天存起的老婆走娘家去了,儿子胜强去学校上晚自习,家里只剩下存起一个人。存起一个人孤坐在灯下,觉得孤单清冷而又无聊。这时候,他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投到对面的屋墙上。那是一堵烟熏火燎得黑陶似的屋墙,就在这面屋墙上,悬挂着一宗物件,那便是当年给他热闹和快乐的锣鼓家什。已经二十多年不玩它们了,它们身上早蒙上一层厚厚的尘灰,锣和鼓之间,还、扯上了密密的蜘蛛网。存起望着那鼓与锣、那大钹及小钹,忍不住跳过去,伸出手,把它们一一取下,然后寻一块抹布擦起来。一会儿,他就把它们身上的灰尘擦干净。将结在上面的蛛网清除掉。他望着那红漆鲜艳的鼓,望着那金光闪烁的大锣小锣,以及同样金光闪烁的大钹小钹,觉得熟悉而又亲切。他忍不住举起手中的鼓槌,咚地一声在那鼓上猛敲了一下。那鼓颤颤的音,嗡嗡的响,仿佛一股热流烫烫地涌遍他全身,让他觉得亢奋和陶醉。他不由幸福地闭上了眼。就是在这时候,那个念头突然产生了:他要把当年的锣鼓队重新拉起来,在这腊月寂寞难熬的长夜里,尽情尽兴地玩一玩,尽情尽兴地热闹热闹。
存起二十年前就是有名的鼓手了。
那时候的存起才二十郎当岁,推个小平头、穿件红背心,两只鼓槌在那漆色鲜红的大鼓上一敲,真是又帅又威风。那时候,由他和贵祥、满柱、二秃、俊友五人组成的锣鼓队,也是这一带最棒的锣鼓队。农闲时节、节期假日,他们就把队伍拉起来在村巷里耍闹。那时候,他们的锣鼓队也最受村里人欢迎,只要听到锣鼓咚咚锵锵地响起来,便纷纷跑来看,把他们团团地围在核心,鼓掌声欢呼声响成一堆儿。然而现在,他们的锣鼓队早已解散了,他这个有名的鼓手也早被人遗忘,每每走在村巷里。甚至连正眼瞧他的人都没有了。这让存起一直感到苦恼困惑和不平。重新拉起锣鼓队的念头一产生,存起便激动得眼里放出了光,血也沸腾了似的涌上脑门儿,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一下子变得年轻精神了。他蹭地一下跳起来,披上一件半大衣就朝门外走。他要去找贵祥、满柱、二秃和俊友,立马把这锣鼓队重新拉起来。
冬天的夜晚黑而且静,一团一团的夜雾丝一样缠绕在村巷里。村巷里的残雪还没有化尽,脚踩在上面发出苏苏的响。存起在村巷里急走着,心里还被刚刚产生的这一念头激动着。他一面走,一面想着敲打起锣鼓时的热闹场面,脸上现出美滋滋的表情来。就这么着,他走到村巷的另一头,在贵祥家的院门前立住了脚。
贵祥是锣鼓队里的大锣手。
存起立住脚,才看见贵祥家已经盖起了一幢四合院,那四合院高高的门楼、高高的台阶,高高的屋墙上镶着玛赛克,门口还有两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存起望着这气派的四合院,不由嘬了嘬牙花子。他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才推开那副黑漆油亮的铁大门。一间布置亮堂的客厅里,贵祥正跟什么人打电话,存起进门半天了,贵祥竟然没有发现他。他使劲吭了吭嗓子,贵祥才转过脸,认出他之后,努着下巴把他让到了旁边的沙发上。
存起坐下来,就拿眼去看贵祥。他发现这个同自己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家伙有些陌生了,留了长头发,肚子鼓起来,穿上了西服系上了领带,完全一副城里老板的派头。存起知道,贵祥也真成老板了,他办了家板材厂,一年净得五十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私营企业家。他发现贵祥在电话里说的也是板材厂的事,这个电话打完了,他又去打另一个,另一个电话打完了,他又拨通了下一个,一个一个打得没完没了。等这么一连打了八个电话后,贵祥才转过脸来接待存起,给存起丢过一支带嘴儿的烟。
存起把烟捡起来,顾不得叼在嘴上去吸,只在耳轮上那么一夹。便迫不及待地开了腔,他眼里放着光,兴致勃勃地对贵祥说,贵祥,你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
贵祥说,干什么?你就说呗!
存起说,快到年关了,咱再把锣鼓家什耍起来咋样?
存起说着就拿眼去望贵祥,等着他回答。可他望见的贵祥早已吃惊地瞪大了眼,随即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存起不解地说,贵祥,你这是笑什么?
贵祥道,我笑你怎么还有这心思?
存起连忙说,大冬天的闷得慌,耍耍锣鼓热闹热闹呗。
贵祥哈哈地笑得更响亮,说,都啥年景了,谁还有闲心玩那个?贵祥这么说着又哈哈地笑起来。贵祥这么哈哈笑着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又响了,他就冲存起摊摊手,又摸起了话筒,喂,哪位?对,我是石材厂的王老板……存起看贵祥又没完没了地扯起板材厂的事,仿佛身边没了他这个人,一颗热烫烫的心便猛丁冷下来。他知道贵祥已经一门心思放在了他的厂子上,早就没有耍锣鼓的兴趣了,便非常遗憾地叹出一口气。怏怏地从那四合院里走出来。
走在村中的巷道里,存起的情绪就不怎么好,脸上美滋滋的表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紧紧皱着的眉头。但他不好的情绪只持续了一会儿,立刻便烟消云散了。他在心里说,贵祥,你没心思玩就没心思玩吧,还有满柱二秃和俊友呢!俺只要把他们拉起来,照样能把锣鼓家什耍得热热闹闹的。想到这里,存起的情绪又高昂起来,他挺挺胸脯,抖擞一下精神,沿着村巷朝满柱家走去。
满柱是锣鼓队里的小锣手。
满柱家距贵祥家不很远,存起绕过贵祥家那幢气派的四合院,再穿过半条窄窄巴巴的村巷儿,就到了满柱家的院门前。满柱家跟自己家一样,也住着几间小草房。存起抬起眼,望着那草房上已经变得黑黑的麦草,竟然有一种亲近温馨的感觉。他连门也没敲,就径直进了院,跨进那草房内。一盏昏黄的灯底下,满柱正跟老婆坐在那里穿糖葫芦。两人面前放着三只篮,一只篮里盛着山楂,一只篮里放着竹棍。两人就捏着山楂朝竹棍上穿。穿好了,再放到第三只篮子里。存起推门进来时,第三只篮子里已穿好了半篮糖葫芦。看见存起走进来,满柱很高兴,忙把手里的山楂丢下,热情地给他让座儿,说,存起,你咋有空来这里串门儿?
存起一脸兴奋地说,满柱,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呢。
满柱说,什么事?你快说啊?
存起便郑重地清一清嗓门,把他要拉锣鼓队的打算说给满柱听。说完之后他拿眼去看满柱,等着他的回答。
让存起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满柱竟然像贵祥一样,也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一面笑着一面说,存起,都啥年景了,谁还有闲心玩这个?
存起说,不玩这个玩什么?
满柱说,挣钱啊?现在只有钱才是真格的呢!说着又穿起了他的糖葫芦,连头也不抬一下。
存起望着,不由地就来了火气,他真想跳过去,一脚把那篮子给踢了,但是他没动。他明白满柱和贵祥一样,也没有玩锣鼓的兴趣了,只好叹一口气,默默地退出来。
贵祥与满柱都没有拉到,存起便知道锣鼓队是没有拉起来的希望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便躺在床上不动了,那样子看上去像霜打的一只蔫茄子。老婆儿子都不在家,存起一个人在床上躺着,便又生出孤单清冷和无聊。他望着那副被他擦拭一新的锣鼓家什,想起在贵祥满柱那里的遭遇,心里还有些悻悻的。存起想,现在的人真是邪门了,为了几个破钱,连个热闹乐子也不要了!人活着若没了热闹和乐子,挣的钱再多,又有啥滋味?对此,存起相当不理解。
夜这当儿就深下来,天上的一钩弦月不见了,满世界变得锅底似的黑。但存起还是没有睡觉的意思,他就仰躺在床上,无聊地望着窗外的黑夜愣神儿。不知这么愣了多久的神,一个呵欠打上来,他才准备脱光衣裳去睡觉。但就在这时候,他猛地怔住了,忽然听到床底下传来一阵阵呼噜声,好像有个汉子睡在床底下。他觉得很奇怪,这是什么声音啊?支着耳朵听了听。那声音还在呼噜呼噜地响,他就腾地一下跳下床,拉开吊在梁头上的电灯泡。他把灯线扯下来,借着灯光向床底下瞧,只一眼,他便怔住了,竟然真的看见一个汉子睡在自己家的床底下!那汉子狗一样趴在那里,一脸的蛛网和尘灰。存起望着差点叫出了声。他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俺家的床底下怎么会睡着一个人?他皱皱眉,又搔搔后脑壳,再巴眨巴眨眼,猛古丁就明白了,这是一个贼。这个贼一准是趁他出门的当儿溜进来的,在正要行窃的时候被回来的他堵在屋里了。存起见那家伙呼呼大睡的样子就冷笑了起来,一边冷笑着,一边抄起旁边的一条顶门棍,狠狠地捣过去。只一捣,便把那家伙给捣醒了,哆哆嗦嗦从床底下爬出来,扑通跪倒在他面前。
那家伙果然是个贼,他可怜巴巴地望着存起说,大哥,求求你,饶俺这一回吧。
存起冷笑道,饶你这一回?想得倒怪美!老子要送你进局子!
那贼更加慌,匍匐着抢过来,死死地抱住了存起的腿,流着眼泪说,大哥求求你,千万别送俺进局子。你饶俺这一回,叫俺咋着就咋着?
存起撇撇嘴,叫你吃屎你吃屎?
那贼说,你让俺吃俺就吃。
存起望着那贼不由笑起来。存起想,这家伙可真是个贱骨头,贱得连屎都能吃,真是连狗也不如。他望着那贼,觉得跟这种连狗都不如的人计较真没劲,心头的火便一下子没有了。他恶心地啐出一口痰,正要飞起一脚把他踹起来,让他快快地滚出去。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的目光不知怎么又落在了那些锣鼓家什上。他想起他要拉锣鼓队的打算和在贵祥满柱那里碰到的钉子,眼珠不由地转起来。他转着眼珠问那贼,俺叫你干啥就干啥?
那贼连忙说,只要饶了俺,叫俺干啥就干啥!
存起说,你说话可算话?
那贼说,俺说话算话。
存起就把那面金灿灿的大锣取过来让那贼来敲。
那贼说,让俺敲这干什么?
存起一瞪眼道,你别管,让你敲你就敲!
存起见那贼很听话地拿起了锣锤,他便抓起鼓槌来。他敲一下鼓,就让那贼敲一下锣;他敲两下鼓,就让那贼敲两下锣,咚!锵!咚咚!锵锵!咚咚咚!锵锵锵!两人就这么你一下我一下地敲了起来,敲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存起敲着敲着就乐了,乐得咧开了大嘴巴。存起的嘴巴里有几颗不怎么齐的牙,一咧开嘴,就像秋天里熟透了的山石榴,在灯光下白白地一闪一闪的。
存起和那贼正这么一下一下地敲着。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了,只见上晚自习回来的儿子胜强一步闯进门。儿子一进门就怒怒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还让人睡觉不!说着又怒怒地将门一摔,走了。存起从打工回来的那天起,儿子就吵着跟他要辆山地车,被他十分坚决地拒绝了,因此,这几天儿子一直同他疙疙瘩瘩地别扭着。存起望着儿子的背影进了小东屋,眼珠子却滴溜溜地转起来。转着转着他有了主意,忙放下手中的鼓槌儿,追着儿子也来到小东屋,向儿子堆出一脸讨好的笑。
他对儿子说,胜强,你不是要辆山地车吗?你答应爹一件事,爹就给你买。
胜强拿眼望着他,有点不相信地说,你让我干什么?
存起说,我让你跟着我敲小锣。
儿子说,要我敲小锣干什么?
存起说,你别管,叫你敲你就只管敲。
存起说着又返回正屋。取过那面小锣来,向儿子手里递过去。儿子望望那锣,又望望爹,犹豫着接在手,又犹豫着敲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存起听到儿子把那小锣敲得脆生生地响,不由拍着手叫了一声好。
意外地得到了大锣手小锣手,存起兴奋得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搓搓手,搔搔后脑勺,在屋里转了一圈儿,才想起下一步要干什么。他把儿子胜强和那贼叫到一块儿,让他们在家里等着,再一次走进村巷里。他要去找大钹手和小钹手。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锣鼓队拉起来,好好地耍他一家伙,让贵祥与满柱瞧一瞧,没有他们,老子的锣鼓家什照样能热热闹闹地玩起来。存起一边在肚子里想着,一边快快地在村巷里走,脸上又填满了兴奋的表情。眨眼的当儿便来到二秃家的院门口。
二秃是锣鼓队里的大钹手。
存起在二秃家的门口站下来,便有些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拍二秃家的门。二秃家的门是一扇铁大门,上面的绿漆早就剥落了,两个铜环锈掉了一只,剩下一只吊在那里。像只独眼睛。他抓着那铁环,在那铁大门上刚拍了两下,手便僵住了。他一拍脑门儿,突然想起来,二秃被判刑了,现在还蹲在县城的牢狱里。僵住了的手只好失望地缩回来。
二秃犯的是强奸罪。二秃没蹲牢狱前,在村里开着一家小卖铺,卖酒卖烟卖糖卖茶,小日子过得很红火。有一回二秃去城里提货,顺便在一家录像厅里看了回录像片,心性就变坏了,回村来的半路上,他看见一个小妇女在地里割草,露出的胳膊白白嫩嫩的十分喜欢人,他就起了坏心思。他瞅着四下没人影,就把肩上的货挑子一丢,三步两步窜了上去,把那小妇女给拖进了旁边的玉米地,将人家给那个了。
就这么着,二秃被关进了牢狱里。
二秃蹲到了牢狱里,当然就无法跟他去打大钹了,存起觉得挺可惜、很遗憾,他站在那里叹了一口气,只好朝打小钹的俊友家方向走。他打算先把俊友动员好,再去物色大钹手。他刚转过身,忽然又立住了,只见二秃家的院门吱吱呀呀地打开了,二秃的老婆美荣从里面闪出来。夜色中。存起看见美荣半开着怀,两只奶子在毛线衣里鼓鼓着,差不多要探向自己的胸口。他赶忙把眼睛挪开去,心里像揣了只小兔怦怦跳。就听美荣开了腔,存起,咋不进门就走哩?
存起慌忙道,我想起二秃不在家。
美荣一扭小腰说,他不在家怕什么?他不在家俺在家哩!美荣说着瞟瞟他,身子就要朝他的怀里靠。
存起吓得跳开去,美荣又一扭小腰开了腔,存起你慌个啥?陪俺玩玩不成哩?俺也不多要你钱,一夜五元就中哩。
存起听了直惊得张开嘴巴说不出话,他瞪着眼怔怔地看美荣,仿佛不认识这个女人了。后来,他见美荣挑着眉儿又要朝他怀里偎,这才像挨了蝎子蜇,一道烟似的逃开了。
一气逃到俊友家的院门口,存起的心还怦怦地跳。他万万没想到,美荣竟变成这样的女人。他记得原来的美荣是个很正派安分的女人,她嫁给二秃后,两口儿一个勤勤俭俭操持家务,一个本本分分耕种庄稼,小日子过得挺安泰,可想不到现如今两口儿都变了,都毁了,一个进了牢狱,判了十几年刑;一个成了卖骚卖肉的窑货。存起不由为这两口子惋惜和难过。存起问自己,这世道到底怎么了,人为什么一个个都变了?存起一时找不出答案来。找不出答案来的存起心绪忽然就坏了,耍锣鼓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他叹了一口气,将脚一跌,干脆回家睡觉去,但刚走了几步又冷丁立住了。他在心里想,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变了?还不就是因为没有过去热闹了?为什么没有过去热闹了?还不就是因为大家都把心思放在钱上了?钱这玩艺可不是好东西,若不咋都这么说,人一有钱就变坏呢?他这么想着,忽然又强烈地怀念起过去的日子来,怀念起敲打锣鼓时那热闹动人的场面。他心中的欲望和激情又一次在胸中鼓荡。他连犹豫也没犹豫,就猛地推开了俊友家的门。
俊友在家。
存起走进俊友住的屋门时,俊友正和几个汉子围坐在那里玩麻将,满屋都是呛人的烟味儿。存起走进来,俊友竟然连个招呼也没打,依旧在那里专注地玩着。显然俊友赢钱了,一圈麻将摸完后,那几个汉子都像死了爹,很不情愿地把面前的票子推给了俊友,俊友面前的票子就聚起了一大堆。俊友望着那票子,圆圆的脸笑成弥勒佛。他把那票子一张一张码起来,仔细数点数点,很小心地掖进自己的腰包里。接下来,俊友同那几个汉子又继续玩,仍然不理睬站在旁边的存起。存起望着就火了,他冲着俊友呸出一口痰,吼也似的道,俊友,你怎么成了赌鬼了?他接着又吼,俊友,还不快把摊子收起来,小心犯法蹲公安!随即他便把他要拉锣鼓队的打算说给俊友听。俊友听着皱皱眉,像打量怪物似的打量着存起说,存起,你有毛病是不是?都啥年景了,谁还有心思玩那个?
存起说,再不热闹热闹,咱们村就毁了!
俊友说,咋毁了?
存起说,都跟你一样成赌鬼了!存起还想说说美荣卖骚的事,忽然听到俊友哈哈大笑起来。笑着,俊友站起身,一把将他推出了门外,接着砰地将门关上,从里面插死了!存起跳着高,还要向屋里闯,哗啦啦,一盆洗脚水突然从门的上梁子上浇下来,把他浇成了落汤鸡。
从俊友家走出来,夜已经很深了,家家户户都死死地关上了门,巷子里静得连一条狗都没有。存起走在巷子里,想起大钹手小钹手都没找到,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他想,难道这锣鼓队就真的拉不起来了?难道偌大的一个村子里,就找不着人来打大钹小钹了?存起想起还等在家里的大锣手小锣手,实在有些不甘心。一块石头绊着他的脚,他不知怎么就来了恼,一脚踢起来,把那石子踢飞了。石子落在谁家的屋墙上,砰一下弹回来,吓得一只夜行的猫落荒而逃。
存起就这么焦躁地走着的时候。忽然冷丁站住了脚,他看见不远处一个黑影闪了闪,一直闪进了二秃家的院门儿。存起眨眨眼。觉得黑影儿有点儿熟,他皱皱眉头便想了起来,是村长。存起想,半夜三更的,村长到二秃家干什么?二秃进牢狱了,二秃家里就只剩下二秃老婆美荣一个人。存起猛地就又想起刚才遇到二秃老婆美荣的情景,心里立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存起就呸地啐出一口痰,心里道,好你个村长,平时在人前人模狗样的,原来是个不正经的东西!这么骂着,存起的眼睛又滴溜溜地转开了,这一转,立马又生出一个主意来。他决定去捉这对狗男女的奸,逼着他们做大钹手小钹手。二秃蹲牢狱了,俊友又成了个赌鬼,只好用这两个狗男女来顶替了。
存起一拿定主意,脸上的笑容又闪出来。他掉转方向,朝二秃家的院子走。来到二秃家院门外,才知道那门已牢牢地关上了。他四下里瞅了瞅,看见旁边有棵小槐树,他便走过去,呸呸地在手里吐了些唾沫,嗤嗤地攀上去,山猫一样翻过不高的院墙,轻轻地落在了二秃家的院子里。二秃家的院子也是个农家小院子,三间草房矮矮的,窗子还是过去的木格窗。有一缕黄黄的灯光正从窗内漏出来。存起摸到那窗下,就看见一张土炕上,美荣和村长已滚成一堆儿。存起不由冷笑了起来。见两人搂抱着翻滚了一会儿。又双双钻进了花被窝,他便猛地将拳头捏紧,使劲咬一咬牙,奋起一脚踹开了那副半掩着的门……
大约凌晨二点左右,存起终于把他的锣鼓队拉了起来。他们是鼓手存起,大锣手那个贼,小锣手儿子胜强,大钹手村长,小钹手二秃的老婆美荣。虽然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杂牌军,而且除了儿子胜强外,还都是些小偷嫖客和娼妇,但存起还是非常激动和兴奋。他扫了大家一眼,挺了挺腰杆,清了清嗓子,把这支杂牌军集中起来,让他们排成一长溜,然后将锣鼓家什一一分发给他们,便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发出了出发的命令。
村里有棵百年老槐树,老槐树下有一片空场儿,早年的锣鼓队就聚集在这里耍闹。今天晚上存起也不例外。他把队伍带到那棵老槐树下面时,东方已经显露出微微的曙色,村巷里越是一派静,所有的人似乎都进入沉沉的梦乡。就在这时候,存起把手中的鼓槌高高地举了起来。随着那鼓咚地一声大响,那贼、胜强、村长、美荣也各自敲响了各自手中的家什。山村静静的夜里,那鼓的咚咚大音,那大锣小锣的锵锵暴响,那大钹小钹的嚓嚓喧闹,是那么宏大、尖锐和震耳。熟睡中的村里人都被这喧嚣惊醒了,他们一个个惊愕地瞪大眼,又一个个匆忙地披上衣,然后慌慌而又惊疑地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来。不一会儿,老槐树下就聚集起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大家立在那里,望着这半夜三更闹起来的锣鼓队,一个个张大嘴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存起,并不理会村里人,他整个身心早已沉浸在锣鼓热烈的喧闹中,他仿佛又回到过去那快乐热闹而又风光的时候,周身的热血也像早年那样喷涌、奔腾。他目光闪烁、精神亢奋,一双大手紧握着鼓槌,用尽了力气只是不停地敲,咚咚咚!咚咚咚!那些锣手钹手们似乎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一个个也都振作起来,纷纷把各自手中的家什敲打得山似的响。就这样,整个夜晚,整个村子,整个村子里人们的心,都被这惊天动地的锣鼓声搅乱了。
(责编: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