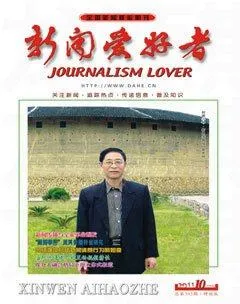新闻传播与辛亥革命爆发
辛亥革命前的报刊舆论传播
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事业得益于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能够不间断地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状态,形成相应的舆论力量,在意识形态的营造和运作功能方面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最初几年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政党、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或者以间接的方式控制报纸,力图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革命派的同盟会在东京,其分支机构在上海开会时,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办报。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也曾经充分肯定报纸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报纸的宣传工作占了九成功劳,武装起义的功劳只有一成。
谈到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准备工作,不能不提到革命先驱田桐与白逾恒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为,正是以这本杂志为基础,革命党人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才得以出现,才能够公开为发动革命摇旗呐喊。在此之前,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靠少数几个人的演讲游说,翻印具有反满思想的小册子和译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革命宣传,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正式机关报,除了在檀香山出版的《隆记报》为兴中会会员所掌握外,海内外的大部分舆论阵地均为改良派所占领。田桐,号梓琴,又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县人,二十二岁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结成莫逆之交。后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4年夏秋间,他与白逾恒(湖北京山人)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是各省留日学生“破除地方团体意见”,联合创办起来的革命刊物,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其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也曾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同主创人员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
1905年8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以兴中会为首的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为了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同盟会成立不久,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基础,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办了其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时,他也为《民报》定下了一项基本任务,即“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进。”从此,革命派创建了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宣传革命真理、鼓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说,从《民报》创办开始,革命党人就真正意识到了只有建立革命的舆论阵地,营造革命的舆论环境,才能真正促成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日后的起义做好思想、道义上的准备。
《民报》创刊后,田桐收集《江阴守城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明末历史文献资料,编辑而成《亡国惨记》一书,以“民报社”的名义出版,用来宣传反清思想。此书一出,人心振奋。同为湖北蕲春人的革命家黄侃,在担任《民报》撰写社论及编辑工作时,也曾用“信川”、“黄病蝉”等笔名,先后为《民报》写了《专一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释侠》、《哀太平天国》等大量文章,鼓吹革命。如《民报》第十七期发表的《哀贫民》一文,黄侃运用从家乡得知的生动事实,叙述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迫下,“羹不盐,爨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同时,他尖锐地指出:“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盗之彰彰者,人皆弃之;荫蔽而为盗,天下无非之者,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号召劳苦大众群起而攻之,“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
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人们多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反对清政府的种族压迫,而黄侃能够留心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同情农民疾苦,鼓吹农民革命,的确难能可贵。后来,他又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的卑劣行径。指出,他们口头上讲立宪,实际上“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造成亡国的后果。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要同他们对立,而且在道德行为上更要同他们泾渭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是黄侃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民报》创刊后,在各地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民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在群众中广泛普及了革命思想,宣传了政党纲领,甚至在清政府为镇压革命而创办的一些新式军事学校和新军部队中,也有广泛传播。武昌一些倾向革命的新军官兵,经常到当地的秘密革命机关借阅《民报》。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当时在兵目学堂学习的陈作新,甚至能够把他所看过的《民报》,“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篇地背诵”,可见当时《民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
同一时期,也正是近代史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第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亚洲。《民报》作为一份“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不仅对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予以深切的同情,更是身先士卒,吹响了震彻海外的革命号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晚清保皇党人从1899年开始,就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03年以前,整个南洋、美洲几乎成了保皇党的天下,在那里出版的中文报纸几乎是清一色的保皇党报纸。为了消除保皇党在海外的影响,肃清他们的流毒,革命派报刊同保皇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07年,田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海防至新加坡,与居正(湖北广济即今武穴市人)一起,主持《中兴日报》,同保皇党旗下的《南洋总汇报》就“革命”与“君主立宪”得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战斗从《中兴日报》创刊不久就开始打响,到1908年9月前后,发展到高潮。田桐有时甚至登坛同保皇党头目面对面辩论,用许多具体事实阐明中国非革命无以挽救,并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对外卖国种种等罪行,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当保皇党头目发言时,听众愤然喊“打”。在《中兴日报》的强大舆论攻势下,《南洋总汇报》渐次理屈词穷,销路大跌,终为群众所厌弃。这一场论战,是早期《民报》、《新民丛报》之间的那场大论战的继续。它同样以保皇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经过这场论战,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同数年前南洋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甚至“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踊跃捐款,仅南洋一带的华侨就支援革命经费达五六百万元之巨,为革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支援。
《大江报》与湖北新军
革命派的报纸舆论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清朝新军中。湖北新军在建立之初是反革命的,曾对湖北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过残暴的镇压。然而在辛亥革命中,湖北新军却是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新军从反革命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及其任总编辑的《商务报》在宣传转化新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詹大悲,湖北蕲春人,他认为报纸是宣传革命的有力工具,是联络同志的手段。他主持的《大江报》,以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大江报》鼓吹革命,把对新军的秘密宣传和公开的革命鼓动结合起来,以新军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对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现象进行披露。军中的弊端,一经士兵到报社申诉,即予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因此“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
《大江报》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发展个人订户,又赠送免费报纸供各营士兵阅览,以加强士兵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报纸副总编辑何海鸣原来就是一位新军下级军官。《大江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士兵们把《大江报》视为自己的喉舌,有什么事就去找报社、找编辑部反映和商量,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士兵们节衣缩食捐款相助。在《大江报》的宣传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到武昌起义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5000人,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江报》的革命动员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詹大悲还担任了《商务报》总编辑,该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成为湖北新军群治学社的机关报,社员向《商务报》投稿,詹大悲总是优先予以刊载,并与其建立通讯联系,他的编辑室里常有士兵出入。当时,《商务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革命爆发前新军群治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商务报》同《大江报》一样,在新军中宣传革命,维护新军士兵利益,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大江报》、《商务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积极宣传动员、细心组织教育湖北新军,使其最终在武昌起义中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革命力量,也把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
在湖北报人的舆论宣传作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而点燃革命导火索的,则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于1911年7月17日发表了该报副主笔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怒斥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立宪派的“伏阙上书”,并指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7月26日,《大江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黄侃,字季刚,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参加者,革命报人。曾参与《民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并为多种报刊撰稿,亦为湖北蕲春县人。1911年7月25日,身为同盟会成员的黄侃自河南回蕲春,途经汉口,《大江报》主笔詹大悲设宴招待这位同乡好友,并诚邀黄侃为《大江报》写时评,黄侃挥毫泼墨,写下了这篇201字的战斗檄文: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亡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病入膏肓,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不能救中国;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文章恰与何海鸣时评相呼应。这篇文章一发表,犹如在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中装上了导火线。鄂督瑞徵极为震恐,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警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第二天,《大江报》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工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
《大江报》出版的时间虽然只有8个月,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大放光芒。由于《大江报》被查封,激起了群众的怒火,整个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就在该报被封的两个多月后的10月10日晚7时,驻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不难看出,以《大江报》为代表的革命报刊的新闻传播,在这次起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封建政权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它始溃于武昌新军之手,则似乎又是偶然;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偶然”,正说明新闻传播推动历史进程的“必然”。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了几家报纸,宣传报道革命的消息,继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胡石庵创办的《大汉报》。
胡石庵是湖北天门人,武昌起义后,他创办的《大汉报》为起义后的第一家革命报纸,报道革命人民保卫武汉的情况。仅创刊号就印了一万多份,一周后激增至五万份。各地读者争相购阅,以至于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一份《大汉报》竟然卖到“五十金”,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的消息,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为革命情势的迅速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革命危急时刻,《大汉报》曾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报道军民获胜的消息,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大汉报》的新闻报道对保卫革命成果,稳定革命形势起了巨大的作用。
其他湖北报人也在革命危难之际纷纷办报抨击袁世凯窃国复辟的卑劣行为,挽救革命果实。临时政府北迁后,田桐对袁世凯的窃权极为愤慨,乃赴北京继续办《国光新闻》报。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阴谋暗算不断予以抨击和揭露。这些报人不但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进行舆论鼓动,还积极参与革命的行动,其中不少人还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詹大悲于辛亥革命前组织革命、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主持汉口军政分府,功绩卓著。田桐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秘书长兼随军参谋。后但任了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韶关大本营宣传处处长,直接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廷,颠覆了帝制,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革命中,詹大悲、田桐、胡石庵等报人敢为人之先,他们创办报纸宣传革命,鼓吹革命思想,发表激进文章,点燃革命烈火,发动群众,成为革命舆论先锋。这些报人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是革命中最坚强的力量,他们的办报活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被时代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辛亥革命前后的蕲春籍报人
辛亥革命之爆发在湖北,与报刊的舆论鼓动分不开;又与当时激进的革命报刊多集中在湖北地区分不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报人中,蕲春籍人士又最多、影响最大。除上述先后主持或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及《民报》、《中兴日报》、《泗滨日报》、《国光新闻》的田桐;创办《大江报》、接办《汉口商务报》,以革命的舆论直接引发武昌首义的詹大悲;以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而吹响辛亥革命舆论号角的黄侃外,还有多位为新闻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他们是:
蔡汇东,字达生,留日学生,在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田桐等革命志士,倡言革命,思想激进。曾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撰述。1905年8月27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首篇刊载了蔡汇东所撰写的时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抨击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批判清政府的投降行径,呼吁国人警醒,救亡图存。此文激起了日本政府的恼怒,以“有害公安”的罪名没收全部杂志,禁止《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此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一次重要的舆论活动。蔡汇东于辛亥革命前数月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出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法官,随黄兴参加了保卫阳、夏的战斗。
朱国钦,1905年曾在香港与保皇党第三号人物徐勤笔战,当时徐勤主办《商报》,朱国钦为《中国日报》编辑、撰稿人。朱国钦文笔犀利,辩锋泼辣,抨击清廷,提倡民族革命,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期,朱国钦继续任《中国日报》编辑。
洪淑龙,字九云,1910年在新加坡应荷属爪哇泗水埠学务总会聘,任华侨学校校长。后又应田桐之请,出任《泗滨日报》兼职副主笔。洪淑龙对副主笔之职甚是自负,曾在报馆门前撰写一联:“大丈夫发愤图强当如是也,好男儿当家作主岂不快哉。”横批为:“还我祖国”。洪淑龙参与了田桐与保皇党的论战,并在《泗滨日报》上发表了《驱邪论》、《辟夷论》等文,其文战斗力之强,震动了南洋,洪淑龙也因此与田桐一起,“互相灿耀于东亚、西欧之间”,成为南洋一带舆论宣传的双子星座。
方觉慧,字子樵,民国初年重要报人。1911年10月19日,辛亥革命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方觉慧任编辑,主笔政,或亲自撰文、或编辑稿件,传达政府旨意,鼓吹革命宏业,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影响。1912年2月15日,《民心报》创刊,方觉慧为主笔。该报“以随时进化,确立民国前提为宗旨”,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反对黎元洪把持的湖北政权。1912年4月15日,《震旦民报》创刊。年底,方觉慧出任报社副经理兼副主笔。方觉慧出言不殚,冷嘲热讽,批判袁世凯、黎元洪,拥护孙中山、黄兴,其人及《震旦民报》在当时舆论界均有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蕲春籍人士参与创办或主持经营、任主笔以及参与撰稿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多达十五种,计有:《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名《民报》,田桐、蔡汇东、黄侃)、《中兴日报》(田桐)、《泗滨日报》(田桐、洪淑龙)、《国风日报》(田桐)、《国光新闻》(田桐)、《国粹学报》(黄侃)、《大江报》(詹大悲、黄侃)、《中国日报》(朱国钦)、《汉口商务报》(詹大悲)、《大江白话报》(詹大悲)、《新汉报》(詹大悲)、《中华民国公报》(方觉慧)、《民心报》(方觉慧)、《震旦民报》(方觉慧)等。
蕲春地处鄂东,距离中心城市武汉仅百余公里,人杰地灵,尊师重教,民风淳朴,思想高尚。辛亥革命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求学于武昌,经商于汉口,因同乡关系互相影响、凝聚,以致形成舆论风潮,从而推动社会变革。这应该是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地处鄂东的武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除了探讨武昌首义中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之类具体问题,更应该探讨新闻传播对革命的爆发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细心搜罗当时的历史资料,认识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思考其中蕴涵的传播学命题,方不负先烈的流血牺牲,也期待史论之新发现。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