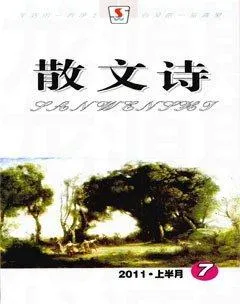词语:意见笔记
闹钟
闹钟怀着旧时的梦想。
比如故宫里,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留下的时钟,它产自西洋,还停留在19世纪。
它的旁边,还摆放着花瓶。导游小姐说:这种摆设,忠于历史,且源于一个传统的观念。
似乎,照片上的皇帝,至今还对这座钟保持着兴趣。
但钟停了。皇帝的乡愁,藏在钟的心脏里。
闹钟松懈下来,为了躲进博物馆。我看着那钟,不再是闹钟。我们发现那位皇帝,是一座钟的失主。他丢了时间,来到这里:进行失物招领。
我们醒来时,一个朝代被装订成历史。我们来到这里,一个朝代成为门票上的古董。
一个古老的装置,比人更懂得停顿。
隐身
为了让你看见我,我要做一个透明的人。但你还是看不见我,我也找不着自己。
透明:一个事物在词中消失。
也许,我到达的纬度,能够让我看到远方。我看到的远方,可以是一个奇迹。但它很少出现,它出现在需要耐心的眺望中。
我反对他。但他是对的。我只有绞尽脑汁。如果他是对的,那就是我错了。这一点,他不知道。我不得不常常来反省自己。
我是一个选民,但从未选过自己。“还是忘掉自己吧!免得遭到反对。”我这样对自己说。这不是谦虚,这就是选择。
选民:看不到自己的隐身术。
我在一个捉迷藏的游戏里找藏身之处。
表面
人们说出同一句话:我终于看到了希望。这句话里有我们都想看到的东西。但“希望”这东西没有表面,它不可看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他人看见。
它不同于“事情”: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
我常常听到:“事情永远不是表面看似的那样”,或“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些话,道出了人们对“事情”的态度。
然而,我却喜欢事情的表面:毫无疑问。
玻璃
一只呆在玻璃瓶中的蜜蜂,一下子抓住了我——一只蜜蜂的感受,带来了一个人内心的比喻。
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可就是找不到出口。这是什么感觉?
玻璃是透明的,我们看不到玻璃本身。玻璃墙是透明的,我们需要的是一扇通向外面的门。
一只蜜蜂呆在玻璃瓶中,它说出一个人的感叹和自语。我摊开双手,就是束手无策。我张嘴说话,不是为了给自己听。我不停地试着出去,是为了能够反复撞在视而不见的墙上。
玻璃墙,只有光线畅通无阻。
天堂
母亲死在去往县医院的途中。22年后,父亲死在自己的单人床上。
我相信,“上天堂的路到处远近一样”(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如果我不相信,他们就不能在天堂相聚。
但我想象不出天堂的模样,也搞不清天堂的位置。
我曾前往杭州,去领略人间天堂。我又到过大别山的一个县城:天堂寨。但我没有碰到我的父亲和母亲。而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我看到外面没有一个人。
天堂:一个人间虚构的地点。
如果你迷信它,它就是你的归宿和乡愁。如果你相信它,有时只是宁可相信。
母亲死在路上,晚年的父亲死在家里。我知道,他们都不愿死。
写作
一个词在它孤单时,同义词将拿它作伴,反义词要与之对称。我在它们之间制定等距离政策,一个劲地造句,说出最初的孤独。
我投稿的杂志已经停刊,我投稿的编辑刚刚辞职。我通过写作,插手生活。词语孤独,大地放假,沉默的人开始说话。
客厅里的桌子被我搬进房间,当作写作的地方:一个木匠失望的矩形,一个汉语的私人杂货铺,一个出版商的隐形抽屉。但我必须绕开这些。
我爱上今晚,正如我爱上夜晚。我爱上纸张,因为我爱上汉语。
我写下没有对象的爱和怀疑。突然间看到春天的花园,正在推理人们走进它的原因。
桃花
桃树是现成的。桃花就开在显而易见的树枝上,其中枯死的一截,长出木耳。
出于喜欢或辨认的需要,我久久地看着它。
桃花盛开,一般都要经历一次寒冷,但我看不出桃花的挣扎。
至于刚刚长出的新叶,还很少。这使得此时的桃树,像一张网。它遮不住一所土砖屋。时光的裂缝和屋檐,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它让桃花开在桃花的久远年代。
现在,两朵最大的桃花,在最近处开放。两朵桃花,代表了一树的桃花,和这个春天的桃花。我仿佛看到更多的桃花和叶片,在萌动。
我不由得自言自语:看不透春天,看不破红尘。
正如这个春天,我不需要沉默,也不能冷眼旁观。
躲雨
阵雨没有恶意。但阵雨是报复性的。
“这避之不及的雨!”此刻,我经历着——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次的时刻。
天一点点地暗下来。雨急促而来。闪电随之而来,撕裂暗沉沉的天色。
这不是暮色。事物盘旋。雷声滚动。感觉盘作一团。
阵雨中,我想到世界,和人的无所适从。其实,阵雨是天空类似于人的一次激动,它总是结束得如此匆忙。
我看到,阵雨过后,天一下子亮了许多。
割草
草被割了多年,却像没有动过。顺着这个念头,我想了很久。
也希望,更多的人和我想同一个问题。
割草这个农活,我干过多年。草,不时地向我涌来。我有些轻飘。
草生长的地方,有看不见的渴望。
露水向往着草原,割草的季节,一晃而过。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草。人们赞美,或咒骂。而草年复一年,等待着歌唱。
但割草时,我没有想过这些。我割草,在入冬前堆放起来,无非用于喂牛,取暖,打春时翻盖屋顶。不过想多了,当初割草的事就不再那么直接。
暮色
想猛然醒来:暮色深处,有什么秘密在悄悄卷起。每一次,我重返惟一的远眺。
除了生活,我看不清其他。
除非你,我不能和另外的人相遇。
在越来越黑的路上,我怕被这样的念头感伤:“家永远也回不了,只剩下地址可以使用。”
这其实是我不想说出的念头。一个人,为何总想离开那些离不开的地方?
我不能回答。我在等待时间的短暂和漫长。或许,我将又一次被不为所知的秘密,运送到自己认为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