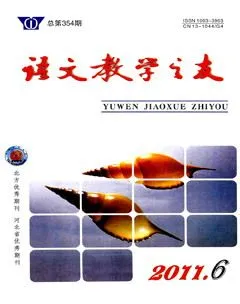李清照:一言难尽的花与酒
人教版《语文》必修4将李清照的《醉花阴》和《声声慢》选入同一篇课文,可谓用心良苦。两首词都写到了愁,写到了秋,写到了酒,写到了西风,写到了等待,还写到了黄昏的黄花,一切都是那样相似,一切又是那样迥异:早年新婚燕尔之后与晚年颠沛流离之际的李清照,其心境已形同天壤,大相径庭。
薄雾浓云愁永昼
《醉花阴》里的李清照,新婚燕尔之后,因丈夫“负笈远游”而深闺寂寞。在只有婚姻而没有爱情的时代,她却曾有过一个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据说,赵明诚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一本奇书,醒来时只记得其中三句:“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明诚不解其意,告诉了父亲赵挺之。赵挺之是个圆梦专家,笑着说:“言与司合是‘词’,安上已脱是‘女’,芝芙草拔是‘之夫’,你将来可能是词女之夫啊!”
21岁时,他娶到知书识礼的李清照。那年,她15岁。这段佳话流传甚广,清人乐钧有诗为证:“奇绝芝芙梦里情,先教夫婿认才名。一溪柳絮门前水,犹作青闺漱玉声。”真是妙不可言!
小夫妻过得很甜蜜,但赵明诚常年为官外任,二人聚少离多。寂寞的少妇便填词《醉花阴》,以述惆怅。明诚原本也才情不浅,接到词后,叹赏之余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三日三夜,填词五十阕。他信心十足地拿给友人陆德夫品评,其中就夹上了爱妻的《醉花阴》。
德夫很认真地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明诚兴冲冲地问哪三句,德夫答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是李清照《醉花阴》里的名句,赵明诚只好甘拜下风。
李清照一想到夫妻俩在一起的日子,沉浸于金石书画里,滋养着“莫道不消魂”的爱情,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此种心境,即便“佳节又重阳”,当时的她,满脑子装的也都是幸福的小烦恼。她在满腹才情里挥洒的岂有真愁?不过是挥之不去的无聊和寂寞。
试想,当她再一次一个人度过一个漫长的白昼,看惯了清晨的“薄雾”与傍晚的“浓云”,香炉里的龙涎香都烧完了,她对丈夫的等待却丝丝缕缕,不可断绝——这年的重阳节,秋意正浓,别家的欢歌戳伤了她孤独的寂寞,因为她恐怕又要一个人靠着“凉初透”的“玉枕”,度过漫漫长夜了。一念及此,词人的心便隐隐作痛了。
于是,词人想借酒浇“愁”,黄昏后“东篱把酒”。愁则愁矣,情调却丝毫未减,依然“有暗香盈袖”。似乎连西风都在跟她“过不去”,吹动珠帘,引诱她看看开得正盛的菊花,惹得她对花自怜,竟是“人比黄花瘦”。
她的愁,她的纠结,皆源自浓得化不开的思恋。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里的李清照,境遇大变。
汴京沦陷后,李清照夫妇也只得南渡流亡。从此,幸福也像她词里的花儿一样,“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凋零了,然后一去不返。国破,家亡,夫死。不幸,在李清照柔弱的生命里如影随形。她只身漂泊于江浙间,抱着一颗支离破碎的心,颠沛流离。
她是一个有泪但不哭的女人。在一个残秋的黄昏,她忍不住“寻寻觅觅”,寻觅过去快乐的影子。但现实让她如此失望,寻到的只有“冷冷清清”的寂寥和“凄凄惨惨戚戚”的感伤。
垂暮之年的李清照,门前冷落车马稀,只偶尔有零星旧友来访。她见过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她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欣喜地表示愿将平生所学相授。可是童言无忌的10岁女孩竟脱口而出:“才藻非女子事也!”
这种感觉,恰似捐了门槛的祥林嫂,依然不准拿祭台上的祭器,还要被人断喝一声:“你放着吧!”那心情,恐怕要一下子坏到极点了。李清照才华盖世,只可惜是个女人。在一个不需要才女的时代,成为才女就是一种悲哀。谣言说赵明诚死后,她曾再嫁张汝舟——一个有家庭暴力又粗俗不堪的男人。不怀好意、心怀嫉妒的男人们,企图以此诋毁她晚节不保。历史的烟雾弹遮住了很多代人的眼睛。以治学严谨著称的胡适之考证的结果是:“改嫁并非不道德之事,但她根本不曾改嫁,那是小人行为。”
心如古井的李清照,就以这样的姿态悄然在人群中退隐,流落江湖。试想,在如此心境下,愁闷不堪的她也只得借酒浇愁,但“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真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当年“薄雾浓云愁永昼”的日子,也已变成一种奢侈的烦恼。如今,只有“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欲说还休。而且,这种等待,漫无目的,手足无措。
连老天也哭了。残秋时节,黄昏的细雨让人更加落寞,还要“点点滴滴”地敲打梧桐,每一滴都像敲在词人的心上:人成各,今非昨,雨送黄昏花易落,病魂常似秋千索,旧欢雨散,好梦难寻,伤,伤,伤。这次第,恐怕真不是一个“愁”字能了得的。
她的愁,她的纠结,皆源自浓得化不开的忧伤。
这两首词里的李清照,尽管骨里肉里都是“愁”,但心境差得实在太远了:一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一个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不可同日而语了。
(作者单位:淄博市淄川区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