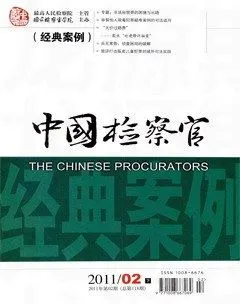女友使用其男友盗窃所得的赃款的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洪某与其女友杨某共同租住在丽江市古城区一出租房内。二人没有工作,也没有其他正当收入来源。2010年8月至11月之间,犯罪嫌疑人洪某以古城客栈内游客为目标,先后盗窃5起,涉案物品有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等电子设备,黄鹤楼等名烟9条,以及人民币现金若干,涉案物品总价值3万余元,所盗财物被洪某变现为现金。每次盗窃完成回到租住房之后(杨某事先不知情),洪某总是会分给其女友一定的金钱,其女友对于金钱的来源明知。但是没有参与盗窃的实行行为,全部赃款被二人用于日常生活开支。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认为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杨某不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洪某的女友杨某不构成盗窃罪的共同犯罪。五起盗窃案,均为犯罪嫌疑人洪某一人所为,杨某怂恿、鼓励洪某进行盗窃的表现非常不明显。卷内其他证据也未反映犯罪嫌疑人杨某参与盗窃的具体实行行为,只是参与事后的分赃行为。那么,杨某是否与其男友进行了密谋等帮助行为呢?当然从五起盗窃案来看,杨某尽管没有明确的支持其男友进行盗窃,却也“心安理得”的使用盗窃得来的赃物、赃款,至少已经默认了其男友的盗窃行为,其对男友的盗窃行为采取的是无所谓的态度;然而默认其盗窃行为。并不能代表二人形成了盗窃的合意。二人形成盗窃的共谋,至少要为盗窃“出谋划策”,对其男友的盗窃行为进行“智力支持”。然而,本案的五起盗窃,二人没有进行任何事前交流,均为犯罪嫌疑人洪某自己作案,事后将赃款分给杨某消费。因此,二人之间并没有形成盗窃犯罪的合意,不属于盗窃的共谋共同正犯,也不属于盗窃罪的帮助犯。
那么,杨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盗窃罪的教唆犯呢?从整个系列盗窃的案情来看,杨某的无所谓的“心理暗示”对其男友有一定的心理支持力。但是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力很难讲引起了洪某盗窃的犯意,因为,每次盗窃,都是洪某偷完东西之后,杨某才知道,也就是每一次具体的犯意产生,都是洪某的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杨某并没有挑起其男友的犯意。杨某的漠视其男友的盗窃行为,顶多是强化了其男友的犯意,让其男友主观认为,自己“所谓的爱”得到了女友的认可,但是教唆犯的最重要的主观构成要件就是“挑起犯意”,因此,杨某的行为也不属于盗窃罪的教唆犯。
其次,杨某的行为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9条将《刑法》第312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与原来的条文比较,扩大了犯罪行为方式,增加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兜底规定。
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应当如何理解?所谓窝藏,就是隐藏赃物或者替犯罪分子保管赃物使其不能或者难以发现。转移赃物是将赃物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行以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收购赃物主要是指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赃物的行为。代为销售则是受本犯犯罪人委托,帮助其销售赃物的行为。
“其他掩饰、隐瞒方法”,是指法条列举的四种方式以外的其他能够起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作用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介绍买卖、典当、拍卖、抵押或者用其抵债,以及提供虚假证明、发票或者涂改原始标识,对原赃物进行加工等行为,都属于本罪的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从司法实践来看,常见的“其他掩饰、隐瞒方法”除了上述司法解释中列举的方法以外,主要还包括收受、介绍买卖等方法。
由于本案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为表现为无偿收受赃款。显然不属于窝藏、转移、收购和代为销售,那么该种无偿收受行为是否属于“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兜底性规定呢?有学者认为,“收受”是指不支付对价而取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包括作为赠物予以接受、无利息的消费借贷等。无偿收受,在取得了处分权这一点上,与保管没有取得处分权有区别。从其他国家的立法来看,一般都将收受犯罪所得的行为规定为赃物犯罪。如《日本刑法》第256条规定:无偿受让盗窃赃物或其他相当于财产犯罪的行为所领得之物的,处3年以下惩役。搬运、保管或者有偿受让前项规定之物,或者就该物的有偿处分进行斡旋的,处10年以下惩役及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中国《刑法》第312条赃物罪盗的行为方式规定的比较笼统,没有采取穷尽式的列举方式,可能是立法者考虑到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无法预测到以后新型的犯罪方式而采取的一种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为日后的司法解释留下必要的立法空间。尽管我国《刑法》第312条并没有明确列举出“收受”的行为方式,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后,将“收受”理解为“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也是该法条的应有之义,因为窝藏里面保管之意,没有取得处分权的行为尚且作为该罪的规制方式,“无偿收受”这种取得处分权的行为方式当然更应该是该罪的规制方式,“举重以明轻”在这里得到适用。同时,从域外立法来看,对于赃物罪均有进行两种量刑幅度,收受行为法定刑较轻,《刑法》第312条修订之后也是两种量刑幅度。分别是3年以下和3到7年有期徒刑,这就为“无偿收受”行为的规制提供了更加合理的法定量刑空间。
从本案反应的案情来看,犯罪嫌疑人洪某将盗窃所得财物变现为金钱和盗窃得来的金钱,供二人生活开支,期间不管赃款如何分配,因为二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已经无法具体区分每笔钱归谁所有,而应认定为共同支配,在此种情形下,犯罪嫌疑人杨某无偿收受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已经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最后对于第三种意见。有同志认为,本案犯罪嫌疑人洪某与杨某属于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对于洪某盗窃来的财物的使用当然“理所当然”,让其女友举报、制止男友的行为不具期待可能性。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超规范的免责事由,应当慎用,罪与非罪的唯一区分标准是构成要件,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讨论违法性和有责性的问题,而不能一开始就讨论免责性的问题,况且,中国传统刑法理论是主客观四要件齐备说,德日的三层次理论可以借鉴但不可盲目崇拜。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为经过上面的分析构成赃物罪无疑,但是是否可以根据我国《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呢?笔者以为不可,五起系列盗窃案,涉案金额达3万元,杨某一直“坐享其成”,主观恶性不可谓不深,同时法律对于“同居”关系也不予保护,法律只是保护“近亲属”关系。鉴于此,杨某不构成犯罪的说法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