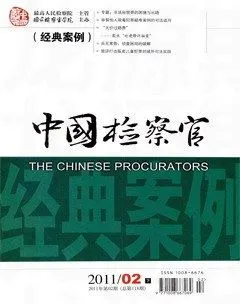施暴后才产生夺取财物意思并取得财物
一、基本案情
董某某赴吴某、孙某等人为其准备的“鸿门宴”,董某某出于害怕也将甘某一同带上,但吃饭时仍与吴某等人发生严重争执。董某某见势不妙立即逃走,甘某被吴某一方扣留。吴某立即让甘某联系董某某,说让董某某带1万元来就可了结双方恩怨。董某某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甘某无法联系到董某某。气急的吴某、孙某随即对甘某拳打脚踢。甘某无奈之下,只得表示愿代董某某偿付这1万元,吴某、孙某即停手。在吴某等人授意后,甘某打电话给自己儿子,说自己打牌榆钱,让其送1万元到附近某车站。随后,甘某与吴某、孙某一行人去车站取钱,吴某一方拿到钱后,甘某和儿子就一同乘车回家。到家后,甘某在儿子的追问下将整件事情和盘托出,随后二人去派出所报案。听闻风声后,吴某、孙某遂于第二天一早主动托人将该1万元钱款还给甘某,甘某亦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不要追究吴、孙二人的刑事责任。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孙某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吴某、孙某在殴打甘某时就产生了抢劫甘某财物的犯意。事实上,在甘某主动提出要代董某某清偿后,吴某、孙某才产生了利用甘某的恐惧心理取得甘某财物的意思,这只是敲诈勒索的故意,因而只能定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孙某的行为成立绑架罪。吴某、孙某实际上实施了通过控制甘某作为人质的绑架行为,并据此成功索取甘某儿子财物,因而应成立绑架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吴某、孙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本案中,吴某、孙某的行为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邀请董某某赴“鸿门宴”;(2)控制甘某,明确表达要勒索董某某1万元;(3)对甘某实施暴力;(4)甘某被迫表示自己愿代董某某给钱;(5)授意甘某以打牌输钱为借口,电告儿子带1万元“赎人”。其中,在第(1)、(2)阶段,吴某、孙某对董某某实施了敲诈勒索的预备行为,但因为董某某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未能接到具体的勒索要求,因而吴、孙二人未着手实行犯罪。但从第(3)阶段开始,吴某、孙某对甘某实施了暴力,并取得了甘某(及其家人)财物,属于行为对象转移所导致的另起犯意问题,应当成立新的犯罪。
(一)吴某、孙某在实施暴力后产生的取财意思,就是抢劫故意
吴某、孙某在董某某逃走、无法勒索到其财物的情况下。对“替罪羊”甘某实施暴行,其发泄怨气的动机非常明显。但根据现有证据,吴某、孙某在对甘某使用暴力时尚未产生(至少是难以证明其已产生)从甘某处夺取财物的想法。甘某为避免遭受进一步的暴力侵害,主动表示愿代董某某给钱,吴某、孙某当即表示同意,并停止殴打。这时,吴某、孙某在明知自己事先的暴力已使甘某无法反抗的情况下,仍然对利用这种“余势”夺取甘某财物抱有容忍、甚至是追求的态度,这就符合了抢劫故意的成立条件。口’在此,利用暴行所形成的抑制被害人反抗的“余势”进而夺取财物,与使用暴力直接取得财物之间,在抢劫罪的法益侵害性(同时侵犯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利)上具有等价性、相当性,因而都能成为抢劫罪故意的行为内容。
同时,吴某、孙某也非常清楚甘某在身体被强制下所做出的承诺完全违背其内心真意,因而并不具有自愿处分自己财产、进而使吴、孙行为合法的性质。这可以进一步确证,吴某、孙某的故意内容应当是实行违背被害人(甘某)意志的抢劫行为,而不是实施利用被害人瑕疵同意的敲诈勒索行为。因此,吴某、孙某只有抢劫的故意,并没有敲诈勒索的故意。
(二)吴某、孙某实施了“当场”暴力劫取财物的抢劫行为,并取得了财物
首先,吴某、孙某使用暴力劫取了甘某财物。吴某、孙某实施了针对甘某的暴力行为,并且通过由暴力所形成的抑制甘某反抗的状态,从甘某儿子处取得了甘某财物。在这里,甘某儿子仅仅是吴、孙二人实施抢劫犯罪、夺取甘某财物的工具,而甘某本人才是抢劫罪(作为财产犯罪)的真正受害人。因此,吴、孙的行为符合了抢劫罪中暴力行为对象和取财行为对象必须同一的原则。
其次,暴力、控制与取财行为符合“当场性”要求。吴某、孙某在宴会处殴打甘某,后在附近车站不法领得1万元钱款,即暴力行为与取财行为实施地本已发生转移、并非处于同一场所,但毕竟吴、孙二人始终持续地控制着甘某的人身自由,因而在抢劫罪的成立条件上说,这与直接在暴力行为实施地劫取被害人财物不具有任何实质区别。故此,从实质的解释论出发,完全可以认为吴某、孙某的暴力、控制和取财行为是“当场”进行的,这就符合了通说中有关抢劫罪必须“当场”劫取财物的见解。
再次,吴某、孙某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本质。甘某电告儿子送钱的理由只不过是打牌输钱、而并非被绑架为人质。甘某儿子尚不足以产生对甘某处境的极度不安感,吴、孙也就不存在所谓“利用他人(甘某儿子)对被害人(甘某)人身安危的担忧领得赎金”的行为,因而没有成立绑架罪的问题。
最后,吴某、孙某事后将钱款主动还给被害人以及被害人的事后态度,均不能改变其抢劫罪既遂的性质。在得知甘某报警后,吴某、孙某遂主动托人将钱款还给甘某,这不足以成立犯罪中止,而仅属于抢劫罪犯罪既遂后的退赃行为,可以作为刑罚裁量时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量。并且,甘某虽强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免于对吴、孙二人追究刑责,但被害人事后的承诺亦不能影响犯罪的成否及其形态,因为公诉案件中国家公诉权之行使不应受制于被害人意志的左右。
(三)吴某、孙某在实施取财行为时具有抢劫故意,符合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理
如前所述,吴、孙二人在采取暴力时还没有(至少是难以证明其已具有)抢劫故意,但在夺取被害人财物之前的控制甘某人身阶段就已经产生了抢劫故意,并且这种抢劫故意贯穿于其取财的目的行为之始终。根据行为与责任同在的原理,只要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的某一个部分(如抢劫罪的目的行为)时具备了成立犯罪的全部责任要素(故意、责任能力、期待可能性、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等),就可以说成立犯罪的主观面和客观面统一起来了,并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因此,吴、孙的抢劫故意虽然只是在抢劫行为的目的行为这一个片段中被体现、而未能支配抢劫行为这一个整体,也不影响抢劫罪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