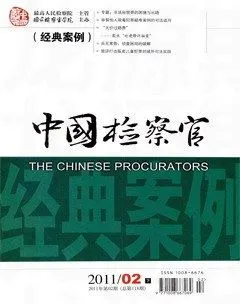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探析
对于刑事证明的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该条款虽然规定比较抽象,但在实践中被运用广泛,一般理解为“孤证不能定案”,即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才能定案,由此确定的证明模式即为印证证明模式,印证证明模式是刑事司法人员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法则。下文结合实践案例对印证证明模式的运用作简要论述。
[案例一]2009年4月17日,被害人石某报案称4月16日晚上被一蒙面人抢劫手机及现金,后公安机关通过手机信号追踪到犯罪嫌疑人陈某。经讯问,陈某详细地供述了抢劫被害人石某的过程,与被害人陈述大致相符:陈某还详细描述了作案现场,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相符。案件移送起诉时,陈某翻供称未实施抢劫,手机系他人卖给自己的,并称以前供述是在被刑讯情况下所作。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赵某伙同另一犯罪嫌疑人驾驶吉普车流窜作案。2009年6月10日凌晨,两人在盗窃一面包车时,被公安民警当场发现。赵某被当场抓获归案,另一犯罪嫌疑人逃离现场。据赵某供述,在逃犯罪嫌疑人为李某,与赵某是同乡。此外,公安机关还从作案工具吉普车上扣押到李某的身份证及驾驶证各一份,与赵某供述相符。经查,该吉普车也是赵某等人盗窃所得,并非李某所有。
[案例三]2008年11月6日晚,行人刘某被撞死在城区道路。公安机关出警后在离事故现场五公里的田地里找到了醉酒驾驶的翁某并扣押了该白色皮卡车。经讯问,翁某因醉酒不知自己是否发生交通事故;经调查,有两名证人证实一白色皮卡车撞死刘某的事实,但未看清肇事司机及车牌;经鉴定,翁某驾驶的白色皮卡车前端灯光装置损坏。
上述三个案例中的证据能否认定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需要从三个方面审查分析。
一、刑事证明思维模式选择——口供补强规则模式与印证证明模式
口供补强规则与印证证明同属刑事证明的思维模式。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口供补强是指在口供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必须与其他证据一起,相互印证一致后。才能起到认定事实、确定被告人有罪的作用。印证证明模式是利用事物间相互印证的关系,借助这种相互印证关系。判断某个证据的真伪和某个事实是否存在。案件事实发生后,证据和一定的案件事实,以及证据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这样。为判明一定证据的真伪及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就可以把该证据与其他有关的证据结合起来,考察它们之间能否相互证实或协调一致。该模式虽然在我国法律上无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广泛运用,而且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据法上的补强证据规则便是对证据相互印证最有力的肯定和强调。而补强证据规则本身就是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由此可知,印证证明模式与补强证据规则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致性。若对上述三案例用口供补强规则进行分析,案例一存在口供,可以适用;而案例二及案例三并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无法适用。
口供补强规则的局限性表现在法律依据上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部分内容,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对于该条款后部分内容却没有正确表达。其局限性表现在司法实践中是片面强调口供的重要性,忽视口供以外证据的收集,导致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增多。相较而言,印证证明模式并不将证据类型限制在口供,而是扩展至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全面地反映了《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含义,对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证实的也可以认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规定:“间接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也可以认定。”因此,对刑事证据分析不宜用口供补强规则,适宜采用印证证明模式。
二、印证证明模式价值定位——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由于在案件的侦查、审查各个阶段,案件的承办方均承担了完全的举证责任,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一旦出现证据不足的情况,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作无罪处理。因此,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办案中难免陷入重有罪证据轻无罪证据的误区。例如,在遇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情形时,若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确实的证据,则往往认为纯属狡辩,不予采信也不予调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8条规定:“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与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因此在运用证据印证模式时,不仅应对证明有罪的证据是否达到印证标准进行综合分析,而且还应对证明无罪的证据是否达到印证标准进行分析判断,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如在案例一中,犯罪嫌疑人陈某在公诉阶段翻供。我们就应当仔细审查其翻供的理由,并调查其他相关证据如讯问的录像、进入看守所的体检情况或其同监号人员的证言等,审查陈某的辩解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印证,以达到排除矛盾、查明真相的目的。印证证明模式将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同等看待、分别审查的价值定位对于端正执法理念、应对犯罪嫌疑人翻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印证证明模式证明力判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作用,单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体现在与待证事实关联性的大小,而多个证据组合的证明力大小一般体现在证据之间的联系。印证证明模式作为一种证据规则,其主要作用就是将具有证明力的各单一证据联系起来,使之形成具有证明力的证据组合,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目的。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按关联性大小不同,可以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可以直接证明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证明力较强;而间接证据则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是否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证明力较弱。
印证证明模式一般先以证明力较强的直接证据作为主要证据,然后再分析其他证明力较弱的证据能否与主要证据相互印证,从而达到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如在案例一中陈某的供述系直接证据,而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被抢手机、被害人陈述为间接证据,则应先假定陈某的供述为真,再审查勘验、检查笔录及手机、被害人陈述等证据在细节上能否与供述相印证。案例二中同案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为证明盗窃是否李某所为的直接证据,现场扣押的李某身份证及驾驶证、被扣车辆为间接证据,则应先假定赵某供述为真,再审查身份证、驾驶证、被扣车辆的信息内容能否印证赵某供述,排除合理怀疑,达到证明结论的唯一性。案例三中对于交通肇事是否属于翁某所为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有看见肇事车辆(白色皮卡车)的两名目击证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出具的抓获翁某经过及对翁某车辆的痕迹鉴定等间接证据。就单个证据证明力而言。目击证人证言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较强,则先假定肇事车辆即为翁某的白色皮卡车,再审查抓获翁某的时间和地点情况及车辆有碰撞痕迹的情况,审查证据之间能否在细节上相互印证并得出唯一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印证证明模式对刑事证明司法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可以把印证证明模式的一般运用方式归纳为:首先对具有证据能力的单个证据进行审查,区分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后,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再审查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接着审查无罪证据中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最后综合全案证据,审查最终结论是否具有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