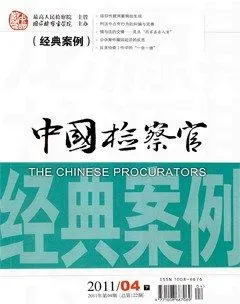李启铭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案之我见
本文案例启示:醉酒驾驶致人死伤,只要对致人死伤结果不具有故意,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达到故意程度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基本案情]某晚,李启铭饮酒后驾车在河北大学生活区道路上从后面将同向结伴并行的两名大学生撞倒。之后,李继续驾驶将乘车人送到生活区校舍附近后原路返回,被门卫拦下带至警卫室。经查证,李启铭是醉酒驾驶,且车速超过该校区时速5公里的限速。被撞二人一人死亡一人轻伤。李启铭负事故全责。
我认为李启明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案,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理由如下:
一、醉酒驾驶致人死伤。只要对致人死伤结果不具有故意的,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从法律规定看,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是交通违法和交通肇事常规类型。《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就包括“醉酒驾驶”的情形,但构成交通肇事罪以造成死伤结果为要件。可见,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是《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常规涵盖范围。
在司法上,醉酒驾驶或醉酒驾驶致人死伤的,按交通违章行为或交通肇事罪处罚是常规,已成为司法惯例。“据公安机关统计1998年,全国共发生5075起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案件,造成2363人死亡;2008年,发生7518起,死亡3060人;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这些官方发布的、成千上万的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案,基本都是以交通违章或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罚的。这里的“基本都是”概率极高,只是没有能够达到“无一例外”的程度而已。
按照生活经验,人们驾驶汽车是为了享受交通便利或者兜风乐趣,没有特别的原因,对发生交通事故都持排斥态度,没有人乐意发生交通事故。循此人之常情,即使是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没有特别的事由,一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法理情理,尺度一致。
二、醉酒驾驶致人死伤。达到故意程度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何认定达到“故意”程度成为关键,为了统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出台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并配发了两个典型案例。
从“指导意见”看,这“故意”的内容是(行为人)对“致人死伤结果”认知,而非对“醉酒驾驶”的认知。从发布的两个典型判例(东莞黎景全案和成都孙伟铭案)看,认定行为人达到故意程度的关键在于醉酒驾驶肇事之后,其后续行为又连续肇事造成新的损害结果。指导意见指出:黎景全、孙伟铭“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车冲撞行驶,其主观上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有关司法人员为了进一步明确肇事之后的“后续行为及其结果”对认定故意心态的意义,还在论文中特意将醉酒驾驶分为“一次碰撞”和“二次碰撞”两种情形,并指出:“在二次碰撞情形下,行为人醉酒驾车发生一次碰撞后,……仍然继续驾车行驶,以致再次肇事,冲撞车辆或行人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此种情形明显反映出行为人完全不计自己醉酒驾车行为的后果,对他人伤亡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此可见,对于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案例外地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键在于肇事后发生“二次肇事”(碰撞),根据二次肇事及其后果所表现出的心态认定是否具有故意。
三、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适用上的差异
从刑法注释角度看,《刑法》第133条之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罪,《刑法》第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罪。因此对醉酒驾驶致人死伤的行为适用第115条还是第133条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认定的依据是行为人对“致人死伤结果”的心态,而不是对“醉酒驾驶”违章行为自身的心态。如果足以认定行为人对明知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会造成死伤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是犯罪故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不足以认定行为人对致人死伤结果具有这样的故意心态,但足以认定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了该结果的,是过失心态,构成交通肇事罪。
确认故意还是过失应当以行为人在行为造成危害结果之时具有的心态为准,具体而言,应以醉酒驾驶造成死伤结果之时的心理为准。在致人死伤的结果发生以后,行为人对自己先前造成的死伤结果的心态。不是犯罪心理,也不影响其犯罪心态的认定。
四、李启铭案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排斥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李启铭“醉酒驾驶致人死伤”案只有“一次碰撞”,即在他撞倒二人致一死一伤之后,虽然继续行驶但没有再次发生碰撞(肇事)。属于醉酒驾驶致人死伤“一次肇事”的情形,按常规应属交通肇事罪。
其次,李启铭仅有的“一次碰撞”(肇事),除醉酒驾驶之外并无特别异常之处。李启铭为接送人而进入该校区,事出有因;与被害人素不相识,无报复个人的动机;也没有表现出对社会公众、该高校学生敌视心理,属于非常普通的醉酒驾驶一次碰撞(肇事)的类型,不能认定他对二被害人死伤结果具有犯罪故意。
再次,李启铭“醉酒驾驶致人死伤”之后,没有停车继续行驶将乘车人送达目的地后又原途返回。根据现有的事实证据,其“后续行为”既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也没有产生具体的危险,不成其为犯罪故意,也不能作为认定他对先前致人死伤结果具有故意的根据。相反,他原路返回以及在校区门口被警卫拦截时没有驾车冲撞之类粗暴举动,表明其肇事之后的后续行为危险性不大,达不到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
综上,李启铭的行为属于普通的“醉酒驾驶致人死伤”之中的普通的“一次碰撞”(肇事)的情形,不能认定对被害人死伤有犯罪故意,不应令其承担故意罪责,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补充说明一点,《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可以适用于校区内道路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伤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项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高校生活区道路属于“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据此,属于《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适用范围。另外,《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对于《刑法》第115条第2款(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属于具体规定或者特殊类型,应当优先适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对于《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而言,也属于具体规定或者特殊类型,应当优先适用。
五、《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醉酒驾驶“入罪”,也不会改变对醉酒驾驶致人死伤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罚的常规
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是刑法中唯一的法定最高刑是拘役的犯罪,也即是处罚最轻的犯罪。“醉酒驾驶”最高处(6个月)拘役,醉酒驾驶“致人死伤”的,适用第133条,以交通肇事罪处罚(通常3年以下有期徒刑),轻重衔接自然合理。不可能越过第133条。直接适用第115条(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另外,比较《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刑法》第133条之一“醉酒驾驶”的法定刑,可见二者的巨大差异。《刑法》第114条“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修正案中“醉酒驾驶”的法定最高刑是拘役。二者主观同是故意、客观同样有公共危险性,同样是危险犯,不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必要,但立法配置的处罚却有天壤之别,说明醉酒驾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可相提并论。
责任编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