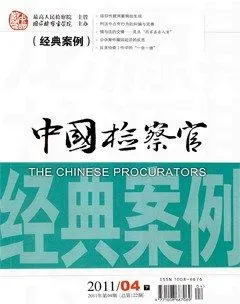从个案的处理看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更新
一句话导读
本文通过介绍个案的处理,分析检察官执法理念从单纯注重实体公正转向强调程序公正,从口供中心主义转向证据裁判主义,从一味追求客观真实转向强调法律真实的使然。
[基本案情]2006年10月18日12时,某派出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将涉嫌贩卖淫秽光盘牟利的曾某在其和妻子共同经营的某音像店内抓获,当场起获淫秽光盘142张。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翻阅卷宗发现犯罪嫌疑人只在派出所的前两次讯问中作出有罪供述,其余均不认罪,表示不知道这些淫秽光盘从哪里来。经提讯曾某,曾某称自己平时开黑车揽活,店面主要由其妻子经营,并由她进货。对此其妻子杜某在公安机关的证言同样证实该点。并称淫秽光盘是她进的。曾某称派出所民警从音像店将他抓获后即将他带到车上,搜查时并不在场,从车上到派出所一直对他刑讯逼供,给他带头套,使电锯,拿棒球棍打全身,用皮鞋打脸,还用脚踹,他不得已才供认罪行。民警把他送到看守所时,狱医看到其身上有伤未予收押,并让民警带去看病。后民警带其到京北医院,并在那里拍了左肩的x光片,后又带回到看守所,在把x光片给狱医后才得以入所。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派出所出具办案说明称,民警在讯问曾某过程中没有殴打、体罚、刑讯逼供的行为。称没有曾某的伤情鉴定和诊断材料。检察官前往京北医院调查取证。医院证实曾某确于2006年10月19日就诊,并拍了左肩位x光片。另外,驻所检察官也向狱医核实了曾某当天入所时确实有伤,并让民警带他去医院检查,但没说伤是怎么造成的,后监所检察官亲自询问办案民警,民警称在抓获曾某前一天,曾某曾出过车祸受伤,因此在入所时狱医不收才带他到京北医院检查。这些重要情节,预审卷宗和两次退补材料中都没有说明。最终检察院以现有证据表明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为由排除曾某的有罪供述,以其他证据无法形成证据链条,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曾某存在犯罪行为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上述材料显示,侦查机关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检察机关在排除程序性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方面,没有简单充当和公安机关共同对付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利益共同体”的角色;没有仅凭公安机关一纸“关于民警没有实施体罚、殴打、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就简单否决犯罪嫌疑人提出刑讯逼供的抗辩事由,而是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中获取的线索积极调取证据,使得公安机关没有刑讯逼供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可以说本案的处理,是检察机关依法尽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体现,更是办案人员执法理念转变的成功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从单纯注重实体公正转向强调程序公正
在以往的办案实践中,由于受传统司法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刑事司法理念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对刑事被追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多年来办案人员积淀下来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观念淡化了执法背后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正是因为执法理念的落后,个别检察官忽视程序的公正,认为实体法是必须遵守的,只要案件的结果不错,程序上的事可以变通,把执法机关视为单纯的专政工具,将刑事诉讼处于“从属”、“服从”、“可有可无”的地位,忽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辩解或置之不理,或严厉训斥或亲自为侦查人员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甚至将其作为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建议从重处罚的理由。对侦查机关重配合轻制约,强调联合办案忽视法律监督。在犯罪嫌疑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靠非法手段获取的寥寥几次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以说,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不力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侦查机关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的发生。
这种过分强调刑事诉讼的工具性价值,缺乏对其独立内在价值品质的认识在实践中带来的恶劣影响有目共睹,近年来暴露出来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冤案就是例证。诉讼程序本身的公正性或内在优秀品质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其工具性而存在,至少在许多场合下这种公正性的欠缺并不影响“正确”的裁判结果的形成。比如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的手段使真正的犯罪分子认罪服法。但是之所以要强调程序公正的独立性价值,就是因为“任何实体权利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确定并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程序的价值不仅仅是保障实体的贯彻落实,更重要的还在于每一个诉讼程序,每一个案件定罪量刑的过程中,甚至每一个诉讼行为,都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文明民主和法治。”
因此,检察官必须牢固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增强对程序内在独立价值品质理论的学习、理解和掌握,加大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重视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侦查人员违法取证抗辩事由的甄别和审查,坚决排除“毒树之果”。以程序的正义保障实体的公正。其目的不仅仅是促使办案人员遵守法律程序,更重要是维护法律程序自身的权威和尊严,以及法律程序背后所体现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司法公正理念的弘扬。
二、从口供中心主义转向证据裁判主义
长期以来,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全部侦查活动的核心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案件时。也只注重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是否做过有罪供述,似乎只要存在有罪供述心里办案就踏实,而不注重有罪供述的来源、提取过程是否合法。
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需要运用一定的证据规则。2010年6月,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规范,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有非法证据收集的禁止性规定却没有排除规则的立法空白。
那么,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需要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须排除?谁来承担证明责任?我们认为,这是判断证据能力的程序问题,解决的是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所做有罪供述的可采性问题,应当和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实体问题需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严格区别,即确立优势证据标准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也符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精神实质。根据该规定的相关内容,只要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就应当由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但前提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有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证据的责任。作为检察人员在审查判断公安机关移送过来的证据材料时,实际上也在承担裁判者的角色,也要进行同样的权衡和举证责任的分配。
以曾某的案子为例,现在能够证明派出所民警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有曾某的供述、曾某到京北医院看病和拍X光片的记录和狱医的证言证实曾某人所时身上有伤并让民警带他去医院看病,看守所才肯接收的情况。而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没有体罚、殴打、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以及民警提出曾某的伤是因为曾某声称被抓获前一天因出车祸受伤,但是在检察院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材料中却并没有提到这个关键情节,亦声称没有曾某的伤鉴和诊断材料。最终。检察院认定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可能性从而排除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那么,为什么只要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我们就应排除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比较两边的证据,很显然,证实民警刑讯逼供的证据环环相扣,能够形成证据链条,有较强的说服力。而公安机关自己出具的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说明如同犯罪嫌疑人毫无理由地宣称自己无罪一样,没有任何说服力,再加之公安机关在两次退补中均未补充到曾某的任何伤鉴和诊断材料,使得民警声称的曾某在被抓获前一天曾出车祸导致受伤的理由更加不具有可信性。这就是优势证据或有说服力的证据标准。因此,在犯罪嫌疑人提出该讯问笔录系刑讯逼供所得的情况下,应当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证实该供述的自愿性和任意性。当然,犯罪嫌疑人一方也应当有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比如展示身上的伤痕或同一个筒号的狱友可以证实或看守所狱医曾为其看伤或民警曾带其到医院检查等)的责任,让检察机关或合议庭有合理理由怀疑刑讯逼供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侦查人员仍然无法就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自愿性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或优势证据来证明,则必须排除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因此,检察官对于侦查机关移送过来的证据材料不能一概照单全收,必须牢固树立证据裁判意识,加强对证据规则的学习、理解和掌握,提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能力,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坚决排除适用,让违法者承担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或许才是根治侦查人员违法取证行为的治本之策。
三、从一味追求客观真实转向强调法律真实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之争,且客观真实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客观真实论认为“诉讼证明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只有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才算达到客观真实的要求”。然而刑事案件作为过去发生的事实无法再现重演,而人们认识它、调查它还要受到主客观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对案件事实的重构不可能完全还原案件的原貌,只是接近案件真相。因此,“客观真实只能成为刑事案件证明的一个客观要求,它告诫办案人员要奋力地接近它,它决不会成为个案的一个具体的证明标准”。诚然,如果目标一旦代替标准,也就等于抹杀了具体标准的存在价值,造成个别执法人员以追求所谓的“客观真实”为借口,往往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将刑讯合法化,忽视证据获得的合法性,甚至不惜投入大量司法资源,牺牲诉讼经济原则。
法律真实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证明的过程中,运用证据对案件真实的认定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因此,将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确立为法律真实,强调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通过证据确定案件事实,通过证据规则确定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这样,诉讼证明活动就能高效准确地进行,同时,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的转化也有章可循。
在证明活动中,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化,必须具备四个要件:(1)每个证据材料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各个证据材料的内容经过排列、组合、分析必须与案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即案件事实相符;(3)借助证据材料进行的推理必须正确,必须符合逻辑规则;(4)全案证据事实必须达到“三统一”,即证据自身统一、证据与证据统一、证据和案件统一。实现法律真实。诉讼证明活动只须紧紧围绕实体法事实的有无进行就可以了。所谓实体法事实指对于定罪、量刑有决定意义的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犯罪事实是否发生;(2)犯罪行为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3)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4)行为的动机、目的;(5)影响量刑轻重的情节(包括从重情节、加重情节、从轻情节、减轻情节和免除刑罚情况);(6)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包括身份事项、责任年龄和有无前科)。
在曾某的案子中,除了曾某的有罪供述之外,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证实曾某的犯罪行为,而曾某的有罪供述又因民警可能存在刑讯逼供行为排除适用,虽然现场起获大量淫秽光盘,但这些物证本身又不足以证实曾某参与贩卖牟利,而曾某关于自己未贩卖淫秽光盘的供述和其妻子所称的平时自己进货,曾某不知情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因此,现有可采性的证据指向证明的实体法事实就是曾某未贩卖淫秽光盘,曾某没有违法犯罪行为。
作为检察官,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及内涵。客观真实是诉讼的目的、诉讼的终极价值,如果放弃对客观真实的追求,诉讼也就丧失了灵魂,司法正义就没有站立的根基。但是,由于案件客观真实的不可再现性以及理解的歧义性等诸多弊端,客观真实只能成为诉讼的目的,而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一种操作性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客观真实是诉讼的旗帜,是自然法的要求与境界,而法律真实是诉讼的标杆,是实定法的标准和状态,在诉讼中二者不可或缺。
责任编辑: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