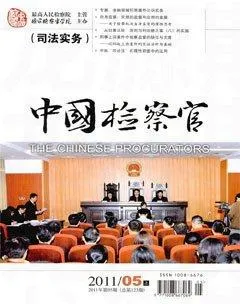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领域中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壮大,随之而来的是涉及证券市场的各种犯罪日趋增多。近年来,涉及该领域的犯罪呈现出专业性强,犯罪手段与方法不断翻新的情况,相比之下,法律的相对滞后,给司法工作带来了许多问题,面对新型犯罪,司法工作人员如何适用现有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有力地打击,以保护新生的证券市场健康稳步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与作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近期在办理我国首例以“抢帽子”交易的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犯罪的案件过程中,便遇到了如何适用法律、如何甄别因果关系等问题。笔者试通过下面的分析论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厘清相关办案思路。
一、基本案情
2001年8月16日,被告人汪建中在本市朝阳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放公司”),法定代表人汪建中,注册资本100万元,汪建中与前妻赵玉玲分别出资80%、20%。2002年10月,北京首放公司增资至1000万元,二人的持股比例不变。公司登记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南里北段健翔新村华亭嘉园A座1605室,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因特网信息服务等业务。
2004年1月15日,北京首放公司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质,基本业务是通过向社会公众发布投资咨询报告的方式,评价证券品种,预测市场走势,为公众提供投资建议。该公司发布证券投资咨询报告的媒体覆盖面较广,主要包括该公司设立的首放证券网(www.shoufang.com.cn)、新浪网、搜狐网、东方财富网、全景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体。
2006年7月至2008年3月间,汪建中先后利用本人及8名亲友(汪公灿、汪小丽、段月云、汪伟、何玉文、吴代祥、汪建祥、汪谦益)的身份证开立了沪、深证券股票帐户,并先后使用上述股票账户在中信证券北京北三环中路营业部、国信证券北京三里河营业部、银河证券北京百万庄营业部、银河证券北京月坛营业部、安信证券武汉营业部开立了17个资金帐户用于证券交易。同时,在工商银行开立了10个银行账户,用于证券交易资金的存取和划转。
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间,汪建中利用其控制的上述股票账户和资金账户,共计交易证券110支,买人金额84.19亿元,卖出金额86.39亿元。其中,汪建中先后针对工商银行、中国联通、中国铝业等38支证券,实施了共计55次“抢帽子”交易的行为,即先行买入某支或多支证券一后向社会公众推荐该证券→再在其期待的价格上扬期间抢先卖出证券,从中获利。
有证据证实,汪建中作为北京首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对公司有控制决策权。案发期间,其先行买入某支或多支证券:然后在买人当天,其会在公司例行召开的集体讨论会上,要求分析师在股评分析报告中加入推荐该证券的信息,后利用公司对外发布股评分析报告之机,通过新浪网、搜狐网、《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知名媒体和网站向公众推荐其买入的证券;此后,在其期待的价格上扬期间(经查绝大部分是在买人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抢先卖出该证券。
经审查,汪建中实施上述“抢帽子”交易的行为,共计55次,买人金额52.6亿余元,卖出金额53.86亿余元。其中,交易盈利45次,获利1.5亿余元:交易亏损10次,亏损2500余万元,共计净获利1.25亿余元。
二、存在问题
针对汪建中的“抢帽子”交易行为,能否适用我国刑法第182条中“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对其定罪处罚?该条款中的入罪条件之一为“情节严重”,情节严重的标准是什么?汪建中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同证券市场的量价变化,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中国证监会在刑事立案审查前,已对汪建中操纵汪券市场的违法《(证券法)》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没收其违法所得1.25亿余元,并处以罚款1.25亿余元),根据这一事实,能否依“一事不再罚”原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是指以法律明令禁止的各种方法,操纵证券市场,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第11条明确规定了操纵证券市场的四种行为:
1 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连续交易操纵);
2 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约定交易操纵);
3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帐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洗售操纵);
4 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
汪建中的行为不符合上述1-4项的规定,而关于能否适用“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来认定其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律依据问题。
对于“抢帽子”交易的行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本案侦查机关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证监会的认定意见:犯罪嫌疑人汪建中利用其控制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向公众推荐证券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在公开推荐前买人证券,公开推荐后卖出,人为影响或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以牟取巨额私利,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侵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汪建中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的“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规定,并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
而证监会的认定依据虽然引用了《证券法》,但也是适用了“其他”条款,实质上其依据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的相关规定,即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但该《指引》并非行政法规,也不对外公开,仅是证监会证券行政执法的指导性文件。并且,该指引中规定的操纵行为要求“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而本案由于“抢帽子”交易行为本身的特点,不像其他典型的操纵市场案件那样有明显的量价变化,因此,本案是否属于《指引》规定的市场操纵行为存在争议。
第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问题。
本罪要求“情节严重”才能入罪,而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尽管2008年3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了《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追诉标准作了规定。但列举的各种标准,均不能对本案汪建中的行为结果是否达到“情节严重”作出明确界定。
第三,因果关系问题。
汪建中“抢帽子”交易行为与证券交易价格、交易量异常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呢?
根据《指引》的相关规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是指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致使证券交易价格异常或形成虚拟的价格水平,或者行为人的行为致使证券交易量异常或形成虚拟的交易量水平。所称致使,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是证券交易价格异常或形成虚拟的价格水平,或者证券交易量异常或形成虚拟的交易量水平的重要原因。
从上述中国证监会证券行政执法的指导性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分析,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要求证实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异常同行为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关联关系。
从法理上分析,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也要求必须有证据证实该行为同行为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由于本案中的“抢帽子”交易的行为特点,不同于以往典型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前者是通过先持有、后公开推荐股票、再卖出,实现获利,后者则是借助资金、持股优势等实施连续交易、约定交易或者通过洗售操纵,实现获利。
典型的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可以通过收集一段时间内,相关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数据,印证该证券是否受到操纵行为的操纵,但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对相关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通过现有技术不能取得充足的证据加以证实,无法排除汪建中荐股的同时,存在其他影响证券量价变化的因素。
基于上述三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不能适用刑法第18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分析意见
“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汪建中在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间,实施了“抢帽子”交易行为55次,交易金额高达上百亿元,非法获利1.25亿余元,其行为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罪刑法定原则,可以概括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应当正确理解:刑法不可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加以事前规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领域,不可能做到一一列举,因此,立法者通过规定“其他”条款,为司法者自由裁量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司法机关也不能据此就无限扩大“其他”的外延,无限制的发挥自由心证,而是要根据立法本意,谨慎适用自由裁量权。
结合本案,对于刑法第182条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只要证实“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情形与列举的三种操纵市场情形类似、具有“相当性”,就可以适用该条款。汪建中通过实施“抢帽子”交易的手段,实现操纵证券市场的目的,其实质同刑法列举的典型的操纵市场是一样的。典型的操纵是利用资金优势或持股优势实现对市场的操纵,而汪建中则是利用其本人的名气、知名度、影响力等地位优势、公众的信赖以及知名网络、报刊等媒体受众广泛等优势,对外公开推荐证券,影响投资者对市场和趋势的判断,从而实现操纵市场的目的。
当然,由于本案行为的特殊性,使得汪建中对于市场的操纵能力及程度与刑法明示的三种典型市场操纵手段存在一定的差别,但这并非本质差别。且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认定意见也将汪建中“抢帽子”交易的行为界定为“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对于刑法已作了“其他”规定,而在实践中出现的具有争议的新型手段,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做出的认定应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故本案的操纵行为基本可以认定。
关于本案是否满足“情节严重”的构成要件的问题,笔者认为,所谓情节严重,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非法获取不正当利益数额巨大;转嫁风险行为给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数额巨大;行为导致证券市场动荡,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等多种情形。犯罪嫌疑人汪建中利用上述优势,影响投资者的判断,从中获利,行为本身破坏了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实施“抢帽子”交易金额高达上百亿元,个人非法获利上亿元,其行为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
关于因果关系问题,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相关证券价格和交易量波动情况的分析报告》显示,北京首放公司咨询报告(含有汪建中推荐股票的内容)发布后,相关证券(推荐的股票)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在整体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即个股开盘价、当日均价明显提高;集合竞价成交量、开盘后1小时成交量成倍放大:全天成交量大幅增长;当日换手率明显上升:参与买入账户明显增多;新增买入账户成倍增加。上述结论是客观真实的,应当说不排除有其他因素会影响相关证券的量价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汪建中采用“抢帽子”交易的方式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影响了相关证券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变化,使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人为扭曲了市场价值规律。
汪建中作为知名股评人,被广大投资者称为“股神”“汪铁嘴”,其利用自己的名气、知名度和影响力等优势、通过北京首放公司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利用知名网络、报刊等媒体受众广泛的优势,对外公开推荐证券,影响投资者对市场和趋势的判断,引诱广大投资者盲目跟进,其结果则造成该证券交易量上升,交易价格被人为拉高。
因此,汪建中实施的“抢帽子”交易行为,是影响该证券量价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操纵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同证券市场的量价变化是有因果关系的。
最后,关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笔者认为,该原则是法理学上的概念,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范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就应到受到刑罚的惩处,很多法律规定中都会明确写明“什么情况,由什么部门或机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受过行政处罚的,并不必然排斥刑法对其行为的惩处,例如许多涉税犯罪,就是在海关给予行政处罚后,如果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接受刑事处罚。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有些行政处罚是刑事处罚的前置要件。因此,不能因为受到了行政处罚,就否定其刑事的可罚性。
汪建中的行为构成刑法第182条之规定,就应当以操纵证券市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至于此前的行政处罚,仅应作为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汪建中主观上具有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以“抢帽子”交易方式操纵证券市场的犯罪行为,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我国刑法第182条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