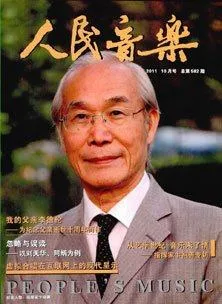根植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音乐
在中国当代的专业音乐创作中,许多作曲家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富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来进行创作,并由此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这种利用大都停留在“借鉴”或“吸收”的层面,而很少是以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这与作曲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既便其中有人属于少数民族,但也很少有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生活的经历,缺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熏陶的积淀,因此自然也就难以在创作中实现更高、更深层次的运用。这方面,藏族作曲家觉嘎算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作为一名地道的藏民,除了在音乐学院接受正规的专业训练之外,他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西藏,可以说藏族传统文化早已深深融入他的血液,而这也会自然而然地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近年来,他扎根于藏族的传统文化创作了一系列风格独特、手法新颖的优秀作品,完成于2004年的室内乐五重奏《轮回》(为小提琴、单簧管、钢琴、长号和大提琴而作)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佛教用语,“轮回”一词在英文中采用梵文的音译:Samsara,但本作品的英文标题却并非该词,而采用的是字面意义的译文:The Cycle Existence,这与本作品将宗教哲学与世俗理念相结合的人文关照,并期望获得某种教化效益有着直接的关联。
藏传哲学认为,人的一生是在摒弃“五毒”(欲、嗔、痴、贪、妒)、超越“四苦”(生、老、病、死)、修悟“三境”(身、语、意)的过程中轮回。这种“摒弃——超越——修悟——摒弃……”的反复轮回是通向人生最高意象——“涅槃”的无常之道。因此作曲家认为,“轮回”作为一种哲学命题,或许能使我们学会思索;作为一种生命历程,或许能使我们学会感受;作为一种教化能量,或许能使我们学会超越自己。
“轮回”中包含的“五毒”、“四苦”、“三境”,它们相加的总数为12?穴5+4+3=12?雪,这个总数既与日常生活中一年的12个月、一天的12个小时(或昼夜相加24个小时)等时间单位直接对应,也与乐音体系中的一个八度12个半音、一个循环12个调(或大小调相加24个调)等不谋而合。鉴于此,作曲家将“12”作为作品构思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并将其贯彻在具体创作中的多种层面,不仅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统一的结构因素,还使其创作构想与相关的哲学内涵联系起来。
在传统音乐理论中,和弦都是以三度叠置为基础的,而在具体的音乐创作实践特别是近现代作品中,由非三度叠置的音组合而成的“和弦”也常常具有一定的使用空间。借鉴三度叠置和弦构成的可能性,三个音按二度结合的和弦也有四种(即以小二度与大二度为基本单位),三个音按四度结合的和弦也有四种(即以纯四度与增四度为基本单位),而且它们在各自的系统中也都体现出与三度叠置和弦结构相似的形态,也都可以相应地称之为“减三和弦”、“小三和弦”、“大三和弦”、“增三和弦”。以上三类和弦共有以下12种原始形态。
1.按三度结合(小三度、大三度为基本单位):
减和弦小和弦 大和弦 增和弦
f—ba—bc f—ba-c f-a-c f-a-#c
2.按二度结合(小二度、大二度为基本单位):
减和弦小和弦大和弦增和弦
bb—bc—bbd bb—bc—bd bb—c—bd bb—c—d
3.按四度结合(纯四度、增四度为基本单位):
减和弦小和弦大和弦增和弦
c—f—bTj3HJRyLGgeufRxwNtJB+gd1KyUuvwwE7/G00ebWFp4=b c—f—b c—#f—bc—#f—#b
用以上12种和弦形态作为作品的基本材料,正好就与“轮回”中的5+4+3=12之总和数“12”相对应。
这种突破传统调式和声规定,将按二度与四度结合的“和弦”也纳入进来的作法使和弦数量增加了两倍。在没有调性约束的前提下,这些和弦的使用都将是平等自由的,这势必会使材料的运用显得杂乱无章,从而影响作品的内在结构力与合理性。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使上述这些和弦相互联系起来并在实际运用中体现出明确的规律性和逻辑性,作曲家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手法,即把结合度数(二度、三度、四度)不同但性质(减、小、大、增)相同的和弦整合成一个“复合七音和弦”。具体构成方式如下:
这是该作品开始的第一个和弦,七个音以叠搭的方式分别构成①②③三个和弦,前三个音(a—d—g)构成按纯四度关系结合的“减和弦”,中间三个音(g—bb—bd)构成按小三度关系结合的“减和弦”,后三个音(bd—d—be)构成按小二度关系结合的“减和弦”。以下是该和弦在作品中的具体运用情况:
例1:第18—21小节
如谱例中所示,此处该和弦是以线性化的形态分布在各个声部,但它们的和声内涵却非常清楚:单簧管与小提琴演奏的两个纯四度音程“a—d”和“d—g”构成和弦①,长号与钢琴右手声部演奏的两个小三度音程“g—bb”和“bb—bd”构成和弦②,钢琴左手声部与大提琴演奏的两个小二度“#c(bd)—d”和“d—be”构成和弦③,此外,长号、钢琴左手声部、小提琴、大提琴在第21小节中演奏的“bd—d—be”半音上行或下行则也是和弦③的分解。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将这些音程以特殊的固定节奏进行反复,从而在相应声部间形成类似于卡农的效果,颇似喇嘛颂经时自然而参差不齐的呢喃低语。
依据同样的原理,分别按二度、三度、四度叠置的“小和弦”、“大和弦”与“增和弦”也可以复合成类似的“七音和弦”。与传统调式和声中的和弦一样,这些和弦也有“原位”和“转位”的不同形态。由于和弦音总共有7个,因此就有一个“原位”和弦和六个“转位”和弦。
在音乐作品中,材料的组织往往都需要围绕一个相对的中心来进行,如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作品中都有的调性或主音等一样。这些相对的中心不仅能使材料的组织更加富有逻辑,而且对作品的结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作品虽然不是调性音乐,但作曲家却用一种特殊的“分段性持续音”来代替“调性中心”的作用,即对上述三种“三和弦”重叠复合构成的四类七音和弦的“根音”作了新的变化,即保留转位顺序的同时设计了作为“调场”的分段性持续音,而这个分段性持续音又与曲式意义上的段落划分相联系,因此又具有了特殊的结构功能。下图为包含“结构”、“调场”、“作品意象”和“音高材料”为一体的结构图式(见下)。
从材料的角度来看,全曲共用了28个七音和弦,依次按“减、小、大、增”四类排列,图示中用粗竖线格开。每类都包括七个和弦,第一个为“原位”,其后的六个依次为六个“转位”。在传统的调式和声中,转位和弦是以原位和弦为基础的,而且无论何种转位它们的根音都相同,但此处的“转位”却并非以之前的“原位”为基础,而是以保持相邻和弦最中间的音相同为前提,如第一类“减和弦”及第二类“小和弦”中的前三个和弦中,每个和弦最中间的音都为“bb”,这也就是作曲家设计的“分段持续音”。不过,此时后六个和弦与第一个和弦就不再是同一个和弦的不同的形态,而是“不同和弦的不同形态”。如第二个和弦“b—e—g—bb—b—c1—#f1”就是“#f1—b—e—g—bb—b—c1”的第一转位,第三个和弦“#d—#f—a—bb—b—f1—bb1”就是“f1—bb1—#d—#f—a—bb—b”的第二转位,以此类推。
该作品的结构与其要表现的音乐意象直接相关,即将“五毒”、“四苦”、“三境”各作为一个部分,分别以“A”、“B”、“C”来表示,而除了循序变换的和弦材料的不同,各部分主要根据“分段持续音”的不同来区分。如“A(五毒)”中的“分段持续音”为“bb”,“B(四苦)”中的“分段持续音”为“be”,“C(三境)”中的“分段持续音”为“b”。这三个部分在分别呈示之后又进行了总结性的回顾,即“A2”、“B1”、“C1”,每部分的材料都只用了一个“增七音和弦”。在这三个部分中,“A(五毒)”最长,意味着“毒”部分之摈弃历程的艰难与漫长。为了突出该部分的特殊意义,作曲家在“B(四苦)”与“C(三境)”之间对其进行了再现性的回顾,即“A1”,材料只用了一个“大七音和弦”。
总体而言,该作品整体上采用了一些具有弹性的处理手法,体现出如下一些特征:首先,“A2、B1、C1”对“A、B、C”的总结性回顾是整体综合再现原则的体现;其次,“A”及“A1”、“A2”部分的三次出现体现出循环原则的特征;再次,七个部分的“分段持续音”依次为“bb—be—ba—b—d—be—e”,刚好是一个原位的“减七音和弦”,从而使材料层面的微观结构与段落层面的宏观结构紧密联系起来;
最后,作品在结构原理、结构形态和结构技法等方面还借鉴了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原则,即通过稳固的三分性框架结构与相对自由的过程性段落结构,以及渐变原则(隐含变奏性质的替换)与突变原则(新材料并列性质的替换)相结合的结构技法,将藏族人文思想和审美观念相结合的文化理念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阐释,从而构成了文化理念的形式化逻辑与音乐的结构形态相对应的同构态。
藏传佛教中重要的轮回思想认为,人是在天界、非天、人间、傍生、饿鬼、地狱“六道”中反复轮回,其中前三种称为“善三趣”,后三种称为“恶三趣”,与此同时又把“六道”分为无色界、色界和欲界“三界”。这种略显神秘的观念和学说一旦纳入到了哲学的范畴并有逻辑地置于形式化的艺术体裁中时,便被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高度,从而凸显出其道德和信仰的内涵。其实,这种理念和审美追求在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和结构技法当中是显而易见的。而作为一部根植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现代音乐作品,《轮回》这部作品所揭示的就是:无论何种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形态,一旦探寻到了它的生成根基和形成源由,那么就能听懂“俗人”们歌声中的那种自在并能够解读他们的“心语”;就能够从“常态”中看到“妙趣”;也许最后还能学会舍弃兴奋、皈依冷静。正因为这部作品中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音响效果上也体现出相应的多样性特征。在该作品中,听众不仅能够感受到雪山、蓝天、阳光等青藏高原的气息,而且仿佛还能听到牦牛身上的铃铛声、藏民的歌唱声、喇嘛的诵经声,甚至还能够从中领悟到宗教的神秘、人生的坎坷和对未来的美好追求。
虽然《轮回》没有直接采用藏族传统音乐的音调素材,但由于其创作构想缘起于藏族传统文化,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因此在基于“音响造型”的织体音型方面充分考虑到了藏族传统音乐的基本语汇和形态特征,以期将作品的音乐风格置于藏族传统音乐、尤其是藏传佛教音乐的基本语境当中。这种“织体”或“音响构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藏传佛教诵经音乐(包括“显宗”念诵经文的声调和“密宗”默念咒语的气韵)的某些特征和藏族传统戏剧“阿吉拉姆”中的“说戏韵白”、“快韵”、“对韵”等的某些声腔和节韵特征作为主要的“织体音型”或“音响造型”贯穿于作品当中,如第1—21小节、第137—155小节、第265—266小节、第271—272小节、第346—349小节、第277—412小节、第372—结束等。前述例1中的音调与节奏便显然与藏传佛教诵经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下例也是如此:
例2:第271—272小节
2.在第29—34小节和第93—106小节设计了一些特殊的织体音型,以之来模拟作为藏传佛教重要法器(乐器)的铜钦——大法号和鼓、钹等综合构成的某些音效特征:
例3:第29—33小节
3.第169—246小节的渐进式发展则参照了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的整体性起伏原则。
总体看来,《轮回》这部作品在整体性音响构造和音乐结构设计等方面,都与藏族传统文化有着紧密关联。从题材的角度来说完全是藏族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部由藏族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将藏族音乐体裁与现代音乐技法相结合的音乐作品。其在创作上完全是基于现代音乐的理念,但其整体音响又是藏族的,这点极其重要而且难能可贵。《轮回》这部作品的实践,对如何用现代音乐的技法和语言表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此文为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曲式结构形态”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8CD64)
吴春福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