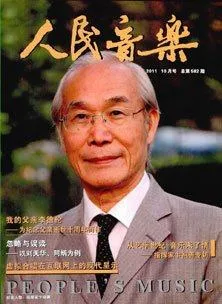感性的智慧与内心的真情
1984年月,我开始了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个学期的学习生活。这个学期,我做了一个受益至今的明智之举——对着学校图书馆唱片目录柜中一抽屉的现代音乐磁带目录,挨个借回去听。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使我知道了当时很少为人所知的现代音乐作曲家的名子;重要的在于,从此以后,现代音乐的音响在我的耳朵中不再是令人惊异,难以忍受,需要适应的了。从此以后,我可以全神贯注地,用聆听的方式去感受现代音乐,而不再被它超乎常规的音响素材所迷惑,也不再为它奇异的标题与永远无法在音乐中听出来的哲理所困扰。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性,那就是从此以后,我开始关注中国现代作曲界的动向,也先后写了谭盾作品的评论、对“新潮音乐”创作群体的分析,以及从美学角度思考现代音乐的几篇文章。
一
当真正能够用聆听的方式去欣赏现代音乐作品时,随着越听越多,我发现,有些作品貌似思想深刻,实则听上去或虚张声势、或杂乱不堪,创作者费尽心机,但落实到听觉上与内心中的感性价值少之又少;同时也有些作品,不仅有想象力超群的奇思妙想,而且在复杂中透出精致,在自由中透出严谨,在奇异中透出自然,在意外中透出流畅。这些作品给人的审美震撼、审美快感与经典音乐带给人的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常感叹,当传统作曲规则不再成为音乐创作的约束与指南时,在听觉的感性世界中,能够驾驭如此复杂的音响关系,实在是太需要“智慧”了。
当一个人具有超出常人的思维能力时,我们说这个人有“智慧”。但是,“智慧”一词,一直是指理性的领域,而面对那些思维条理不清、语言逻辑混乱、说话颠三倒四的伟大艺术家们,我们用什么词汇来描述他们超出常人的思维能力呢?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苦苦的寻找这个词。直至我从李晓冬博士那里听到了“感性智慧”一词(李晓冬2005年语,博士论文《感性智慧的思辨历程》,2007年)。虽然他仅仅在博士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这个词,而并没有深入定义,但这个词让我如获至宝,它对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的意义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理性思维,一种是感性思维。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目的,遵循截然不同的规则,追求不同的价值取向。理性思维处理真假、对错、比较、分析、推理,遵循逻辑的规则;当一个人能够在诸多的因素中,在复杂的关系中始终保持条理清晰、推理正确、答案完满时,我们就会说这样的人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指理性思维中的智慧。但是在艺术的创作中,没有真假与对错之分,不遵循理性逻辑的规则,艺术家所拥有的超乎常人的智慧,不是理性的智慧,他们拥有的是对感性样式的超强想象力与驾驭感性材料的超人能力,他们能够在复杂多样的感性材料中驾驭这些材料,将其组织成丰富而多样的感性结构,这种智慧就是“感性的智慧”。学兄宋瑾一语中的为“美”下了一个经典定义“美是感性的有序与丰富性”(《走出慕比乌斯情结》,宋瑾,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在感性的体验上给人以有序而不单调、呆板,丰富而不杂乱、无序的体验,创造出这样的作品,需要的是感性的智慧。“感性智慧”一词,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思维本质!
在我看来,艺术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感性智慧含量的多少。感性智慧的含量是决定艺术作品审美价值大小的核心。然而正是由于缺少“感性智慧”这个概念的召唤,使得一些作曲家忽略了,在音乐创作时该把自己脑力的重点放在何处。
在现代音乐的创作领域,搞点新花样,弄点别人没见过的小发明,这是靠理性的小聪明就可以做到的。比如,选一件非常规乐器(如鼓风机、炒菜锅、酒杯、高压水枪、汽车轮毂、石头……之类),用一种别人没用过的声音(比如搓纸、撩水……之类),采用一个以前别人没见过的乐器组合(比如琵琶+大号,长笛+埙+尺八+非洲鼓……之类),是属于靠小聪明就能够想到的事。我们可以靠理性的推理,迅速拉出一张能弄出声响的物件的清单,然后将其任意排列,前面加上1YCWJlOjlsOvN95cPHpjXqS9nbz64OtGrXFMimmV3W0=一个“为”字,后面加上“而作”两字,就搞定了。公式是这样的:“为”+“发音物件”+“而作”,比如,“为打字机、石块与定音鼓而作”。在理性智慧的层面上完成这样的作品是不需要太多智慧投入的。但是如何让打字机、石块与定音鼓的声音结合成一个既丰富、又有序的音响组织体,能够在感性的体验上给人以强烈的审美震撼与审美快感,这就不是一般头脑能够驾驭的工作,而是一个具有很高感性智慧的头脑才能完成的。
在现代音乐的创作领域,提出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表现题裁,把一种观念或哲思作为作品的标题,也是靠理性思维的小聪明就能够做到的。比如,道、器、黄道图、电离、七叉角的鹿、同构与异化……之类;当然趁音乐创作观念混乱之时,投机取巧用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虚词或从康熙字典里选几个绝大多数人不认识的字当标题,就更不需要什么智慧。比如我刚刚发明的一个作品的标题是《却、原来——为打字机、石块与定音鼓而作》,这样的音乐创作题裁,靠理性思维的小聪明,一会儿就可以写出一大堆。但是要想从深邃的思想与复杂的情感中抽离出可为音乐表现的感性特征,并将这些感性特征落实到音响的组织形态上,使人们能够从对音乐的听觉感受中领悟到这些思想与情感,则需要太高的感性智慧。
正由于音乐创作是一个需要很高感性智慧的领域,才使得作曲家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使得作曲成为常人不敢轻易问津的领域。如果音乐创作不需要对音乐音响的超强敏感性,不需要对听觉意象的想象力,不需要对音响组织结构的驾驭力,不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实践与刻苦的钻研,任何一个人单凭耍点小聪明就能搞定,那么我想,也就不会有人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产生起码的崇敬感。所以我经常觉得那些热衷于搞点小花样,在音乐创作领域耍小聪明的人,是在自已作践自己的行业声望。
令我仰慕的作曲家,是那些在驾驭音乐音响方面拥有令人无法企及的感性智慧的作曲家。
二
在我看来,浪漫主义时代的最后代表应该是新维也纳乐派的三位大师。虽然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十二音作曲技术中理性设计的成份,但在我看来,勋伯格、贝尔格、威伯恩的作品中包含了大量情感炽烈的作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二音技术使人们意识到了存在着一条靠理性设计可以构成音乐作品的捷径,在这条捷径上,理性的聪明可以弥补感性智慧的不足,加之后续的整体序列、偶然主义、简约主义,特别是约翰·凯奇的恶劣影响,使得现代音乐的创作在总趋势上踏上了一条理性主义猖獗、人性情感缺失的道路。这个趋势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现代音乐似乎什么都能表现,就是不表现人类的情感;一些现代音乐作曲家,什么都想表现,就是想不到去表现人类的情感世界。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艺术能够像音乐那样如此细腻、微妙、直接而即时地表现人类内心情绪与情感的体验。情感不是音乐表现世界的全部,然而没有情感的音乐世界是令人多么遗憾。所以我一直呼吁现代音乐作曲家们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内心中的情感世界;我渴望能够看到在现代音乐创作领域中出现打动人情、感人至深的作品。
三
也许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与观念,第一次听到秦文琛的作品时,就立即吸引了我对他的关注。我是用听觉来判断秦文琛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我是用心灵来感受他作品的情感与精神内涵的。从我第一次开始听他的作品,到写出评论他的《宏大的悲歌》,直到现在写这篇序言,我都从来没有和他交流过,没有想去了解他的创作动机、创作观念、作品表现的意图、技术手法等,原因在于,我遇到过很多作曲家,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言论不能落实在作品的音响上,从而让听者从听觉感受与内心体验中领悟到他们的言论所宣称的东西;在音乐审美的领域,我不听信作曲家的言论,我依赖自己聆听音乐过程中的直感;我更相信我来自听觉的直观感受、来自内心的原发体验。我从秦文琛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复杂-精致,自由-严谨,奇异-自然,意外-流畅的音响组织结构;惊诧于他对音乐音响结构完整性与统一性的控制力;惊诧于他的作品在带给人强烈、惊异震撼的同时让人感到自然而流畅;惊诧于他对声音控制与把握的细腻与微妙。在他作品中透出的感性智慧的高度,加之宏大的气势与高远的意境,让我对他产生高山仰止的距离感;但我又为他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细腻、深沉、真挚而感动,这种感人至深的真情令人觉得他的作品与人心贴近,很亲切。他的作品给人的深刻感,不是简单靠理性分析与归纳就可以概括的;他的作品给人的情感体验,也不是靠简单的日常情感联想就能够明确把握的。体验他的作品同样需要感性的智慧与真情的投入。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他的作品着迷。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为一个人的作品评论集写序,这些溢美之辞,犹如出自一个粉丝对偶像的莫名崇拜。但是我没有这种顾虑。因为我坚信,创作应该发乎真情,评论更应该发乎真情。我自己说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是一个用全身心感受音乐的人,是一个会被音乐感动得不能自制人;我认为,一个人在聆听音乐时应该率性归真、返朴童心,我特别讨厌在音乐评论中看到狡猾的政治家嘴脸;不想在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时候,还考虑社会生存策略,给自己也给被评论人留有回旋的余地;我很希望在这样一个文集序言中,暴露一个对音乐艺术充满笃敬之心的人,一个用全身心感受音乐的人,一个尤其在音乐中不能容忍虚假与耍小聪明的人,一个认真的思索者的真实态度。作为一个态度的拥有者,请允许我在此放纵自己的真情实感,来表达我对秦文琛作品的热爱;我也感谢这本评论文集中文章的作者们,他们旁证了我对秦文琛作品的热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偏好,不仅仅是出于直观的感性体验,更不是空穴来风的胡吹胡擂;当然,我更要感谢秦文琛,感谢他让我在自己的一生中有缘结识并近距离地接近了一位世界级的作曲家。
周海宏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