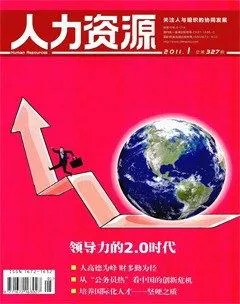优质企业文化与应对经济危机
自1825年以来的近两百年中,企业经常面临的挑战,是造成生产力极大破坏的上百次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然而,并非所有的私有企业都在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面前败北,特别是那些拥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往往是例外。优秀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对环境挑战做出积极而正确应对后的丰硕成果,往往也构成了企业应对下一轮更严峻危机挑战的犀利武器。而其各具特色的先进价值体系,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松下的社会使命至上的价值观
稳定在《财富》500强中的日本松下公司,成立于1917年,到1928年还是一个只有300来人的小公司。在1929年杀伤力极大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松下公司陷入了经济不景气的困境,但总裁松下幸之助体恤工人生活之艰难,实施了不解雇、工资照发的对策,赢得了广大员工的心,树立起仁慈善良的企业家形象,结果,松下公司在这次危机中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有所发展。
松下幸之助的可贵,在于他能结合这次经济危机深入思考了“企业使命”问题,并于1932年得出了“实业人的使命就是使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结论,立志通过“把贵重的生活物资像自来水一样无穷无尽地供应给社会”来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他非常看重自己得到的这种认识,把获得这种认识的1932年定为“创业命知第一年”,而把松下公司过去的15年称之为“母体内的胎儿时期”。松下大张旗鼓开展创业命知纪念活动,说服全体员工认同他的社会使命至上的价值观。松下幸之助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期间,大量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资,不是用低价卖给那些急需它们的穷人,而是宁肯倒掉烂掉废掉,这是企业主只顾追求利润、没有觉悟到身负神圣使命的结果。他强调指出: “即使是个人企业,其经营方针,不能只从私人的立场和方便来考虑。应该是时时考虑到自己的企业对人们的共同生活影响如何?是起好作用呢?还是起坏作用?必须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和判断问题。”可见,松下提出并实行的应战经济危机的方案是:企业主改变价值观,从“利润至上”改为“使命至上”,并使全体员工认同和执行“社会使命至上”。这是从人的思想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色。
对于处于东方文化发源地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来说,既有源自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作指导,又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工作经验,最有条件建成世界领先的社会使命至上的企业文化。
IBM的科技乐观主义
在爆发经济大危机的1929年,美国IBM公司还处在幼年阶段,是它改名而来的第6年,而它的缔造者老沃森却已经55岁了。历尽生意坎坷的老沃森,用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应对这场危机。当时,美国许多商人心中茫然,不知所措, “剪不断,理还乱”,悲观失望,借酒消愁:但老沃森却乐观自信,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股票狂跌、财政不佳而惊慌。他要求IBM全体员工一如既往地里面穿笔挺白衬衫、外面穿无瑕贵西装,依然如故地滴酒不沾,还是一聚会就合唱歌曲,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世界经济危机。
当时,美国许多公司根据销售形势不佳而减产,随着人力资源过剩而裁员,但老沃森却继续大张旗鼓地倡导他坚持了18年的“思考”理念,既不跟风减产,也不随波裁员,他高调宣布“现在不是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不足”, “现在是一个必须将一切做到最好的时刻”,他要求工厂增加科技含量高的制表仪及其零部件的产量,并将其储存在库房里。当时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削减研发预算,老沃森却增加对研发部门的投资,不仅投资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进行信息处理研究,还耗资100万美元建造了美国第一所企业实验室(它成为后来包括施乐公司的帕罗阿尔托研究中心和微软实验室在内的企业实验室的典范)。老沃森因这些非常规的言行,在当时被人称为傻瓜、疯子,IBM也因此濒临资金链断裂的边缘。但老沃森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可以唤起需求,科学技术可以推动销售,科技进步没有终点。他深信IBM公司当时研发和生产的能进行数据处理的制表仪,不仅是人口普查必不可少的设备,而且是一种能够处理一切可计量值(如资金、库存、军队等)的设备,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果然,当罗斯福总统1935年一签署《社会保障法案》,由于每个企业都必须详细记录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工资和必须缴纳的社保资金,对制表仪的需求几乎一夜之间迅猛增长,以致政府有关部门计算制表仪的订购量不是以合而是以整船为单位。年幼的IBM就这样在危机中成熟起来了,后来获得了计算机领域的“白雪公主”和“蓝色巨人”的美名。
不难看出,老沃森应战危机的方案是:相信科学技术,加大科技投资,看重科技含量,增加相关产量, “科学技术至上”。这是科技乐观主义文化,具有大机遇与高风险并存的特征。看准了,企业就大飞跃:看偏了,企业就会破产。有诗曰:“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能过关”不等于“必过关”。但多次苦战,终必过关。这对于我国企业界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索尼“专心创新至上”的价值观
日本索尼公司成立于1946年,也是一家崇尚科技价值的企业。它没有公司歌曲,也没有禁酒要求,但其缔造者井深大、盛田昭夫等管理者自觉建设的“技师至上、刻意创新”的企业价值体系,却很有特色。
第一,他们不仅提出了要摆正“增加利润”的位置,还提出了要摆正“扩大规模”的位置,实质上做出了“赚取利润诚可贵,扩大规模价更高,若无真实价值增,利润规模皆可抛”的价值排序。索尼作为一家制造企业,坚持其最高任务就是要生产出对人们确实有用的、能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物质产品。
第二,他们提出了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金融投机商兴风作浪,导致汇率与工业竞争力无关地发生变化,造成股价与上市公司业绩无关地大起大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热衷于去炒股、炒汇等来盈利或弥补损失,索尼明确反对这样做。盛田昭夫呼吁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同时提出了“通过投机买卖而不是靠提高生产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的口号,认为“用技术改善旧产品并创制新产品”的价值,高于“炒股”、 “炒汇”、 “贴自己的牌子卖别人的产品”、收购、兼并等的价值。在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看来,只有坚持把精力放在用技术改善旧产品并创制新产品上,才能够激发员工的自豪感、自尊感、责任感,才能够培育员工的工作热情、创新理念、和谐思想和忠诚意识!正是在这个价值体系的指引下,索尼成功地把新技术转变成了许多吸引人的新产品,并在频繁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茁壮成长,长期保持在世界500强之内,在2009年排在第81位。
索尼应对危机的方案,就是专心致志地创新,包括以推出新产品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销售创新和管理创新, “专心创新至上”。对于不缺规模的中国国有公司来说,索尼的创新文化显然有着长期借鉴的战略意义。
微软“创造未来至上”的价值观
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于1975年,创始人比尔·盖茨当时只有19岁。微软发展很快,1986年在美国上市,2009年位列世界500强的117位。盖茨对于股市和汇市的投机性,对于股价和汇率反复无常的大幅波动,具有天然的忧患意识。他担心股票上市以后,员工上班时会老想着股票价格而分散工作注意力,滋生“靠买卖股票致富”的投机倾向;他更害怕“金融巨鲨”兴风作浪把他的公司搞垮。然而事实上,尽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发生了一百多场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但微软不仅毫发无损,反而越办越大,越办越强。微软的成功,可归结为其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自己“改变世界、创造未来”的公司使命。
要创造未来,首先要正确预测未来。盖茨从小受到美国计算机解放运动的熏陶,在大型计算机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深信未来是个人电脑的时代,是软件可以发展为独立产业的时代,因此个人电脑的商机一露头,盖茨立即辍学创办公司,并把公司使命确定为“让个人电脑进入每一个家庭、占据每一张书桌”。结果,微软坐上了个人电脑软件行业第一的宝座。盖茨对微软的成功总结道: “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
盖茨继续坚持以“改变世界、创造未来”为己任,于1995年出版了畅销全球的书籍《未来之路》,预测未来是许多个人电脑连接起来的网络时代;但该书未预料到计算机网络时代来得那么快,而且这种网络会发展成为全球化的商贸网络。这两个“没有料到”是盖茨对未来预测的偏差,据此,有专家预言:“因特网将会迫使微软公司停业”。但盖茨把“微软将破产”的专家预言当成一场真正的危机来应对,发动全体员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各自提出应对危机的方案,然后带着这上百种的方案去一个幽静处开始自己的思考周,得到的结论是:立即把公司的人、财、物,从主攻“交互式电视”迅速转向主攻“计算机网络”。结果转向获得了成功,使微软在计算机网络时代不但没有破产,而且继续保持了软件产业的领先地位。这表明了以“改变世界、创造未来为己任”的微软,虽然积极大胆预测未来,但并不幻想预测没有误差,其“创造未来”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发现、及时纠正预测误差,然后按照纠正后的预测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微软打造“创造未来至上”的企业价值体系的生动体现。
为了满足创造未来的需要,盖茨认为公司不能只“开发”而不“研究”,他说“可以预见到个人电脑将发生的很多变化(性能、存储量、显示水准、动态图形处理等等)……另一些变化则较难猜测,比如电脑的语言处理能力、推理能力、声音识别能力或者是学习能力等等”,因此盖茨决定,微软不但要加强与学术研究界的联系,而且自己也要进行基础性研究。微软研究院就是为创造未来而建立的基础性研究机构。这个机构一开始就安排了30位专职研究人员,计划每年投入1000万美元,到1995年专职研究人员就增加到了300人。
1999年,盖茨又出版了一本预测和创造未来的著作《未来时速》,探讨了网络时代之后的数字化时代。盖茨给微软规定的企业目标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继续保持它在个人电脑时代名列第一的地位。尽管微软目前还不一定排在第一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微软仍在前几名之中。
自创建以来的35年里,微软已经打造了“创造未来至上”的企业价值体系,这使它在各种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面前十分主动,几乎感觉不到危机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它所感觉到的危机,是预测未来发生误差的危机,是自己领头羊的地位被别人取代的危机,它应战危机的方案就是: “深入思考未来,正确预测未来,成功创造未来。”对于我国国有公司来说,借鉴这种“创造未来至上”的企业文化,是不是也可以减轻乃至摆脱汇率、股价之类金融危机的干扰而赢得主动呢?这显然是值得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