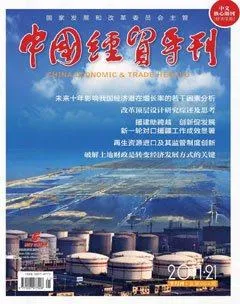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趋向及对我国的政策含义
“全球经济失衡”是2005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最早正式提出的,其突出特征是美国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增长,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东地区及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的持续大规模增加。该现象出现上世纪90年代后期,1999年开始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2004年后呈现加剧态势。部分观点认为,2007年美国的次债危机及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失衡进入强制性调整阶段。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涉及到主要相关国家的储蓄和消费、政府收入支出、对外经济部门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外汇储备账户等的调整,是一个涉及到宏观和微观变量的、相互联系的过程。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缓慢性和结构性调整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
(一)G20提出的三部门指标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积极加强各国宏观政策的合作和协调。2011年2月和4月召开的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提出了两阶段治理全球经济失衡的方案,选取包括公共债务与政府赤字、私人储蓄与借贷及经常账户赤字三类指标度量全球经济失衡,而汇率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作为治理全球失衡的参考变量。
G20提出的指标体系,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一致。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失衡是指对外经济的失衡,而对外经济失衡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表现为包括贸易项目、国外投资净收益和经常转移净额在内的经常项目,持续出现巨额的顺差或者逆差;贸易逆差的存在意味着某种借贷关系的成立,国际资本的流入或外汇储备的减少,反之,贸易盈余的存在,意味着国际资本的流出或外汇储备的增加;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失衡实际上是国内经济失衡的表现,经常项目差额反映的是国内的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经常账户盈余意味着国内储蓄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大于投资,反之,经常账户赤字则意味着国内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
(二)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并没有显著调整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以全球经济失衡为显著特征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冲击。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涉及到以美国为代表的经常账户赤字国与以日本、亚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经常账户顺差国的调整。本文采用G20会议提出的三部门指标体系,主要对美国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失衡调整状况进行分析。
1、美国的私人部门和经常账户都有所改善
金融危机后,美国私人储蓄率上升较快,家庭债务负担略微下降。具体来看,私人储蓄率在2005年5月达到0.8%的低值,2007—2010年从2%上升到5%。美国家庭债务负担率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美国家庭债务率在2005—2007年基本处于12—14%之间,2008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10年四季度降为11.75%;家庭金融负债率2008年前高达18%以上,2009年和2010年持续下降,2010年四季度降到16.64%。
从对外部门来看,危机前经常账户赤字开始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调整步伐。1998年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重超过2%后急剧扩大,2006年为6%。2007年开始调整,2009年降为2.94%,2010年略微上升至 3.55%。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11.7%,为1998年以来最高增速;拉动经济增长1.34个百分点。2011年一、二季度,美国出口按年率分别增长7.9%和6.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2、美国政府部门的不平衡状况加剧
为应对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恶化。危机以来,由于政府通过财政的大规模扩张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下降,并利用公共资源为金融机构再融资,美国政府部门的失衡加剧,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急剧扩大,从2007年的1.85%增加到4.66%,2009年和2010年上升到9.72%和10.07%;联邦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2008年为69.4%,2009年、2010年持续增加,分别达到了84.20%和93.20%。2011年上半年,美国甚至出现了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国会众议院于8月再次提高了联邦政府举债上限。
3、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调整不显著
亚洲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盈余的调整不显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对外贸易盈余在2008年出现了大幅减少,韩国甚至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和马来西亚在2009年贸易盈余显著下滑。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亚洲主要经济体的货物贸易盈余2010年有所回升,中国的贸易盈余持续下降。
从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看,亚洲主要经济体的最终消费率尚未出现显著提高。原因主要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些国家大多采取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投资相对于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较显著的拉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扩大消费需求,主要涉及生产要素市场化、提高劳动者收入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的系统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尽管短期内,美国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化”带动了私人部门和对外贸易部门的调整,私人储蓄率显著提高,家庭负债率小幅调整,经常账户赤字明显缩减,但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失衡状况空前加剧;而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货物贸易盈余在危机后大幅缩小,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开始反弹,最终消费率尚未出现上升趋势。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总体上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依赖以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等促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长期性因素,目前尚未出现显著变化。失衡调整将是缓慢而长期的过程,但其中也酝酿着一些新的变化。
二、美国的结构性变动将对全球失衡调整形成深远影响
经济格局的变迁,更大程度上是诸多微观结构的变化,逐渐形成一种趋势性的力量。
(一)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
危机之后,美国最主要的变化是奥巴马政府将“再工业化”作为重要战略,即奥巴马提出的“岩上之屋”而非“沙上之屋”。奥巴马提到“岩上之屋”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将更多地依靠储蓄、投资和出口。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12月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提出重振制造业的目标主要是创造和维持高回报的制造业岗位。框架还强调了政府两大重要任务:一是积极促进目前研究水平已很先进、没有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但可能成为潜在投资领域的技术发展,政府保护其知识产权,促成其发展形成规模,并为技术扩散提供便利条件;二是政府将确保美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并消除国内市场上来自国外生产者的不公平竞争。
奥巴马政府将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并提出了在5年内使出口翻番的口号,为此,美国专门成立了“出口促进内阁”和“总统出口委员会”,从2009年开始陆续出台了快捷融资、简化审批程序等一系列刺激措施。《2010年美国总统贸易政策日程》提出,贸易政策的优先目标主要包括:维护和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增强美国在贸易规则体系中的权利;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技术创新等。
(二)美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诉求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最有潜力的地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增强其战略性产业竞争力的同时,积极构建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更多地谋求其在新一轮产业和贸易格局中的优势。
一是美国积极加入并推进“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TPP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利和透明度等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涉及到的边境内问题。这是奥巴马执政后美国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标志着美国对贸易谈判的新模式与区域合作新方式的战略转变。
二是虽然APEC是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以签订正式条约作为法律纽带,但美国当前积极利用该平台,为更好地实现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5月19日至20日主要的议题包括加强区域贸易和投资一体化、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加强监管合作及规制融合等重点议题,这些都关系到了美国下一轮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贸易、投资与监管规则,是美国核心利益的体现。
三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的质疑,成为中美近几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新焦点。美国认为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阻碍外国投资和对华进口,要求中国审核所有创新政策,确保这些政策不给外国和国内供应商区别待遇,同时实现中国政府的承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以吸收外国投资和进口,这充分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的战略取向及政府的积极作用。
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服从于促进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考虑到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放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一步作用的空间已受到明显制约,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出现回落、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宏观调控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预计失衡的调整将是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另外,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酝酿着调整,全球产业发展也可能进入大调整和大重组时期,各国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和标准等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三、对中国的政策含义
(一)失衡的缓慢调整:加大了我国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难度
一是受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影响,预计我国外部需求的增长速度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趋于放缓,这使得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二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甚至不排除推出QE3的可能,这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也将更加突出。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可能会造成更多的热钱流入,并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监管和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是2012年将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无论从加快经济复苏步伐,还是从国会两党争取更多支持看,美国都有可能围绕人民币汇率升值、双边贸易与投资及国内自主创新政策等进一步对我国施压,对此,我们应有充分估计,及早做好相关预案。
(二)失衡背景下的结构性调整:机遇大于挑战
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推出新兴产业革命,我国一方面,面临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同发达国家技术和经济水平差距扩大的风险。能否抓住关键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要素禀赋及制度竞争力,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二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作用。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战略性指导作用的边界如何界定,二者如何相互作用促进经济有序发展,成为问题的关键。
另外,美国试图通过TPP主导亚太地区新的贸易和区域合作模式,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面临如何既采取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经济与贸易规则体系,又积极参与并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两难,基本立足点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目标,既要顺应发展趋势,不断促进我国经济贸易规则的改进与完善,又要顶住国际压力,坚持立场,切实维护我国经济发展的利益。
(杜琼,1980年生,山西祁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