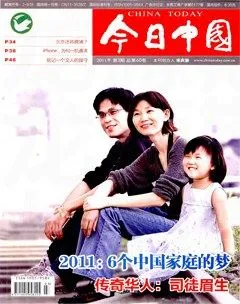我为音乐狂
音乐是一种美妙的天赐之物,它能够跨越时空和文化的鸿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迄今为止,人类学家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文明中能少得了音乐。事实上,音乐的历史比人类文明还要久远——它似乎潜藏在我们这个物种的血液之中,与生俱来,割舍不断。
世界上能够发出乐音的动物种类极少,只有部分鸟类和哺乳动物,拥有节奏感的动物就更罕见了。曾有研究者试图训练黑猩猩和猕猴打拍子,结果只换来数千次的失败。反观人类,却对音乐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不但享受音乐的美感,还懂得主动寻求和创造更美妙的旋律。科学家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让人类如此为音乐痴迷?
音乐快感从何而来
古往今来无数人为了音乐如痴如醉,达尔文也不例外。他认为伴随着人类的进化,音乐也在不断演变,越来越复杂、精致、美妙。但与生物的“适者生存”不同,达尔文发现很难找到驱使音乐进化的动力。1871年他甚至有点冷酷地写道:“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排列音符的能力事实上对人的日常生活习性没有一点用处,人们为何乐此不疲实在令人费解。”
近期,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的科学家将音乐带来快感的根源锁定为多巴胺。多巴胺是一种脑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主要负责情欲、快感、亢奋及满足等信息的传递,对食物和性爱的渴求都要归功于它。这是大脑制造的一种奖赏机制,通过无数次重复快感来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延续。正是有了多巴胺,原始人才会在肚子不饿的情况下依然有觅食的渴望,也是因为它,才有了饱餐之后路过食品店时依然有压抑不住的购物冲动。
被测试者在聆听悦耳音乐时,常常有战栗、颤抖、发冷、起鸡皮疙瘩等现象,科学家观测到这些音乐快感通常伴随着心跳、脉搏、呼吸频率的波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脑血液大量涌向分泌多巴胺的区域。
随后科学家为被试者注射了一种极易与多巴胺受体结合的无害放射性元素,并利用PET扫描跟踪这种元素的运动情况。如果多巴胺数量较多,则该元素将会随着多巴胺在血液中运动;如果多巴胺较少,该物质就会固定不动。这项实验首次验证了人们在听到喜爱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大量多巴胺的事实。
多巴胺的诞生
在确定了多巴胺在音乐快感中发挥重要作用之后,轮到核磁共振成像仪登场了。
这一次研究者特别招募了8位音乐爱好者,并请他们带来了各自最喜爱的音乐——为了保证实验不受干扰,这些音乐中不带有任何人声。他们多数选取了古典乐,也有部分爵士、摇滚和流行音乐。
核磁共振显示,听自己喜爱的音乐与听他人喜爱的音乐时,多巴胺的分泌水平完全不同,前者高出后者平均6到9个百分点,有的人甚至高达21%。这个数字极为可观,要知道,6%即等同于享用一顿美餐后的心满意足,这说明对某些人来说,好音乐比美食更令他们感到愉悦。(由于研究对象是从200多名自认对音乐“有感觉”的人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这一结果不能简单地推广到所有人中。)
此次实验还意外发现,在音乐高潮到来前约15秒钟和高潮真正到来时,大脑的不同位置会产生两次多巴胺的小高峰。研究人员表示,多巴胺先后集中出现于两个部位,说明期待快感与实际体验到快感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那么人是因为喜爱音乐而分泌多巴胺,还是因为多巴胺的快感而喜爱音乐呢?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人类真的相当喜欢音乐。至少这些被试者的多巴胺显示,他们普遍喜欢巴伯的《弦乐柔板》、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和德彪西的《月光》。
意识障碍造就音盲
能享受音乐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还有一些人是无法区分好听和难听的音盲者,他们不仅唱歌跑调,而且意识不到这一点,即无法察觉出乐曲中的一些音符在不在调上,因此无论听什么音乐都无法从中得到乐趣与享受。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出现在大脑意识环节。换句话说,在一串难听的音符响起时,音盲者的大脑能够做出短暂的响应,却没有形成持续的意识,因此无法察觉。
脑电图仪对正常人和音盲者进行的分别监测发现,两组实验对象在听到跑调或不协调的音符大约200毫秒后都有反应,但音盲者在约600毫秒之后,反应基本消失。这短短一瞬间不足以识别不协调音符并传递给更高一级、负责感知的大脑区域。
严重音盲患者不只是无法欣赏音乐那么简单,还可能存在沟通障碍,如辨别不出对方话语中传达的表示生气、害怕或讽刺等情绪,这就需要求助专门的训练和治疗了。
千万年来一直陪伴着人类的音乐,依然存在着太多的谜题,好在它还将长久地萦绕在人类耳边,我们有的是时间,为之或悲或喜,或者冷静剖析。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个小孩子满脸陶醉、咿咿呀呀地哼唱着从没有人听过的歌曲,不妨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因为人类最珍贵的本能,莫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