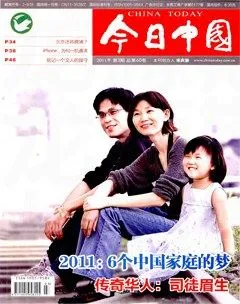整个民族在期待什么
整整50年前,我的父母在内罗毕的恩姆巴卡西机场送我——一个瘦弱但无忧无虑的八岁男孩——登上国际航班,让我回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我倒没有像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那样,他从印度被送回国接受英式教育之后,注定五年都不能见母亲一面。其后十年间,我和家人至少每年团聚一次,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但是这样残酷地逼迫家里的小男孩与母亲骨肉分离,伯恩家族和吉卜林家族究竟想要收获些什么呢?
我坚信我的家人根本不可能预见到我50年以后的未来!他们大概能够想到我会为人父母,但绝对不会想到我会管理一家伟大的大学出版社,也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小男孩后来会成为那所英格兰学校的校董。不过如果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这的确是他们期待我在接受了那所学校的教育之后,能够成就的人生。学校会给我灌入一些英国的文化和教养。说句风凉话吧,我的父母大概还希望学校里身着黑色长袍的老师能够施以棍棒之教,去除在殖民地长大的孩子身上的野性,改掉他带着非洲口音的英语,就后一个目标来说,他们成功了。我的确因为各种各样的恶作剧常常被老师拿一根竹棒教训——当然,那些并非体罚,只是“教训”而已!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大多数父母都期待学校能够发掘出孩子身上最优秀的东西。当然,总有一些家长会异想天开,事实上这类人不在少数,万般渴望老师们能够施展某种魔法,把他们十分平庸的孩子变成天体物理学家或者小提琴演奏大师。
这样的期待让我担忧,不过远比这更让我担忧的是,更有些可怕的家长整日孜孜于让孩子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也通不过任何考试,因为成功的教育会让父母在孩子眼中变得很愚蠢。相信我: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教育被视为一种基本权利,事实也理应如此。但问题在于如果教育由国家提供而无需个人付费,而不仅仅针对那些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那么迟早有一天,公众会期待国家为其子女的教育承担全部责任。
我很高兴地看到东方家庭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们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最大的义务。相反,在我的祖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常有人为此命题辩护,声称父母都,根本没有时间教育下一代。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具体承担该义务的教师又不无鄙视。教师的低薪更使这一情况呈恶化之势,或许人们认为教师和其他拿低薪的政府公务员一样,提供的是一项“基本服务”吧。
有句格言说:“能者做,不能者教。”难怪教师这个行业在许多国家如此不受尊重(讽刺的是,经济越是落后的国家,公民对教师行业反而越尊重)。然而,如果人们停下来想一想,会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成年之后都要承担某种教育者的角色。作为父亲,我显然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角色。作为商人,我也总是需要为员工提供建议和培训,作为他们的榜样。我们都是教育者!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期待学校怎样帮助我们培养孩子呢?每个孩子在离开学校时,都应该扎实地学到一些核心科目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些基本的了解。他们应该流畅地使用自己的母语,懂得必要的社交礼仪。我愿意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一种适宜的单纯环境中学到这些。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我还有更大的期望。作为一个商人和雇主,我希望大学毕业生能够了解一些世故,懂得职场的纪律和责任,最起码要有一些批判思维的能力。我觉得这些乃是当前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人们合理期待的领域:高校毕业生的确掌握了职业技能和考试技巧,却很少有人表现出色,能够识别问题或机遇、分析局势、制定备选方案、对若干可能的解决方案加以明辨。这些是我们在工作中需要的品质,也正是成功的必要品质。
不过育人的过程始于家庭和小学,而不是大学。而尽管我在本文开头谈到孩子们远离家人之苦,离家求学不一定有害身心健康。我对此有发言权: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学校就是我的家,我无时无刻不乐在其中。我相信吴伟的女儿在香港读书也定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