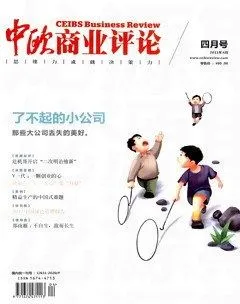我为死作好了全部准备
我有幸这一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继续推进残友,它没有大到我无能为力的样子。所有创新我都走在最前面。当一切全部推完了,企业就完全去掉我的影子。如果最后大家还能说,“你只要活着就是一杆旗,只要活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我就心怀感恩。
高福利国家把残疾人照顾得好得不得了,发展中国家做得没有那么好,但无论好与不好,谁也解决不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级需求,残疾人群真的不能实现第五级需求?
对残疾人来说,不让他们走入第五级,就是把他们当动物饲养。香港的残疾人朋友来我们这里参观,对我说:“大哥,看到你们,我们就想哭,我们每天活得没滋没味啊!”他们的残疾补助金足够生活了,白1打麻将,晚上就泡吧。要知道,人生是一个钟摆,老在一个摆上会断裂的。
被砥砺后才会懂得
我出身于高干家庭,父母留下些遗产,足够自己衣食无忧了。我用10年的时间上了3个电大,也算接受过高等教育,可一点成就感也没有,自卑地耗在家里,这种活法很摧毁人,把人变成行尸走肉。
每一个残疾人,无论残疾状况如何,都是在一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成长的。上小学,人家放学后,你才能跟人交流:家人上班去了,等他们下班,你才有家的感觉。许多残疾人在家里受到过多的呵护与照顾,心智却变得更加软弱。我很幸运,“文革”十年逼着我融入主流社会。尽管进不了医院,不能接受治疗,我的身体彻底完蛋了,可即便没有这十年,身体早晚也得完蛋,血友病人就是会不断出血嘛。这十年,父亲作为走资派被关了起来,母亲也被关了几年。我到处流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我读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特别有感觉。生活是真正的大学,人必须真正被这个社会磨炼与砥砺,才能看清这个社会。
与其他残疾人的不同是,我更加了解健全人。一般残疾人跟健全人在一起有隔阂,他们不了解主流社会。可即便我坐着轮椅和健全人呆在一起,也能感觉到他们所有的喜怒哀乐和压力。当一个人不说话,我能察觉到他讨厌你了。因为小时候寄宿别人家,家里不能给人钱,你要处处观察别人的脸色。没有这种经历的外人永远无法理解。司马迁有一篇《报任安书》,讲到自己关在监狱里的感受,也说别人没有亲身体会,是永不会明白的。
健全人走向社会,从最底层往最高层上升的过程中,心态是平衡的,自信心随着成绩的提高而建立。残疾人一生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寂寞地呆在家里,不停地伸手。偶尔幸运地结婚,在妻子和儿女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永远有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这样的压力下,不是特别坚强的人,都想要自杀。我就自杀过三次。这是很恐怖的生活,一点儿也不人道,可到这一步也没有办法。千百年来,一个社会自己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又怎么顾得上鳏寡8faa031b54c01e068053e9fbe7a3d6eb孤独?所以人要学会自助,当年我们就是以此出发,尝试自救。
利万物而不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相信,每一个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时候,都有自雇的能力。不管他有没有文化,是聪咀还是傻子,摆摊也好,做苦力也好,都是自己愿意的。人人都有雇佣自己的能力。对残疾人来说,道理也一样。其实,人生的目的最终绝对不是为了钱,只是在当下的社会,周遭的各种事物太不安全,太不保险,逼得人们格外看重钱而已。
电脑对残疾人而言,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只用脑袋不用四肢,网络对残疾人意味着可以坐在家里干外面的事情。我想改变原来的活法,围绕“屏幕”创业,改变残疾人的命运。残友公司正是在这样的主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残疾人主观上耐心,客观上稳定,构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在残友,理科毕业的残疾大学生就做软件,因为软件的工程量最大,也最赚钱,我们一单合同最高达到过600万元:文科类的残疾大学生就做动漫,他们能够熟练使用大型3D、动画制作软件:没有文化,可以走出门的残疾人,就生产山寨机、笔记本,实现就业:重残出不了门的人就在淘宝上帮人看店,挂个QQ卖货,也能自养:还有一些残疾人文化程度不太高,就去现代服务业的呼叫中心(声谷通讯)。呼叫中心的最大问题是员工频繁跳槽,残疾人一来,跳槽问题解决了,他们坐在那里,每天回答600个同样的问题,一点都不烦。
我们这12年最辉煌的是两个“没有”,第一没有贷过款,第二没有领过政府的民生补助。弱势群体依靠高科技强势就业,不是别人可怜我们。这与我的个人性格及企业文化有关,我们想向主流社会证明,残疾人在这些行业是优质的劳动力。这话可不是轻易喊的,既然是优质人力资源,就别找政府要钱。
我们走到今天,各产业相互配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我们给了残疾人(包括健全人)空间。这里的每一个人必须不停地有自己的空间。一个人的能力超过了现在的职务,一定要给他/她空间,给不了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企业方向出了问题。
残友是一个“社会运动”:我们有一条商业的腿,围绕“屏幕”,软件、动漫、电子商务,残疾人爱下到哪就下到哪;我们有社会组织,残疾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欢迎创新,“社会运动”就是要包纳宽容,只要证明方法可行,我们就采纳,所以残友利万物而不争。有员工说,我就愿意和国外机构打交道,我们就让他去募款(基金会有募款活动)。他募来款项,有了业绩,想做募款部的主管,我们就成立一个募款部,让他去做。
12年前,5个人,1台电脑,从我家中起步,没有银行贷款,残友发展得比一般企业快。无论残疾人还是健全人,为什么在这里每个人的幸福感都这么强?我的同事刘敬文(残友集团副总经理)就是健全人,以前是《晶报》的首席记者,月收入2万多元:在残友,他每月只拿3500元。为什么愿意留在这,里?这里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离开残友,很多年轻人走到社会上是愤怒的。
我只能追求光荣
我为我的死作好了全部准备。总部很快要搬到新场地去了,我就守在老地方,跟集团完全脱离开,这里(指残友集团现所在地)改成郑卫宁办事处。我死了,办事处就撤销。我活着是他们的一杆旗,他们需要我出差、出国,我就去做,让残友的平台广为人知,让更多的残疾人过上新的生活。我把事业传承给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目前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对好的一个制度。以制度应对危机,比一个人应对好很多。
我想对做企业的人说,别说企业困难就不能和谐了。能,怎么不能?论困难,谁有我们企业困难,一分钱款没贷过,经常处在缺钱的状态。有两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员工没有拿过工资。即便现在,我们拿的也是半饥半饱的工资。然而大家每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都能跟企业愿景的实现形成共振,每个人都愿意牺牲。
我们没有关于企业文化的书和守则,没有工作规章,什么都没有。大家一走进来,全部看得见。人在做,天在看,就这么简单。包括我自己,我是为了什么?没那么多伟大思想,我就是追求我的个人价值。仅仅由于我短命,我无法享受物质生活,我不能抠女(粤语,拍拖女生),我不能唱K,我不能逛街,我不能旅游世界。我不能,我出去了都不安全,因为经常要输血。那我就追求光荣,就这样。
罗曼·罗兰说:“人生是艰苦的,对那些不甘于平庸鄙俗的人,是一种每日的战斗。”战斗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价值实现的路径跟企业愿景结合就更好了。孤军奋战很少能成功,那就照企业的要求来,大家一起用力,每一次成功都是自个儿的实现。
我是一个幸运儿,千百年来被压抑的群体,我这一代能够引爆一种趋势,够幸运的了。一个人精力有限、学识有限、能力有限,做好一件事情不容易,我有幸这一生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能继续推进残友,它没有大到我无能为力的样子,没有大到我仅仅想要把握权力和影响力。所有创新,我都走在最前面。当一切全部推完了,我在企业什么都不是了,就完全去掉我的影子。如果最后大家还能说,“你只要活着就是一杆旗,只要活着就是一根定海神针”,我就心怀感恩